同龄同寿两诗翁
这一对双子星可谓有缘人。二人同龄,都出生于1928年;去世韶光也相差无几,相隔96天双星陨落。余光中去世于2017年12月,洛夫则是2018年3月,二人都是90岁遐龄。
余光中(1928-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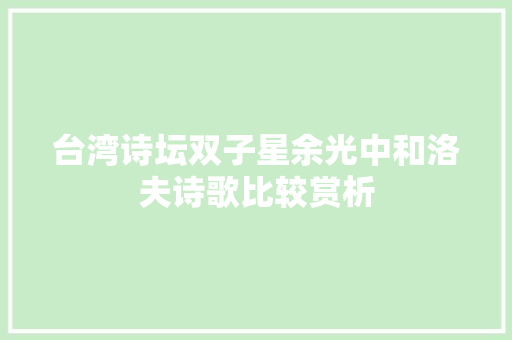
余光中自称“江南人”(祖籍泉州,生于南京,母亲是常州武进人),对江南情怀满满,贰心中的江南是“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鹞子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多燕子的江南”(《春天遂想起》)。余光中1949年赴喷鼻香港,次年到台湾,生平生活在大陆、台湾、喷鼻香港、欧美四地,他曾诙谐地说“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喷鼻香港是情人,欧美是外遇”。
洛夫(1928-2018)
洛夫是湖南衡阳人,1949年去台湾,1996年搬家加拿大温哥华。他曾做过24年军人,去台前在衡阳从军,去台后当过海军陆战队队员和金门联结官,45岁以“海军中校”退役。洛夫对家乡衡阳感情很深,1988-2012年间先后九次返乡探亲。“醒来/不知身是客/偏偏游子夜尿多”(《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写出自己第一次回抵家乡夜里激动难眠的心情。
洛夫回到家乡衡阳
台湾诗坛双子星
余光中和洛夫在台湾新诗史上都贡献卓著,造诣特出。整体来说,二人在诗歌创作方面,同中有异,异大于同。
余光中生平共出版20本诗集(不含旧作选集),共写了一千多首诗,个中最有名的诗集代表作该当是《白玉苦瓜》;他还把自己的诗翻译成英文,出了一本自译诗选集《守夜人》。洛夫生平出版11本诗集(不含旧作选集),个中《魔歌》被评为台湾文学经典;还出版两本长诗《石室之去世亡》(1965)和《漂木》(2001)。这两首长诗名气很大,是洛夫的代表作,他凭借《漂木》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余光中1954年与覃子豪等创立蓝星诗社。虽然他的早期诗歌也倡导“横的移植”,向欧美学习,但后来“从西方回归东方”,做了“转头浪子”。他的诗风整体上偏传统一些,抒怀色彩和古典色彩更浓,有时很看重格律和押韵,如“风,也听见/沙,也听见”“哭,也听见/笑,也听见”(《民歌》),“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给我一杯海棠红啊海棠红”(《乡愁四韵》)等。
洛夫1954年与张默、痖弦创办《创世纪》诗刊。他的诗虽说兼顾“横的移植”与“纵的继续”,但整体上偏于当代。像长诗《石室之去世亡》,充满十足的当代感,“没有什么比一树梨花夭亡更令人发狂啊/如果你迷恋厚实的屋顶/你会失落去浩瀚的繁星”,意象繁复,诗意朦胧。
乡愁诗比较
余光中和洛夫都是由于战役缘故原由离开家乡,飘零宝岛,以是心里时时怀念大陆、思念家乡,因此都写了很多乡愁诗。
余光中被称为“乡愁墨客”,他的很多诗都弥漫着浓浓的乡情:“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乡愁》),“钟全体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白玉苦瓜》),“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还是白霜/祖国已非少年的祖国”(《独白》),“月光在海上铺一条金路/渡我的梦回到大陆”(《舟子的悲歌》)……每一句都饱含着他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动听肺腑。
洛夫也写过很多乡愁诗,像《我在长城上》《那年代,乡愁与铜像》等,最著名的是《边界望乡》。1979年洛夫访问喷鼻香港,在余光中陪同下,于港深交界处的落马洲闲步,写下了这首名作,“一座远山劈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表达了墨客的乡愁之重和不能返回祖国的悲痛心情。
洛夫的长诗《漂木》本色上也是一首乡愁诗,而且把乡愁上升到哲学高度。所谓“漂木”,便是一棵飘零的树,诗中写到“树,忘了树/末了在锯木厂的木屑飞扬中/找到无数个自己”。这首诗长达三千多行,创百年新诗之最。
传统文化诗比较
余光中和洛夫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二人都写了大量以古代历史文化为题材的传统文化诗,以此表达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余光中称自己是传统文化的“守夜人”,他在诗中写到:“末了的守夜人守末了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守夜人》)。他写得最多的是屈原和李白,生平五写屈原四写李白。他写屈原“把影子投在水上,把名字投在风中”(《水仙操》),“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漂给屈原》),表达对屈原的无比崇敬。他写李白“酒入愁肠,七分酿成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寻李白》),这大概是百年新诗史上写李白最有名的、最霸气的诗句。
洛夫晚年曾经写过二十多首“古诗新铸”的创新作品,题为《唐诗解构》,把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等人的诗歌进行诗意重修,打造一道靓丽的诗歌风景。洛夫的长诗《长恨歌》是致敬白居易的作品,写得大开大合,用语大胆,技巧纯熟,受到很多人推崇。“一堆昂贵的肥料/营养着/另一株玫瑰/或历史中/另一种绝症”,表达了对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荒淫误国行为的痛斥。
余光中与范我存结婚照
爱情诗比较
余光中和洛夫的爱情诗也很有名。余光中与表妹范我存的爱情故事流传很广,他为之写了很多诗,如“你带笑地向我步来/月色与雪色之间/你是第三种绝色”(《绝色》),“一池的红莲如火焰,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竟觉得/每朵莲都像你”(《等你,在雨中》)。后面这首我非常喜好,感情深厚,措辞幽美,又有当代感。
洛夫的爱情诗写得也很缠绵,像“你那曾被称为云的眼珠/现有人叫做/烟”(《烟之外》)。有一年洛夫生日快到了,夫人陈琼芳郑重宣告:“赶紧为我写一首诗,否则今年的生日我不给你做饭,让你饿肚子。”洛夫苦思冥想,写下名诗《由于风的缘故》,第一段写到:“昨日我沿着河岸/溜达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想象奇特,意象新奇,让人击节。
洛夫与夫人陈琼芳
“新古典主义”与“超现实主义”
有一个问题必须面对,余光中和洛夫在台湾诗坛都负有盛名,造诣在伯仲之间,但不可避免招来孰高孰低的评议。有人认为,二人早期造诣相称,难决牝牡。但后期余光中探索乏力,诗艺有所低落,创作重心转向散文;而洛夫对诗艺不懈精进,日臻完美,他1982年创作的悼母长诗《血的重版》堪称精品,新世纪创作的长篇巨制《漂木》更是惊世之作,以是洛夫的诗歌造诣高于余光中。
余光中讲诗
当然,余光中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诗歌和散文双峰并峙,综合文学造诣比较高,以是梁实秋评论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造诣之高,一时无两”。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好洛夫。我认为洛夫的诗在当代性和思想深度两方面都更胜一筹。洛夫曾经评论余光中的诗“意象的创造性不足,短缺一种哲学的深度……浅层次的居多”,我以为大致如此。
余光中的诗多是传统抒怀,喜好直抒胸臆,浪漫文学色彩浓厚,自称为“新古典主义”;而洛夫每每奥妙借助意象和形式的创新,弯曲表达情绪,适当疏离现实,更富有当代诗风格,这大概便是“超现实主义”。台湾评论家简政珍认为“以意象的经营来说,洛夫是中国口语文学史上最有造诣的墨客”。
洛夫的荷花诗与禅诗
个人很喜好洛夫的荷花诗和禅诗,二者每每又融为一体。洛夫生平爱荷,和黄永玉一样是个“荷痴”,他说:“懂得欣赏荷的人,才真正懂得爱”(《一朵午荷》)。名作《众荷喧哗》中写到:“我就喜好看着你撑着一把碧油伞/从水中升起”。他在散文诗《大悲咒》中说:“我的涅槃像一朵从万斛污泥中升起的荷花。”荷中禅意,韵味十足。
洛夫写过《无声禅诗十帖》《金龙禅寺》《夜宿寒山寺》等大量禅诗,他被称为“诗魔”即与此有关。“晚钟/是游客下山的小路/羊齿植物/沿着白色的台阶/一起嚼了下去//一只惊起的飞蝉/把山中的灯火/一盏盏地/点燃”(《金龙禅寺》),朦胧的禅意,幽美的诗境,新巧的措辞,当代的手腕,让人着迷。
“下次你途经,人间已无我”(余光中),“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由于风的缘故”(洛夫),韶光无情,余光中和洛夫,这对台湾诗坛的双子星都已作古,但他们的作品仍旧光彩熠熠,“与永恒拔河”,人间永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