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就像一颗颗饱满的种子,有若何的造就就会有若何的发展。
——莫愁大不雅观园
外孙铁头,2015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本诗集《柳树是个臭小子》,那年他只有9岁。该诗集2016年获第25届“东丽杯”全国鲁藜诗歌评比“新人新作”奖。
2017年,他的第二本诗集《玉轮读书》再次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想,外孙写诗已经有了一定的根本,如果再深入学一些古诗,定能使他已经开启的诗心之窗更加妖冶敞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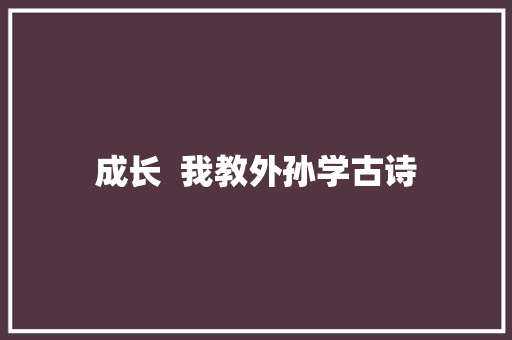
我是语文西席出身,很喜好古诗词,出版过童谣集《小鸟早起》。因此,外孙节假日来我这里,教他学古诗的事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如何教外孙学古诗呢?常言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必须设法勾引外孙对古诗感兴趣,因此我就选择一些有插图的古诗书教他。
看图学诗,外孙以为既有趣又能帮助他理解诗意,学起来兴趣很浓。我学过《儿童生理学》,知道孩子学习的把稳力是有限的,因此每次学习均在半小时旁边,这能使他对学诗保持持久的激情亲切与希望。
我的教法比较大略,一是“读”:一样平常先由我范读两三遍,再让外孙朗读两三遍。在外孙朗读中,创造字音读错,就及时予以纠正。比如《石壕吏》中“如闻泣幽咽”中的“咽”字,外孙总误读成“yàn”,我就给他讲“咽”字的三种不同读音和不同用法:一种读音是“yè”,如哽咽、喇叭声咽;另一种读音是“yān”,如咽喉、咽喉要道;还有一种读音是“yàn”,如咽唾沫、细嚼慢咽、狼吞虎咽。
当外孙读得比较上口时,就让他结合课文中的注释和插图自行理解诗意;当外孙对某些诗句理解不了向我发问,我就捉住契机予以讲解。比如《潼关吏》中有“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的诗句,外孙不知“戟”为何物,我就画出戟这种兵器的图形给他看。这样,一首古诗的措辞笔墨演习内容便丰富起来。
二是“背”:在熟读和理解诗意的根本上,让外孙背诵。外孙在背诵过程中,有卡壳处我就及时提醒,并帮助他想出影象的办法。比如《木兰诗》中的“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他总把诗句弄颠倒,我就对他讲,欢迎木兰的人物是按辈分大小出场的,他便不再背错。
三是“写”:先是看着写,后是背着写,通过动笔写来加深影象。比如《潼关吏》一诗,虽然不太长,但不押韵,背诵有一定难度;而通过写,外孙便很快背诵下来。在默写时,外孙常把一些字形相似的字写错,比如《石壕吏》中“暮投石壕村落”中的“暮”字,总把“暮”字写错,我就用卡片写出字形相同的5个“mù”——暮、幕、墓、慕、募,并通过组词教外孙加以差异。
我已经离开讲台多年,而教外孙学古诗,使我重新找回做西席的乐趣。有人说,最好的诗教来源于家庭,我深表认同。女儿小的时候,对背诗很感兴趣,我就一首一首地教她背。
当时我在一所中学任语文西席,曾叫只有四五岁的女儿给大哥哥大姐姐们背诵我正教的《木兰诗》。这种示范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学生,教室里掌声一阵接着一阵。没想到时隔多年,外孙又成了我的“学生”,跟我津津有味地学古诗,实在令人愉快至极。
孩子就像一颗颗饱满的种子,有若何的造就就会有若何的发展。外孙爱上写诗并非有时,其母险些每天娓娓地带他读诗背诗,在和风小雨的滋润津润下,这粒诗的种子才得以破土萌芽。我教外孙学古诗,实在是在为诗苗浇水,而诗花能否尽情地盛开,则取决于他自己的天赋与发展。
来源:《莫愁·家庭教诲》
1
编辑:巴恬恬
校正:张秀格
审核:王淑娟
莫愁大不雅观园
有温度 有态度 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