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以为“花间派”就此失落传,但是没想到过了七百年的韶光,“花间”一派在世上依然还有传人,这个人便是素有“清初第一词人”之称的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出身清朝贵族,自幼学习了浩瀚的儒学经典,成年之后又潜心研究文学理论,反对清初词坛作者对唐诗宋词的大略模拟。
纳兰性德在继续“花间派”词风的同时,对之又进行了一些摈弃,自创出了一种豪放中还兼有婉约的独特词风,在后世中享有极高的盛誉。
清代徐釚在《词苑丛谈》夸他的风格,是“不啻坡老稼轩”。意思便是,他无异于苏轼、辛弃疾再世。并且他的“豪放词”兼有“言情”功能,在后一点上,比苏轼、辛弃疾还要略强上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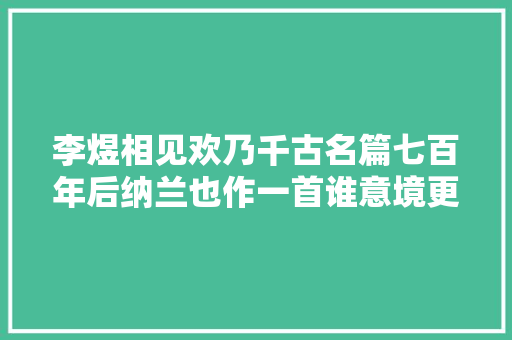
尤其是在“离愁”这个主题上,纳兰性德造诣斐然,他的《相见欢·微云一抹遥峰》是个中的代表作。而在同一个主题和词牌上,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同样造诣极高。
一、从《相见欢·微云一抹遥峰》看纳兰性德奇特的词风《相见欢·微云一抹遥峰》——清·纳兰性德
微云一抹遥峰,冷溶溶,恰与个人清晓画眉同。
红蜡泪,青绫被,水沉浓,却与黄茅野店听西风。
词作意译:
一抹淡云浮上了远方的山峰,寒山衔云,彷佛是那个人清晨在镜子前画眉一样。
昨夜她独守闺房,看红烛落泪,忍青绫被寒,憋着一屋子让人透不过气的,浓浓的水沉喷鼻香。而我却夜宿黄茅野店,耳中灌满了西风。
纳兰性德这首词,上阙先是由清晨看到的风景,遐想到“那人”在清晨画眉的场景。高下阙再倒过来,由她的空闺冷寂,再通过“蒙太奇”似的手腕,遐想到自己在边塞野店中的环境。
这种写法,恰好便是清代评论家所提到的“蕴豪放、婉约为一体”的范例写法。
古人常说“远山如黛”,把远山比成美人的淡淡的眉弯,纳兰性德并不是第一个人。但是看到了远山,很少有人能立时遐想到独守空闺的爱人。
古人作诗填词,有把青山比成君子的,也有把青山比成朋友的。比如辛弃疾写“我见青山多妩媚”,虽然用了“妩媚”二字,但是完备没有把青山当爱人的意思,而只是把它当成心腹。
由此也可以看出,纳兰词的独特之处。纳兰性德在塞生手军,看到寒山上挂着白云,遐想到了闺中人清晨画眉。然后又清晨画眉,倒着回忆到了她昨晚独守的寂寞。
寂寞的人会怎么样呢?她清闲空闺饮泣中。杜牧在《赠别》中说:“腊烛有心爱惜别,替人落泪到天明”。这里的“红烛泪”,便是代指“那人”在哭泣。
“青绫”是一种高档的薄型面料,水沉喷鼻香也是贵族闺房中常见的喷鼻香料。她夜晚呆在这样的房间里,按理来说是不会以为冷的。但是在词作人看来,她该当是很冷的。
由于在开头那几句中,词人已经把“冷溶溶”和青山的意象连贯了起来。既然她的眉像冷溶溶的山,那么她自然全体人都是带着冷意的。
她之以是会哭泣,正是由于离愁使她觉得到寂寞空闺冷。这里的画面,实在是词人自己展开的遐想,不是真实的场景。末了一句“却与黄茅野店听西风”,才是他当时真实的写照。
二、李煜与纳兰性德风格的异同《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南唐·李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样平常滋味在心头。
李煜的这首词,虽然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但是它的有名度也靠近“国民”级别了,当代还有人把它改编成歌来演唱。
这首词的特色便是,用口语化的措辞来讲“离愁”。当然,由于李煜个人的一些经历问题,也会有人从这首词中解读出“亡国之恨”。
“无言独上西楼”,是由于心中有愁,愁到无可名状,无法言说。再看到天上冷月如钩,残缺不全,回忆到了现实中的寂寞。
由于当时的李煜,已经是北宋的“囚徒”了,那么“梧桐深院锁清秋”,锁的或许就不但单单是“清秋”了,还有词人本身,以及他的离愁。
接下来,词人非常直白地重复了他的主题,见告大家,他的这种离愁像细丝和头发一样,是剪不断、理还乱。
他不断地回顾过去,明知痛楚却又无法割舍掉。由于真执的感情是不受理智约束的,以是才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煜全词都是“明写”离愁,紧张是写自己对故国的思念之情。用语非常浅近,完备不须要过多的阐明,只要一读就能明白词作表达的意思。
而纳兰性德的《相见欢·微云一抹遥峰》紧张是写“离愁”,或者是对亡妻的思恋。在技巧的利用上面,显得就比较繁芜了。
李煜词作纯是出于自然感情的流露,没有对行文进行刻意的雕琢。但是,纳兰性德词作中润色的迹象却非常重,写得也很是讲究。
比如,纳兰性德会先写“远峰”,然后再写“清晓画眉”,是先由远景写到想象中的近景。下阙第一句先写闺中,再写“茅店”,这是由室内写到室外。
并且由于闺中的环境完备是靠他个人的想象,而想象又是“虚”写的,以是这首词是由实写到虚,然后再由虚写到实。
其余,纳兰性德也把稳到了词作中色彩的搭配。“微云一抹遥峰”,云是白色的。“红烛”是赤色的,“青菱”自然是青色的,还有末了的“黄茅野店”,“黄茅”是黄色的。
作为一首风格比较特异的“边塞词”,纳兰性德可以说是写得很精细了。但是比起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彷佛还是差了一口气。
李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中有一句名句,便是“寂寞桐梧深院锁清秋”。梧桐在中国传统诗词意象中,代表了高洁的品性,而“清秋”的意象代表是“愁”。
“愁”这种意象,本来是无影无形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被“锁”起来呢?实在,这里代表的是词民气坎中的无奈与暗藏的恐怖之情。
由于明显是有人,不想让他表现出这种“愁”。那么,该怎么办呢,只有把他的这种愁绪与他这个人本身,都一起锁起来。
李煜在他后期大量的“亡国词作”里,一味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故国之思”,以是“锁清秋”一句涌如今这里,就显得有一点可疑。
事实上,也一贯有人疑惑这首词并非是李煜的作品。他们认为这首词的作者,是与他处于同时期,并且同命运的蜀后主孟昶所作。
仿佛只有孟昶那种胆小怕事的形象,才能与“锁清秋”不敢愁的形象挂中计。不过更多的学者,还是支持这首词的作者为李煜的说法。
结语李煜的词之以是历来都广受好评,紧张是在于他的词作情意真切,用语自然,险些不会进行什么雕琢,他纵然是“雕琢”,也绝不会让人一眼就看出来。
一个作者的创作造诣,的确会受到个人经历的限定。李煜之后,再也没有涌现过这样一位多愁善感,同时又文采过人的悲剧帝王,以是再也没有人能写得和他一样平常生动。
纳兰性德的生命比李煜还要短暂,他只活了三十岁。他的悲剧紧张是个人的悲剧,关乎儿女私情与个人仕途。而不是像李煜那样,写的是亡国悲剧,盛大动人。
纳兰性德的《相见欢·微云一抹遥峰》,背后并没有什么繁芜的故事。不过是借“花间派”的风格,写出了边塞征人与闺中爱人的“离愁”。
不过,纳兰性德也凭借自己出色的学问跟见识,使得七百年前的“花间派”,在脱俗之后得到了重生,“蕴豪迈于柔情”,在清初文坛上闯创出了一条新路,一样不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