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算起来,不如我们水秀山青,逍遥清闲,甘淡薄,随缘而过。”
樵夫表示认同,接着他俩就“水秀”好还是“山青”好进行了辩论。渔翁说以“无荣无辱无烦恼”之乐,樵夫对以“逍遥四季无人管”之欢;渔翁又夸以“无忧虑”之幸,樵夫还以“无短长”之福。末了二人联诗两首,共话山水之乐。
这段笔墨与小说主线关系不大,在清朝版本的《西游记》中乃至还被删掉了,一样平常读者也只是把它们当作诗词来看,实在作者在这里复诉了邵雍的处世哲学,要想弄懂它,就得理解《渔樵问对》。
短长关系不可分离,无处不在
《渔樵问对》的开头,樵者问渔者,鱼贪饵之利而受害,人贪钓之利为什么却能蒙利?既然大家都是为利而动,结果为何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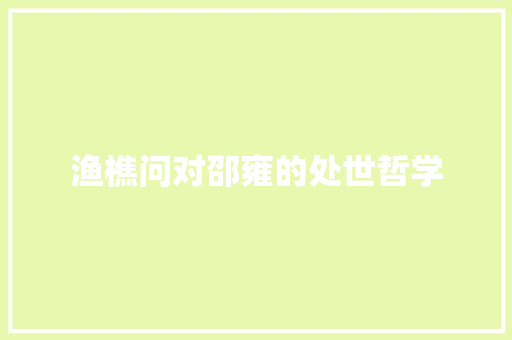
渔者于是进行了辨析,说:“子知其小,未知其大。”
樵者把短长关系大略的对立了起来,故而没有看到,对付鱼来说,吃到饵是利,被钓中计是害。可是,如果鱼整天都找不到食品吃,那么这样的害不是更大吗?比较于饿去世,冒险吃饵的害处不是要小些吗?对付人来说,钓到鱼是利,吃鱼也是利,彷佛钓鱼有利而无害。可是,如果人整天都在钓鱼,却一条也钓不到,又没韶光去干其他的营生,没有收入,这不也是大害吗?如果还要冒险出海捕捞的话,害就更大了。因此,钓鱼就像吃饵一样,得冒着受害的危险去钓。短长关系不可分离,无处不在。故云:
“鱼利乎水,人利乎陆,水与陆异,其利一也;鱼害乎饵,人害乎财,饵与财异,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
”
利与害属于“同出而异名”者,它们既对立又统一。鱼之短长寄于饵,人之短长寄于财。鱼如果不与人争饵,怎么会受害?散户如果不与庄家争财,害又从何而来?故知,争是从利转化为害的中介,以是《老子》说:“夫唯不争,故无尤。”财富实在是靠创造出来的,并不是靠争取而夺得的。夺得之物,岂能长保乎?
反过来,让是从害转化为利的中介,人相向而行,旁边相让,则畅通无阻;鱼倏忽水中,先后有序,则能鱼贯而行。因此,邵雍说:
“夫义者,让之本也;利者,争之端也。让则有仁,争则有害。仁与害,何相去之远也!
”
让不仅将害转化为利,而且还得仁;而争如果只是为了利,就可能害义。孟子见梁惠王的第一句话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众人皆笑其迂腐,可是义乃是利的根本,只有义才能让,进而使害转化为利。
相反,如果只追求利,而不讲义,那么父子跟路人就没有什么差异,都只是利益关系而已。更糟的情形是臣为利而弑君、子为利而弑父,故邵雍曰:“利不以义,则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追求利益一定要基于道义。
这便是《渔樵问对》里的义利之辨。
“有利”并不即是“有用”
樵者又问,鱼得烹饪之后才能吃,这是不是解释自己的木柴对渔者有用?如果没有木柴,鱼是否因不能吃而无用?
对此,渔者回答说:“子知子之薪,能济吾之鱼,不知子之薪以是能济吾之鱼也。”木柴对付鱼的用途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火,假使木柴因淋湿而不能生火,那么它对付烹饪也就从有用转化成了无用。因此,木柴是“体”,火才是“用”。
火寄托于燃料之上,燃料得火才有用,火得燃料才有体;水无形无状,以浸润为用,浸润以水为体。因此,火属于用,水属于体,火可以使临近的水变热,水却不能够使临近的火变冷,这是由于体用有别的缘故。以是说,有体必有用,但是体不即是用,用也不即是体。
众人都认为有利就会有用,而被人利用便是受害,因此“用生于利,体生于害。”但是我们已经论证过,利与害是不可分离的,故而体与用也不能分开。众人愚钝,没有弄明白有体必有用的道理,因而才执着于“有用”跟“无用”之间的对立,看不到它们的统一,故而误以为某些事物一无是处。
《老子》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人们执着于有形有状之物,认为它们于己有利,就如樵夫执着于木柴一样;可是如果没有无形无状之物,没有火,那么有利的木柴也就没有用处。盘子的外表再精细,如果不是空心,就不能装东西;屋子的外墙再华美,如果没有内部空间,也不能住人。人们在盲目逐利的时候,是否也该当想一想:这对付自己有没有用?
“名”与“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樵者出柴,渔者出鱼,二人烹鱼而食,之后在伊水边闲步,谈论《周易》。这部分的内容与《不雅观物内篇》一样,因此我们略过不谈。
之后他们又评论辩论了名实问题,渔者说:
“夫名也者,实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敷,利丧于有余,实丧不敷。此理之常也。”
战国期间,当“循名而责实”的“正名”思想在儒、墨、名、法诸家盛行的时候,庄周却独树一帜的说:“名者,实是宾也。”对付“实”来说,“名”是宾,实为主,名为客。主强,则客有礼,主衰,则客来欺,它们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可是众人惑于“名”,就像被狙公用“朝四而暮三”来戏耍的猴子一样,真以为换了个名字就可以得到更多橡子,循着隽誉去,就能哀求现实符合空想,抱负名实俱进。
需知,实不敷才会去求名,利过多才会受害。修身是想要有利于己,贪婪之徒却以身徇利,以至于伤身害性;立身的根本在于名声,世俗之众却以身徇名,导致名不副实。实在,修身和立身才是目的,利与名只是手段而已。梦想隽誉会让人迷失落自我,不知道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梦想财利会让人堆积隐患,不明白登高必跌重的道理。
名不副实者,平时唯恐人不知,当丑闻爆出时,却反而求人不觉;贪财受贿者,往常收取时唯恐太少,等到暴露之后,又恨收得太多。
因此,渔者对樵者说:
“是知争也者,牟利之端也;让也者,趋名之本也。利至则害生,名兴则实丧。利至名兴,而无害生实丧之患,唯有德者能之。”
“非分之福”与“本分之福”的差异樵者问渔者说:“子以何道而得鱼?”
渔者回答要凭借竿、纶、浮、沉、钩、饵六物,六物不具备,就一定钓不到鱼。但是,六物具备也不一定能钓得到。尽人力,便是使六物都能具备,之后有无鱼来食饵、钓不钓得中计,便是听定命了。明白人力与定命之分,才能理解得与失落之别。
人不能够完备决定自己是否得富贵,必待机遇定命然后得之;天不能够授予人功德,只有自己去修行才可获取。因此,富贵受定命的浸染更大,功德受人力的影响更深。知晓了这层道理,就不会患得患失落,修行在于我,是求而可得之;富贵在于天,是求而不一定得之。谁都无法决定自己能够生在帝王家,但谁都可以修身学道做贤人。故云:“积功累行,君子常分。”当定命不在我、修功累行而不得时,便是君子所说的“命”,明白这层意思便是“知定命”了。
“命”分为幸运与不幸,君子安于本分,修功累行而不得定命,便是不幸;小人非分,肆意妄为却得天所助,便是幸运。以是,我们常常觉得到,不幸便是碰着了自己本不该碰着的祸事,幸运则是碰着了自己猜想之外的福分。
君子安于本分而遇福,是他应得的;小人不安本分而逢祸,也是他应得的。故而,小人得福,则为非分之福,君子得祸,则是非分之祸。非分之福系于天,本分之福系于人,岂能不尽人力而坐视哉!
要若何去看待世间万物?
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究竟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变成了蝴蝶呢?从“归天”的角度来看,庄周与蝴蝶难道不都是“物”吗?
天生万物,人得其秀而最灵,故知人也只是一物而已。置身于人群之中,不把自己视为人,怎么去认识人呢?置身于万物之间,不把自己视为物,怎么去不雅观察物呢?执着于物我分别,然后“以我不雅观物”,则茫然而不知所得。不如从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角度来“以物不雅观物”,这样才能够究物理、察人情。
这种哲理只可融会,难以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