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约七八个月前,汪君静之抄了他的十馀首诗给我看。我从来不知 道他能诗,看了那些作品,颇自惊喜惊叹。往后他常常作诗。去年十月间,我在上海闲住。他从杭州写信给我,说诗已编成一集,叫《蕙的风》。我很歆羡他创作底敏捷和成绩底丰富!
他说就将印行,教我做一篇序,就他全集底作品略略阐明。我颇乐意做这事;但怕所说的未必便能与他的意思符合哩。
静之的诗颇有些像康白情君。他有诗歌底天才;他的诗艺术虽有工拙,但多是性灵底流露。他说自己“是一个小孩子”;他确是二十岁的一个活泼泼的小孩子。这一句自白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人格和作品。小孩子天真烂漫,少经人间世底波折,自然只有“无关心”的激情亲切弥满在他的肚量胸襟里。以是他的诗多是赞颂自然,咏歌恋爱。所赞颂的又只是清新,俏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纯挚的恋爱,而非缠绵,委曲的恋爱。
这才是孩子们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的气度!
而表现法底大略,明了,少宏深,幽渺之致,也正显出作者底本色。他不用熬炼底工夫,以是无那风雅的艺术,但若有了那风雅的艺术,他还能保留孩子底心情么?
我们现在须要最切的,自然是血与泪底文学,不是美与爱底文学;是呼吁与谩骂底文学,不是赞颂与咏歌底文学。可是从原则上立论,前者固有与后者并存底代价。由于人生哀求血与泪,也哀求美与爱,哀求呼吁与谩骂,也哀求惊叹与咏歌:二者原不能偏废。但在现势下,前者被须要底比例大些,以是我们便急迫感着,认为“先务之急”了。虽是“先务之急”,却非“只此一家”,所往后一种的文学也正有自由发展底馀地。这或足为静之以美与爱为中央意义的诗,向现在的文坛稍稍辩白了。况文人创作,固受时期和周围底影响,他的年事也不免为一个主要关系。静之是个孩子,美与爱是他生活底核心;赞颂与咏叹,在他正是极自然而适当的事。他彷佛未曾经历着那些该当呼吁与谩骂的情景,以是写不出血与泪底作品。若教他勉强效颦,结果必是虚浮与矫饰;在我们是无所得,在他却已有所失落,那又何取呢!
以是我们当客不雅观地容许,领解静之底诗,还他们本来的代价;不可仅凭成见,论定是非:这样,就不辜负他的一番心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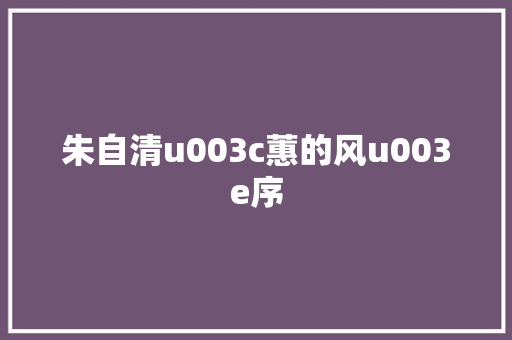
1922年2月1日,扬州南门禾稼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