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词评家普遍认为,苏轼词“疏狂”多于“豪放”,而辛弃疾才是真正的豪放派。然而,若论二人造诣最高的豪放词作品,辛弃疾词还是败给了苏轼词,这是怎么回事呢?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辛弃疾在六十六岁时,写下的压轴之作。而《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是苏轼四十七岁时,写下的豪放词代表。
当代学者王兆鹏、郁玉英依据当代传播学研究方法,比拟了大量宋词名作在宋、元、明、清四朝,进入选本的次数、唱合次数和搜索数据。
然后,得出一个影响力排行榜: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连前十都进不了。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却在宋、元、明、清皆为“第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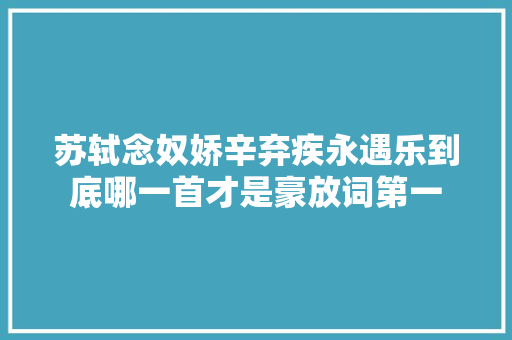
因此,《念奴娇·赤壁怀古》才是“宋词第一名篇”。不过这只能解释《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影响力大,却并不能证明它比《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更加豪放。
《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豪放,表示在作者对面前的景物,以及三国沙场的描写上。
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豪放,则表示在作者对风云变幻的历史的浓缩,对历朝北伐战役成败的反思,以及本人的廉颇之志上。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思想深度与广度,明显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之上。不过由于用典太多,大大地影响了作品的传播力,在抒怀方面是不及苏轼词的。
一、《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成败皆在“用典”上《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宋·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骚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平凡巷陌,人性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顾,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口语翻译:
江山千载,景致依旧,雄踞东南的孙权,却不知哪里去了。历史就像是一个大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旷世豪杰的风骚余韵,全被雨打风吹去了。
斜阳照在芳草、碧树上,那里有一条平凡的小巷,传说是南朝刘宋武帝刘裕住过的地方。想当年,刘裕两度挥师北伐,金戈铁马,气吞万里,收复了黄河南面大片的故土。
他的儿子宋文帝,也想像他老子刘裕一样北伐中原,“封狼居胥”。结果却由于草率出兵,落得一个两淮失落守,胡马饮江的了局。从此往后,南朝人只能仓皇北顾,满目哀伤。
我南归已经四十三年了,回望过去,依然还记得当年的扬州路,曾经是烽烟沙场。往事不堪回顾,转眼间,百姓们已经在异族的祠庙里,烧起了喷鼻香。
又要打仗了,朝廷到底会派哪一位老将出征呢?谁又会来问:廉颇将军已经老了,他的饭量到底如何了?
辛弃疾这一首词是他晚年的集大成之作,用典已经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词的上半阙中,辛弃疾先引出东吴孙权与南朝刘宋武帝刘裕的典故,表达出了自己北伐的志向。
而不才半阙中又连用“元嘉草草”、“封狼居胥”、“狒狸祠下”等典故,深化了词作的内涵,透露出了对韩侂胄草率北伐的深深担忧。
刘义隆“元嘉北伐”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如今南宋的公民过惯了安逸的日子,军队想必也没有什么战斗力。在这种情形下选择北伐,风险非常大。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当年在率军南侵时,在瓜埠山上建了一座行宫,后来被改成了寺院。由于他的小名叫“佛狸”,以是百姓就把这里叫“佛狸祠”。
南宋的百姓们安逸的生活过得太久了,早就遗忘了那段惨痛的教训,居然跑到以敌酋名字命名的寺庙里,大搞敬拜活动。
这些典故,都表示出了辛弃疾对“开禧北伐”准备不充分的担忧。可是只管如此,辛弃疾仍旧希望,朝廷在选定大将的时候,能够考虑到自己。
这位六十六岁,半截入土的老将仍旧抱有这样的心思,才是真的豪放。不过由于这首词用到的典故的确太多了,在普通读者中间传播就很吃力了。
二、《念奴娇·赤壁怀古》“泄了气”却仍旧火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北宋·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骚人物。故垒西边,人性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比拟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再来看苏轼这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你会创造,这首词的用语十分浅近,险些不须要口语翻译,如今的人就能够看懂。
这首词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写景,并且还做到了情景交融。由于开篇便是滚滚长江向东流,磅礴大气的场景。
那千古的风骚人物,像一粒粒砂砾被浪花淘尽,剩下来的则像金子一样平常闪耀着光芒。那是谁呢?那是三国期间,东吴的都督周瑜。
随着,苏轼就开始描写,自己想象中的赤壁古沙场。那赤壁是一处怪石嶙峋的地方,奇石穿云,惊涛拍岸,发出万马奔驰似的雷鸣。
波涛激荡,拍打在岸边,仿佛堆起了千层雪,这是多么地动魄惊心啊!
就在这样一幅画卷之中,呈现出了多少的英雄豪杰。苏轼在这首词的上半阙中,基于自己想象的细节描写,堪称是出神入化。而下半阙里又从周瑜、小乔这一对英雄美人的结合入手,刻画了一个足智多谋的漂亮儒将形象。
最妙的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句话略过了战役场面的描写,仿佛古龙小说中写“小李飞刀”,既突出了它的快,又突出了它的轻巧,正是“无招胜有招”。
但是,这首词到了末了却“泄了气”。由于苏轼在词的末了溘然拐了一个大弯,说他自己只是在“故国神游”,发梦罢了。
并且他看着自己头上已经涌现的白发,创造征战疆场,美人在怀的梦想,早已经不属于他那个年纪了。这所有的东西,不过是他在“自作多情”罢了。
苏轼这首词写于“乌台诗案”后他的人生迁移转变点上,以是也难怪他会“灰心”。由于前面的“故国神游”写得实在是太浪漫了,符合大多数人的想象,以是“灰心”的地方,也就忽略不计了。
结语比较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与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的词显得沉郁抑扬,思想内涵比后者更为繁芜,可惜太过于理性了。
这可能是由于,辛弃疾当时已经是六十六岁老人的缘故。辛弃疾只管生平都热衷北伐,但是他并不主见贸然用兵,以是他在词中表达了很多繁芜的思考。
在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六十六岁的辛弃疾又一次复出了,不过这只是由于当时的宰相韩侂胄想拿他当幌子,替主战派助势而已。
后来,韩侂胄创造辛弃疾和自己根本不是一条心,又很快把辛弃疾赶走了。辛弃疾内心愤怒不已,直接写诗大骂对方:“叶公岂是好真龙!
”苏轼写《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时候,思想还很纯挚。由于当时的他虽然已经四十七岁,也不算年轻了,但是毕竟他的前半生一贯都过得非常地顺利。
而到了黄州期间,苏轼终于走出了自己的“天真”。他借着《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来回顾了一下自己在壮年以前的民气抱负。
由于苏轼在这首词中用的是国人最喜好的三国故事,以是群众根本非常广泛,再加上措辞也浅近易懂,内容中既有征战疆场的豪情,又有英雄和美人的结合,的确是非常有传染力。
因此,苏轼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传唱程度,远超辛弃疾那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至于苏轼词末了“漏气”的那极小一部分,则完备可以忽略不计了。
那么,这两首传世名篇,到底哪一首更加豪放呢?我只能说,“豪放”实在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办法而已。如果单从这一方面理解,那么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确实更胜一筹。
至于辛弃疾,他的豪放不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上,也不在于他其他的诗词上,而是在他自己的身上。由于,他早就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豪放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