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视频网站上有一个很播放量很高的视频,该视频将一年来热门歌曲以串烧的形式来了一次大盘点,30首一口气听完,每首歌中的成名句确实韵味十足,很好听。
该视频的歌曲串烧从一只白羊演唱的《赐我》“我彷佛独自站在那三尺红台,等你来为我喝一声倒彩”开腔;依次出场的有盛哲《在你的身边》“我以为忘了惦记,而面对夕阳希望你回到本日”;梦然《是你》“满是骄傲的面庞,是光融不掉的冰花窗,是你、是你、身后的青春都是你”;曹雨航《江湖之间》“儿女情长仿若昙花,逃不过相忘江湖之间,忘不了惊鸿一眼,独自卷帘望寒星几点”……
实在,将歌词联唱称为串烧是一个特殊贴切而形象的称谓。串烧,本是指将肉类、海鲜、蔬菜等食品串成一串进行烧烤,成为一种食品类型的名称。将这个饮食行业的词语移植到别的领域里,涌现了歌曲串烧、铃声串烧、资讯串烧等词语。
而歌曲串烧呢,便是将不同种类的歌曲、铃声、资讯等取其精华部分串在一起,组合起来,使人们在一段韶光内听到不同风格、种类的歌曲、铃声、资讯等。个中,歌曲串烧类似于以前的歌曲联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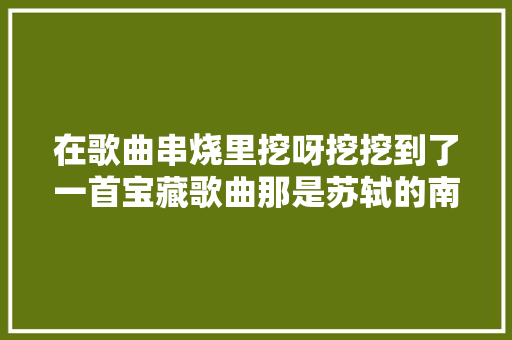
如果你以为歌曲串烧是当今才盛行起来的一种时尚演唱办法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实在呀,歌曲串烧并不是当今才有的一种演唱办法,这种形式古代就有了,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移植征象了。
在古代,它还有一个特殊好听的名字,叫集句。所谓的集句,便是选取古人已经创作出来的现成句子,然后进行二次创作。将古人现成句子进行整理、汇编,写成一篇新作品,这样的创作方法叫集句。
集句本是古诗中的一种文体,也叫集句诗,词也是一样的道理。说白了,集句诗本身便是二次创作的过程。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七》中考证,西晋文学家傅咸的《七经诗》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集句诗:
集句,始傅咸。傅咸有《回文反复诗》;又作《七经诗》:其《毛诗》一篇,皆集经语。是集句所由始矣。
宋代盛行诗词串烧集句诗在我国文学史上是由来已久的一个传统。到了宋代,集句诗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从北宋石延年、王安石、苏轼到南宋的文天祥,都喜好创作集句诗。
文天祥在燕京狱中曾经将唐代墨客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成诗。他的《集杜诗》二百篇最为著名。文天祥的集杜诗是具有独立文学代价的创作,情真意挚,意境完全,如出己手。文天祥以诗为史,写出了宋亡前后的历史过程,并且在诗作中渗入了自己的感想熏染。
王安石也非常喜好集句诗,《招叶致远》一诗便是王安石集句诗中的一首代表作,这首集句诗里的句子全都出自古人诗句,却被王安石信手拈来,串烧成篇。如果不细加考量的话,很难相信这是一首串烧诗,由于四句诗的诗意贯通,反而倒像是王安石的原创诗歌一样。
王安石不仅爱创作集句诗,还首开集句词之先河。南宋词人吴曾在《能改斋词话》卷二中写道:“王荆公(王安石)筑草堂于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叠石作桥,为集句填《菩萨蛮》云:数间茅屋闲临水……”
集句词涌现于宋代的缘故原由很大略:创作集句词的紧张词人,便是推演集句诗风者。这也反响了诗坛词坛相互影响,以及宋代诗词创作者“以诗为词”的一个侧面,也足以解释集句的涌现是词体向诗歌靠拢的一个表现。
宋代文人在集句诗词创作中盛行用典、隐括、集句和古人韵等法度模范,但不同的人对这种创作方法持有不同的不雅观点,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宋代文人墨客集句作词紧张有两种形式:“五、七言体”与“杂言体”。个中以五、七言体集句时,一样平常多用《生查子》《浣溪沙》《玉楼春》《菩萨蛮》《南乡子》等篇幅短小而且形体整洁的词牌,集句大多为唐代墨客的五、七言诗句。
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不敷而道的技巧,不过是对已有诗词句篇的汇编、词句的堆砌,是从他人的诗词作品中摘章断句的技巧,没有什么创新。
但有的人却认为这是一种很高明的创作手腕,这一类创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古为今用、以故为新的方法,长于早年人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并且是对传统文化的继续,是对古人创作的认同和接力。当然这样的不雅观点是正面的,也是肯定的。
有了这样的创作氛围和创作履历,大批的文人雅士都不谋而合地加盟到集句创作团队中来,而苏轼更是集句诗创作中的高手。
作为文坛巨擘,苏轼喜好“以诗入词”,他对历代诗歌都有所阅读,对当时盛行于文坛的集句诗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为此写成了三首《南乡子·集句》,个中第二首不得不提一下,由于这首词中的句子都是出自唐诗,且每一句都来历非凡。
可以说,苏轼的这首《南乡子》是一首超一流的串烧歌曲,由于宋词便是宋代的盛行歌曲。一起来看一下苏轼创作于黄州期间的词作《南乡子·怅望送春杯》,原词如下:
怅望送春杯。渐老逢春能几次。花满楚城愁远别,伤怀。何况清丝急管催。
吟断望乡台。万里归心独上来。景物登临闲始见,徘徊。一寸相思一寸灰。
苏轼的歌曲串烧,每一句都有来头既然这是一首集句词(歌曲串烧),就有必要说一下每一句的来源和出处。
闲补一笔,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师长西席在《论再生缘》里说:“苟无灵巧自由之思想,以利用贯通于其间,即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去世句。”
由于好的集句诗词在创作过程中,单从难度、音韵等方面来说,并不亚于一首原创诗词的难度,加之在古代没有搜索引擎的赞助下,靠人的影象将历代诗词名句储存起来,并做到精准检索,这本身便是一件难度系数很高的事情。
而苏轼却出人意料地做到了,以是说,如果将陈寅恪的这段评语利用在苏轼的集句诗词中,亦不失落为切中肯綮的评价。如果按照现在的乐坛标准曲衡量的话,苏轼毫无疑问会斩获歌曲串烧达人的称号。
好了,走进苏轼的这首集句词,开篇句“怅望送春杯”,出自唐代墨客杜牧的《惜春》诗,杜牧原诗写道:怅望送春杯,殷勤扫花帚。谁为驻东流,年年长在手。
苏轼在开篇句中直接采取“怅望送春归”,词作为何以这一句开头?实在便是为了点明了词人对酒伤春的情境。
起笔充满惜春的忧伤感。词人痛惜凝望动手中的这杯酒,这是一杯送春归去的酒,也就自然而然地撩起了词民气中比酒更浓的伤春之情。
在宋代词作中,抒发词人惜春伤春的作品不胜列举,如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如秦不雅观的“清闲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再如贺铸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都是蜚声文坛的千古名句
由于在文人墨客心中,春天是美好事物的代表,而春天的流逝也代表着美好事物的逝去,这难免会引起文人墨客的伤春与惜春之情。
第二句“渐老逢春能几次”,出自唐代墨客杜甫的《绝句漫兴九首》,杜甫原诗写道:仲春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次。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杜甫此诗是流落成都时所作,诗中抒发了春光易逝,岁月催人老的情绪,他将自己的情绪寄托在一杯酒中。
渐老,饱含着年光时间易逝的悲哀语调;逢春,则是在悲哀中透出的一丝喜悦;能几次?又是悲哀的情绪。杜甫在诗中不仅仅只表达了一种悲哀的情绪,非但一悲,墨客将逢春的喜悦也一并化为悲哀。一句之中一波三折,笔致淡宕苍老,情绪沉郁抑扬。
苏轼在第二句之以是采取杜甫的诗句,同样是词人对伤春之情的直接抒发。由于伤春,由于感叹岁月流逝,进而引起词人对春光易逝、岁月催人老的伤感之情。
苏轼此处采取杜甫的诗句,也是颇有一番用意的:一是反照了第一句的“怅望送春杯”,二是对自己因“乌台诗案”而贬谪到黄州后的心情写照。
苏轼在黄州时,写有《安国寺寻春》一诗,诗中写道:“看花叹老忆年少,对酒思家愁老翁。”这两句诗也反响出了苏轼在初贬黄州时的心情,也可以和“渐老逢春能几次”相互印证。
此时的词人正有一种看花叹老、对酒思家的心绪。
以是下句就写到了“花满楚城愁远别”,这一句取自唐代墨客许浑的《竹林寺别朋侪》诗,原诗写道:花满谢城伤共别,蝉鸣萧寺喜同游。前山月落杉松晚,深夜风清枕簟秋。
许浑的原诗句只是纯挚地抒发伤春惜春之情。苏轼在这首集句词里采取这一句,是非常符合词人此时此刻的心境的,这一句也与词境的意蕴很契合。
由于当时正值春天,黄州正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时令。这样的时令也正是花喷鼻香满园的景象。楚城,在这里指的便是黄州,由于黄州在古代属于楚国。“楚”字在传统文化中是具有双重含义的,它既是一个地理名词,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意象。
带有双重标签的“楚”字常常涌如今唐宋期间的诗词作品中:如刘禹锡的“巴山楚水悲惨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如李白的“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如柳永的“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再如张炎《解连环》中的“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等,这些带有“楚”字意蕴的诗词名句不胜列举。
苏轼初贬黄州时的生活是艰辛的,他处境困难,举目无亲,以是也就格外地思念家乡、思念亲人,加之贬谪的经历,他的感情很低落。
面对此情此景,词民气中的愁绪是深奥深厚的,当花满楚城之际,更是令人触景生情、触目伤心。而将这样繁芜的感情表达得最深切的,便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不雅观,他同样由于贬谪的境遇而写下的词作《千秋岁》中,就有“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的凄婉表达。
实在苏轼和秦不雅观的境遇是相似的,而秦不雅观的这句“飞红万点愁如海”恰好可以成为苏轼“花满楚城愁远别”的注脚。苏轼采取许浑的这句诗,情境是非常真切的,贯入词人贬谪经历的这一深层意蕴,让人隐然感到词人的各类心绪,以是苏轼的用意与许浑原诗句中伤春伤别的诗意就有着寰宇之别了。
接下来的“伤怀”二字,言简意赅,韵味十足,看似大略的两个字分量綦重,蕴含着词人此时此刻的临老逢春、远别等各类痛楚的感情。上半阕也只有这两个字不属于集句,而是苏轼自己的话语,这样的表达进一步将所集唐人的诗句融为己有。
上片末了一句“何况清丝急管催”,出自唐代墨客刘禹锡《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一诗,原诗写道:目前无意诉离杯,何况清弦急管催。伤心人别有一番凄婉的心境,更何况宴会上清丝急管的音乐让民气乱如麻,以乐衬哀只能加重当事人难以为怀的悲哀。
北宋词人周邦彦的《满庭芳》一词里有这样的几句:“干瘪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细品苏轼和周邦彦这两首词作中的句子,词意是相似的,但苏轼的这句在表述上明显深婉哀痛了很多。
据宋代词话条记中的记载:“东坡来黄州,二君(指太守、通判)厚礼之,无迁谪意。君猷秀惠列屋,杯觞盛行,多为赋词”。苏轼词中写到的酒筵上的丝管之声,是黄州太守为苏轼所设。
过片开头,词人着力写思乡之情:“吟断望乡台”,这一句取自李商隐的《晋昌晚归立时赠》一诗,原诗写道:征南予更远,吟断望乡台。
苏轼在词作中虽然采取的是后一句,实在也暗含了李商隐诗中上一句的诗意。苏轼生平仕途跌宕起伏,贬谪的足迹踏遍千山万水,但对故乡的思念始终如一。
苏轼在《醉落魄》一词中就写道:“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这正是苏轼思乡情结的深情流露,回归故里,归隐山林,寄情山水,成为了萦绕在苏轼心头,生平挥之不去的情结。
苏轼贬谪黄州,阔别故土,当饮酒登高之际,又怎能不思念故乡?那一刻,他的乡愁愈加浓郁起来,以是接下来词人纵笔写出“万里归心独上来”。这一句也出自唐代墨客许浑的《冬日登越王台怀归》一诗,这是一首七律,原诗前四句写道:月沉高岫宿云开,万里归心独上来。河边雪飞扬子宅,海边花盛越王台。
词人此时虽然身处筵席的歌舞宴乐之中,但还是少了一份归属感,大有“独在异域为异客”的孤独感。贰心系故乡,归心似箭,当然在宴会上的其他人是不明白词人的心境的,又有何人会明白苏轼此时此刻的登临之意呢?“独”字突出了词人身处黄州的那一份孤独感。
苏轼在黄州期间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种强烈的思乡情结,在《侄安节远来夜坐二首》诗中,苏轼写道: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
一诗一词,诗词互照,诗词中流露出来的是相同的情绪,诗意词意也是同样的哀婉深奥深厚。行文至此,苏轼心中那种由于贬谪而表现出的痛惜无望之情愈加强烈起来,词人无可摆脱的迁谪意识,不才一句中进一步流露出来。
下句“景物登临闲始见”,出自唐代墨客杜牧的诗作《八月十二日得替后移居霅溪馆因题长句四韵》原诗写道:景物登临闲始见,愿为闲客此闲行。
杜牧的诗句很高妙,高下两句,“闲”字就涌现了三次。苏轼借用杜牧的这一诗句是很有深意的,这不仅表现在诗意上,更表现在作者的心境上,个中又暗含了苏轼自己的情状。这一句既起到了衔接高下文的浸染,又在整体年夜将词义交融贯通起来。可谓衔接奥妙,过渡自然。
苏轼登临高处,纵目远眺,春天里的美好景物,此时被他看得真真切切。这一句从表面看,彷佛只是用来写景,细品之下还是蕴含着词人省察自身的意味。“闲”字,饱含了自己遭贬谪无可作为、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痛楚心境。
苏轼在黄州写过一首蜚声词坛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名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抒发的正是词人空想落空,空想与现实差距如此之大的感慨。
而“景物登临闲始见”一句正是词人对无可作为的痛楚与愤懑的深切哀叹。然而,此时词人又能如何?他也只能“徘徊”了。“徘徊”二字,同上片中的也“伤怀”一样,不属于集句,而是苏轼自己的话语。
词作此处涌现“徘徊”二字,蕴藏着很多层面的信息,暗示着词人此时心态由外向转向内向。由于接下来词人重点写了生理活动,是词人反不雅观内心的过程,以是“徘徊”二字在行文上属于一个过渡句。
词人辗转徘徊,情绪无法宣泄,无法抒怀,以是他反思内心,得到的结果却是“一寸相思一寸灰”,词作就在这样深婉哀怨的语调中结束了。苏轼这首集句词的结尾采取李商隐《无题》诗中的名句,情绪饱满,苏轼彷佛将所有的情绪都集中在这一句,表达也就很沉痛了。
“一寸相思一寸灰”这一千古名句,出自李商隐的《无题》诗,原诗里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情绪表达,是李商隐写失落意的爱情的,这种失落意的爱情中又常常融入墨客的某些出生之感,在相思成灰的爱情感慨中也可窥见李商隐仕途的失落意和人生境遇。
苏轼在黄州是若何的一种的心境呢?有一首诗可以解释一点,他在《寒食雨二首》的结尾中写道:“君门深九重,宅兆在万里。也拟哭途穷,去世灰吹不起。”苏轼在黄州处境困难,生活悲惨,这长歌当哭的诗作《寒食雨二首》,是苏轼对郁结在心头的无限惆怅的宣泄。
纵不雅观苏轼的这首集句词,实在是词人在黄州心境的写照,而他在黄州创作的《寒食雨二首》的结笔句,则可以很好地表明这首集句词的内涵。苏轼仕途跌宕,阔别故乡、亲人、朋友的孤独,这两种情绪,在此时此地是一样的深婉哀痛,这首集句词深刻地反响了苏轼当时心态的一个侧面。
从全词的构架上来看,全词起笔于酒筵,中间写登临望乡,结尾是对“一寸相思一寸灰”的深入反思,词作完全地呈现出词人的生理活动过程,这齐心专生理活动从向外不雅观照发展到反不雅观内心。这是词作内容上的一大特色。可见此词呈现反不雅观内心的特色不是词人刻意为之的,也不是出于有时的。
同时,在这首集句词所采取的唐人诗句中,句句相符词人谪居黄州的情境与心境,经由词人创造性地交融贯通后,这首集句词焕然成为新的篇章,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已不仅仅是一首纯挚的“笔墨游戏”的集句之作了。
小话诗词
苏轼集唐人诗句谱写新词,奥妙自然,信手拈来,词作浑然天成,读来犹如词人自己创作的新句子一样,这又是全词的另一特色。东坡在黄州期间还写过《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在个中一首中,苏轼自满地写道:
世间好语众人共,明月自满千家墀。
……
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当令君丧魄。
乃至在诗中,苏轼对他的集句作品还有这样的自我评价:“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千章万句卒非我,急走捉君应已迟。”
由此可见,苏轼对付自己从前人诗作中集句创写新词的是非常自傲的,苏轼自傲的实在便是自己信手拈来、交融贯通的创作能力.
而这首名为《南乡子》的集句词无疑是苏轼集句词中的代表作品,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苏轼学识的渊博,也能看出苏轼创作的自由灵巧度和写作手腕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