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实在有点儿深了。儿子她娘,比来严重失落眠,此时,居然发出了均匀的鼾声。我近晌也难得有一时之宁静,心想,出去涣散步吧。
暮春,景象回暖,山花烂漫,万物清醒,但晚上室外还是有些许凉意。我披了件罩衣,拿了手电,轻轻地掩关着厅门,但,门还是发出了长长的“吱”声。
乡下,现大搞“俏丽村落庄”培植,太阳能路灯照得乡间主道通明。傍晚,乡民们喜结伴于灯下硬化了的乡间公路上闲步炼身,谈天谈笑,呈显一派国泰民安,盛世繁华之景。我独喜一人于僻静处溜达,尤爱在树影婆娑,光影斑驳之月下,仰月思古,忆昔怀旧。
我是个依山而居,伴水而长的乡下人。屋前的峡水湖,深深地刻录着我儿时足迹,地坪右下首沙地,是我儿时爱玩耍的地方,好久没去过了,此时,溘然想去那走走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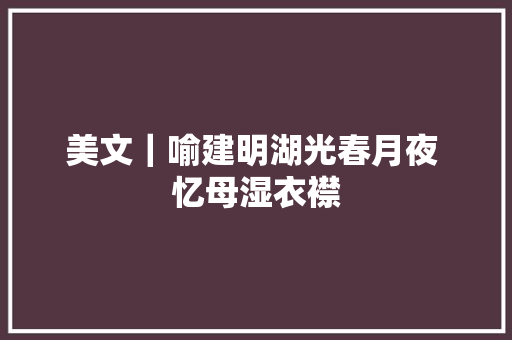
转身开门,回至屋内换了双套鞋。重出门,过前坪,开始下坡,路灯已难照射。在路灯下,未感玉轮之明,一到暗处,顿觉皓月当空,繁星满天。我打动手电筒,小心翼翼,恐怕草地上溘然钻出草绳似的动物。
手电灯光下,足边浅水处,微波粼粼,鱼嫩嫩和细虾虾在尽情嘻戏着。近处草丛中的虫鸣和对岸的蛙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曲美妙的乐章。不觉走到了“地皮神”旁,这地皮神上面是枫树丘,下面叫地皮丘,当然,枫树丘现已填土变成了公路。两丘田高下的高度差约有五六米,这五六米的落差中,有块沙土,这沙土土质是面沙型,便是很细很细的那种白沙。
地皮丘属水亩,常年被淹,枫树丘虽也属水亩,但在我影象中,几年都难淹一次,而这块沙土,每年要被淹没三四个月,即春夏涨水时。每当夏未水位低落,峡水湖边就现出了一条洁白的“玉带”,玉带把湖水与岸边树木花草隔开,像是牢牢地缠绕着湖面,玉带上以细沙为主,实际便是小沙滩。这块土的细沙,平均少石,坐在这细沙上,有种柔滑松软之感。这沙土中间以前还有块大石头,下面部分深深镶嵌在沙里。如今这湖以养鱼为主,蓄水常深,本日的水位,刚好淹没了这块沙土。
“嗙!
嗙嗙!
嗙……”溘然,远处传来了这种嗙嗙声,彷佛很有韵律。这种声,我似觉非常熟习,到底是什么声音呢,我一时又想不起,只知汇入今晚这美妙虫鸣蛙声中,很是和谐动听。月光下,悄悄的湖面,倒映着的山峰和玉轮,朦朦胧胧的。我丟了块小石,湖面激起了荡漾,水中的山形和月影,在如银的明月下,随波浮沉,伸缩晃荡,变得更模糊了,但彷佛富有了活气和活力。今晚景致极美,我索性坐在身旁一块石头上,这石头大概这天间钓鱼翁的座凳,上面还垫了层厚纸壳。
望着水中起伏的倒影,脑海中现出了我儿时的一幕幕。很爱卫生的我娘,换洗出的衣服一样平常不过夜就要洗涮,而因白天要出集体工,故常常晚上在这地皮丘边捣衣,娘每次总是要我提着镜灯,来作伴壮胆。哦!
我想起了,这亲切的“嗙嗙”声,很像我娘用木杵拍打衣服的那种捣衣声。
若是明月高悬的晚上,娘捣衣的幽美姿势,可看得清清楚楚。娘蹲在水边,上身和头稍向左侧偏斜,右手握木杵捶打着衣裳,捶打十来下,左手就拿着衣衫往水中一拽,动作麻利洒脱,接着又放木凳上拍击,发出有节律的“嗙嗙”声。我则在这沙土上玩细沙,或躺在大石上仰望天宇,数星赏月,异想天开。也喜好在明月下,往水中打漂漂,那石片或瓦片在月下湖面弹跳着向前飞漂,甚是好看。
我娘,姓刘名雪英,一九二七年生于贫苦之家,两岁时被抱养至殷实的大户人家。娘读过几年学堂,羊毫字写得算好,在那个年代的乡下,是算得个能“文”女子了。娘容颜靓丽,卫生精细是远近出了名的,至今都有人提及她,是像某个某个女名星,那时节,打抬硪都拿我娘的仙颜作号子唱,还说我家的梭筒钩都是擦得亮光光的,地上干净得是人都打得滚滚。
也确实,我娘皮肤白皙,姿容清秀,气质优雅,就连病入膏肓,卧床不起时,亦有“黛玉”之美,独具其魅。听说我娘在外家做女时,不乏富贵求婚者,而我那士绅外公却偏偏选了我父亲这个穷诗人。我娘还是个多面手,饭菜做得好,花也绣得美,做的布鞋优柔适脚样子容貌好,连手工打个补丁都是缝线均匀,形状大小彷佛恰到好处。
娘终生未生,四十岁时,抚我为儿。娘爱我疼我赛过亲生,我十来岁了,娘还抱着我亲,喊“满伢子”,唤“心蒂根”(方言,意为心肝宝贝)。我在宁乡六中读高中时,娘随我父住大田方华锋桥小学,学校建在半山腰。每逢周六下午,娘就早早站在小学下首的田埂上,举目眺望着我回来的方向。一样平常,我走到了离小学直线间隔也有近三华里的擂钵塘,转过那路边屋角,就可了望到我娘站在那田埂上的朦胧身影。
当我快到小学的山下响水坝时,娘就下得山来,往前走一两百米来接我。离很远,我就挥手喊娘,娘亦亲切地边应边呼满伢子。每次接到我后,娘高兴得真是喜笑颜开,满面东风。娘总是要先站着看看我,尤喜好摸摸我后脑,且关怀地问这问那,有时乃至还要牵着我手走一段,彷佛世上就她的崽最可爱似的。
娘无其他嫡亲,该当说,我便是娘的唯一精神寄托,娘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我身上。晚餐,娘总要费尽心机弄点好菜,常常是几两肉,加几个荷包蛋,我知道,父母平时是舍不得吃的。晚上睡时,娘还要进我房间问寒问暖,坐我床边,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我曾对娘说,我肯定考不上大学,因我的英语一窍不通。而娘安慰道:“崽呀,虽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读书也不是唯一的出路呀!
只要身稳手稳口稳,人生处处好安身。考不上,娘不会怨你的!
”
周日下午返校时,娘还要给我炒一罐头葫芦鸡蛋带上。而每欲动身时,便是我不想挪脚的时候,更是娘不舍的时分,每次总要拖延到必走不可了,才依依不舍地移步动身。娘则要送我一两百米途,千打发,万叮嘱。而后,娘返回,竟又站在那田埂上,一贯目送着我,我频频回顾,常常见娘在以衣拭泪。我已走到了一个两百来米长的转弯处,娘实在已看不到我了,但娘还站在那眺望着,因我走出这大弯后,有几十米远的路段,娘还可隐约望得到我。当我到了擂钵塘,又转了那屋角,娘已完备望不到我了,但我常躲着看,见娘还呆呆站在原地,举目远眺着我这方向,要好大一会,娘才缓缓转身返回。唉!
此情此景,我常忆常堕泪,然而,纵有千行思母泪,怎及娘亲念我心?
不管寒来暑往,括风下雨,娘都是如此迎送,除非是娘病了或遇极恶劣景象。烈日的夏天,娘撑着一把洋伞站在那高处,遥望远方,盼儿早归,这应是人间间的一道靓丽风景!
尤其冬天,寒风冽冽,娘腰间系块黑围身布,双手用围身布裹着,站在田埂上,目送我的姿势,好幽美,好伟大啊!
娘如此迎送我,也真是折煞我也!
我曾多次对娘说过,真别这样,可娘便是坚持着,每次,娘都是慈祥而带幸福感地看着我,以“嗨嗨”轻笑回答着。我知道,娘对我的所有爱,全部溶化在这“嗨嗨”笑声中。
那时,娘的乳房模糊作痛,由于我读书,百口只靠我父微博人为,已至负债,故娘仅在流沙河镇上吃了几副中药。直到八三年春,我代课教书时,才带娘去长沙检讨。一查,竟是乳腺癌晚期,真是晴天一声霹雳,我果断借钱,给娘在长沙做了切除手术。
八五年,我已弃教回家养长毛兔,这时,娘的癌细胞已扩散,致全身疼痛难忍。那时的止痛药难买,娘痛得以手扯发,指扎床沿。几十年了,这床沿我一贯留着,床沿上,指甲印痕至今还清晰可见。尤其是娘的胸部已有硬梆梆的肿块,更是又闷又痛,我坐靠床档,抱着娘,给娘抚摸。有时娘痛晕靠在我怀里,我也累得抬不起眼皮,垂手睡着了。
娘因吃多了西药,导致大便秘结,多天不通便,娘胀得无法忍受。我给娘买了果导片,还在五妽家讨了些芝麻油给娘吃,都没下得动。娘是胀痛得在床上翻来滚去,见娘如此痛楚,我心疼得堕泪,但也只能干焦急,年迈的父亲也是措手无策。我鼓着勇气对娘说:“娘,我用手指给你掏吧!
”娘摇头,我做了几次事情,娘应是实在难熬痛苦了,也就用那无助而显抵牾的泪光望着我,无力地点了下头。
二十来岁的我,还未谈婚,且上无姐,下无妹,父亲又年迈。望着娘亲如此痛楚,心想,娘自己未生,一把尿一把屎地带大我,本日伺候娘,不靠我又靠谁呢?我也不能避讳什么了,为了减轻娘的痛楚,我把指甲剪了,用两床棉被折好叠加,上面再铺了床烂被单,搂着已骨瘦如柴的娘爬负在上面,把一只盛了点水的便桶放在床边。等统统准备好了,从背面褪下娘的裤子,我右手凃了些芝麻油,然后用右手食指逐步插入娘的肛门,钩着大便往外掏。
一粒,两粒,三粒……娘的大便全是一粒一粒的了,由于秘结韶光长,已奇臭无比,真的臭得使我有点受不了,我只好返脑在稍远处吸口气,再闷着气给娘掏。我每取出一粒,娘就无力地轻“哼”一声,细声道:“崽呀,舒畅,我舒畅多哒。”一粒一粒地取出了一些,寡言少语的老父亲,站在床边“啧啧”着,说了几声:“崽呀,真难为你哒!
”从此,只要娘胀痛得难熬痛苦了,我就如此给娘掏,后来还总结了履历,实在指甲不能太短,只是要磨得调皮。 看着娘减少了一点痛楚,我亦如释负重。娘在床上常流着泪,断断续续说:“崽呀,我晓得我时日不多哒,我最不放心的呢,便是你还冇讨堂客。”还多次说:“你会有好报的,我会给你送胖子崽,送胖子孙来的。”这是我娘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如今,我常对我儿孙们说:“你们都是我娘送来的。”
为了宽娘的心,我曾在屋外路边,约请了两位慈眉善目的陌生老者,解释缘由,请他俩假扮民间名医,为我娘“看看”病,“骗骗”她。两位过路老者听明缘由后,点头称我是“孝子”,且来到床边,望闻问切,像模像样地“演”得非常逼真,让娘也真高兴了一回,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心中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火花。
八六年正月,娘已处于晕厥状态,至大小便失落禁。老父亲合营着我,给我娘改换擦洗。换下的裤子,我穿着套鞋,便是在面前这地皮丘水边洗涤,这儿,也是我娘曾经捣衣的地方……
呜呼!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一晃三十六年矣。娘!
我若有来生,还要做您的“心蒂根”。
泪眼模糊,衣襟已湿,起身仰望星空,曾经照着我娘捣衣的玉轮,已渐西沉。耳边蛙声依旧,虫鸣不断,唯有那“嗙嗙”声已听不到了,大概是永久听不到了啊!
作者简介
喻建明,网名:桃花居士,宁乡市老粮仓镇峡山水库人。常居宝庆府,偶写小文章。
[责编:胡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