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是古代文学史上的宝贝,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诗词的形式多元化发展。有一种诗文构造很奇妙,利用汉语词性的变革,在顺序上回环往来来往,正反通读皆可,在文学上称其为“回文诗”。
关于回文诗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最早是苏蕙的《璇玑图》,正读、反读、斜读可以解出七千多首诗词;也有人认为回文诗最早的雏形是西晋初期的苏伯玉妻的《盘中诗》。这种诗词文体构思奥妙,后世很多人争先效仿,就连苏东坡,纳兰容若等才子也乐在个中。
璇玑图
回文诗究竟是一种纯挚的笔墨游戏,还是有其独特的艺术代价?情书君以宋朝一位不有名墨客李禺的代表作品《两相思》为例,和大家一起分享回文诗之美,阐发其文学代价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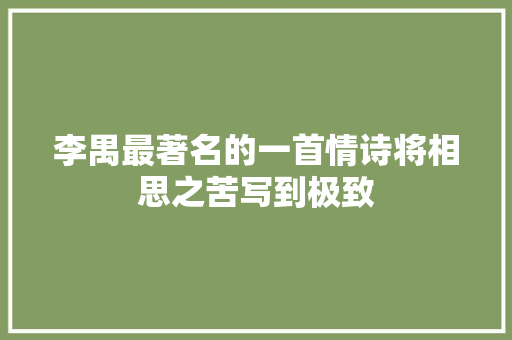
《两相思》
宋•李禺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去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寂寞,夫忆妻兮父忆儿。
情书解诗:李禺是宋朝一个很低调的墨客,不显山不露水,他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头衔,史籍上对他的记载也特殊少。但他这首《两相思》却可称千古绝唱,后世无人能及。
这首诗描写一位丈夫思念妻子,山水路遥,许久未曾相见。思念涌上心头,想用酒浇愁却又怕很快就把酒喝完了,想要落笔写封书信,却又不知从何提及。人离去,锦书难据,在这孤独寂寥的夜里只有无尽的思念。
这首诗无论是格律还是韵律,遣词造句都用的很精妙,将一个丈夫思念妻子的心情跃然于纸上,可谓是将相思之苦诠释到了极致。
如果说单看这一首诗,在古代文坛上并不能算刺目耀眼夺目的名篇,不敷以让李禺名垂千古。这诗奇妙的是,倒着读便是另一首诗,诗词意境大不同,且丝毫没有违和感。
《两相思》
宋•李禺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羽觞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李禺的这首通体回文诗,构思新颖,遣词造句之间彰显独特风格,倒着读便是一首思夫诗。无论从诗词格律韵律还是诗词表现的张力来看,倒读的这首诗都堪称情诗中的佳作。全诗写出了一位闺中的妇人对丈夫的思念,永夜漫漫,无心就寝,欲寄彩笺,奈何山水路遥,只得满眼泪水。
李禺的这首《两相思》堪称是回文诗中的佳作,千百年来被后人称誉。但也有不少人不认同这个不雅观点,以为回文诗只是一种笔墨游戏,并没有什么艺术代价。回文诗在中华文化史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请听情书君细细道来。
一、回文诗真的只是一种笔墨游戏吗?
提及笔墨游戏,我最先想到的是有一种嵌字体,又称“诗钟”,是古代文人在筵席上吟诗作赋的娱乐办法,在限定的韶光里,将限定的字词融入诗中不同的位置,都是临屏而作,极其磨练一个人的即时创作能力。情书鄙人,也曾涂鸦过,和大家一同分享。
《题月梅》
文/微情书
月华起处萤争渡,梅子黄时雨不休。
撷梅煮酒今何似,啸月吟花趁此时。
相邀月色弄清影,不与梅花比浅妆。
不同皓月相怜久,却羡寒梅独早芳。
北固山头梅似雪,西花桥上月如钩。
长亭古道思月老,谪仙笔下有梅湖。
独畏浮云遮霁月,不辞冰雪共寒梅。
题月梅
诗钟和回文诗在游戏层面有其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回文诗的创作难度系数更高,要语句畅通,首尾连贯,却是须要强大的笔墨功底,非一朝一夕能达到的。
刘坡公在《学诗百法》中也提到:“回文诗反复成章,离心离德,不得以小道而轻之。”他告诫众人不能轻视回文诗的艺术造诣。如果真的把回文诗当作一种笔墨游戏,那也是一种高等游戏,一样平常人是不会玩儿的。
二、回文诗,是辞藻堆砌还是有其独特的魅力?纵不雅观李禺的这两首情诗,所选用的意象都很普通,“夜”、“雁”、“酒”、“山”……论辞藻华美,其实谈不上。诗句上的奥妙组合也绝非大略的辞藻堆砌。比如“羽觞一酌怕空壶”,羽觞与杯酒,空壶与壶空,颠倒顺序,便是两个不同的词,墨客遣词造句的能力却是厉害,最高明的地方是所选用的连接词,比如“怕”字就用得很奥妙,怕空壶,怕酌酒,两层意思都很好理解,这便是回文诗的魅力之处。
如果纯挚的辞藻堆砌,诗句颠倒之后是很难读畅通的,更何况一首诗又不止一句话,还得兼顾格律韵律,诗词大意还得融洽得当。墨客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学秘闻是写不出上佳的回文诗的。回文诗确实是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它比普通的绝句,律诗的创作更有难度,也更具特色。
三、回文诗对古代诗歌发展有何影响?
回文诗起源于晋朝,在唐宋期间,深得文人墨客喜好。由于这种形式的文体比较中规中矩的诗词,更有意见意义。诗词本便是高雅的艺术,正由于有“趣”,更有张力。
春秋之后,诗歌呈多元化发展,回文诗便是个中的一类奇不雅观。古代有名的墨客,写诗填词,信手拈来,为了寻衅更高的创作难度,他们乐此不疲。回文诗的创作技巧,将修辞手腕以及词性变革融为一体,后来的宋词与清词,很多元素都有回文诗的影子。比如清代的纳兰容若也曾写过一首《菩萨蛮》:
《菩萨蛮》
清代:纳兰性德
雾窗寒对遥天暮,暮天遥对寒窗雾。
花落正啼鸦,鸦啼正落花。
袖罗垂影瘦,瘦影垂罗袖。
风翦一丝红,红丝一翦风。
中华文化传承从来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经历千百年,回文诗能流传至今,一定有其可取之处。
结语:
从李禺的《两相思》,我们领略到了回文诗构造与意境的双重美。从最初的笔墨游戏演化成一种艺术形式,回文诗对推动诗歌文化发展起着至关主要的浸染。同时也告诫我们要辩证的看待问题,不能偏颇,你以为呢?
参考文献:
《纳兰容若诗词选集》
《学诗百法》
《乐府古题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