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楚辞中最主要同时也是最动人的一首长诗,人们对《离骚》真是爱恨交加,一方面它雄奇瑰丽的词章,壮烈冲动大方的感情,神秘浪漫的氛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眼力,令众人惊叹。可是,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楚地巫祭文化的不理解,造成了对《离骚》的理解困难。很多人感叹:《离骚》真是太难懂了!
实在,这首长诗是屈原出于个人发奋目的而创作出的一部文学作品。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先秦时期缺少文学不雅观念与文学传统。屈原是如何独立创作出如此辉煌壮丽浪漫深情的诗篇,并由此把诗歌艺术推上一个顶峰的呢?
对此,汉代大儒王逸在他的《离骚经章句》中指出:《诗经》是屈原创作《离骚》的源头,而《离骚》正是继续和发扬了《诗经》的艺术手腕,才能得如此巨大的艺术造诣。他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喷鼻香草,以配忠贞……”。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众所周知,王逸所处的汉代是一个膜拜儒家经典,排斥异真个时期,楚辞中所显现出的忠实和刚毅,显然会受到儒家学者的欢迎,但楚辞的敬拜形式又与儒家思想相背离。王逸在不理解楚辞的文化背景下,为了让楚辞流传下去,也只有借《诗经》来粉饰楚辞的本来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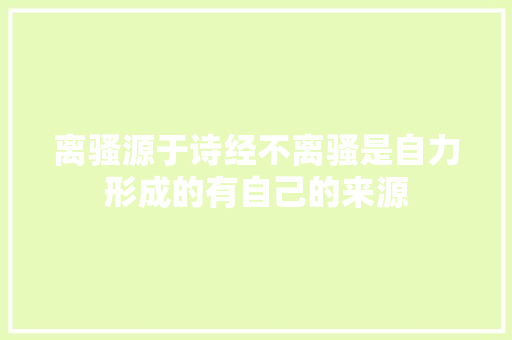
那么,《离骚》的源头是什么呢?换言之,屈原是怎么创作出《离骚》的?即《离骚》的形成模式和来源是什么?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诗经
一、《诗经》并不是《离骚》的源头,《离骚》是独立形成的,有自己的来源;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成为我国诗歌艺术的开端,对后世诗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汉代儒家学者的大力推崇下,《诗经》更是成为儒学经典,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还影响了后世很多文人的精神和思想。
它网络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有300多篇。这些诗歌多数来自民间,也有少部分来自于上层文人;它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社会、爱情婚前、风尚习气、自然天象、地理地貌、动物植物等等很多方面,反响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具有非常主要的历史代价和文学代价。
在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文化制度之下,带有强烈巫祭色彩的梦辞却没有成为异端邪说,反而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诗经》的“庇护”浸染可以说功不可没。在汉代大儒王逸的刻意粉饰下,楚辞终极得以保存并流传下去。可是,《诗经》并不是《离骚》的源头活水,换言之《离骚》有自己的形成模式和来源。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它的功用只局限于敬拜和外交等正式的场合,被当作某种具有神圣启迪性的经典来看。很多时候,《诗经》是被当作一种仪式的,紧张用于诸侯朝聘宴享中的礼制,在特定的场合要利用特定的诗乐,规定严格。
诗经
例如:在《礼仪 乡饮酒礼》中就有记载:
“……设席于堂廉,东上……工歌《鹿鸣》、《四牡》、《皇甫者华》。卒歌,主人献工。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
这段话的意思便是说:当朝中诸侯要进行宴请时,会让乐工专门歌唱《诗经》中的某些篇章,比如《鹿鸣》、《四牡》、《白华》等,而且在歌唱某一篇目时,要用笙演奏相应的曲目。这就像我们当代人在欢迎嘉宾时,会播放相应的“迎宾进行曲”一样,是我国传统礼仪的表现。
其次,在先秦时期,人们强调的是《诗经》的外交用途,而并非它的文学性。在《论语》中,孔子认为《诗经》“可以言”,也便是可以正式地表达自己。换言之,便是看重《诗经》中的兴、不雅观、群、怨的教养功能,认识功能和政治功能,而并非《诗经》的抒怀功能。
再次,在先秦时期,人们并未认识到《诗经》的抒怀功能,《诗经》也并没有构成一个文学传统。它不是供人欣赏感叹的文学作品,而是具有外交功用的“辞令”,因此《离骚》对它进行模拟和改造是不可以想象的。事实上,《离骚》在句式,复沓,用韵及篇幅构造上都与《诗经》有巨大的差异,两者之间不可能有先后的承继关系。
《诗经》各种版本
因此,《离骚》并不源于《诗经》,而是有着自己的形成模式及来源,那便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祭歌和楚地分外的巫术敬拜文化。屈原作为楚国的三闾大夫,这一职务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宗教性子。因此,他势必会对带有浓郁情绪色彩的巫术祭歌产生兴趣,并借助宗教感情来发泄自己的感情。这样,巫术祭歌和巫祭文化,当然就会成为影响屈原创作的第一要素。
事实上,《离骚》是屈原独立创作出来的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屈原为探求精神寄托和安慰而向巫术祭歌学习和借鉴后的成果,是具有很高抒怀代价的文学艺术作品。那么,《离骚》的源头为何是巫术祭歌?本文将从《离骚》的内在构造,文学意象以及措辞特点等方面进行详尽的剖析。
二、《离骚》在内在构造上采取了巫术祭歌的构造作为一部长篇抒怀诗,《离骚》表达了屈原远大的政管理想以及怀才不遇的悲愤,其感情非常强烈,其内容也十分繁杂。它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宜,以及一些巫术敬拜和神话征象。可以说,在构造上,《离骚》古今杂陈,人所莫测,非常地让人难以理解,切实其实可以说是摸不着头脑。
对此,人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事情,提出了很多种划分《离骚》段落构造的方案,但依然很难明得。于是,有些人就认为,《离骚》的构造是凌乱无章的,是不能够做划分的。实在,《离骚》是有自己的内在构造,这一构造与巫术祭歌相同。只是由于人们对楚文化的隔膜而忽略了。
屈原写《离骚》
从巫术祭歌的构造来看,《离骚》实在也有着完全而严密的逻辑性:即《离骚》在构造上是对以《九歌》为代表的祭歌的模拟,总体上可分为三大段。而在第二段和第三段,《离骚》和《九歌》的整体构造完备雷同。详细论述如下:
第一段是从开头到“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犹未亏”。对付这一段的紧张内容,王逸认为,这是屈原在自述出生,属于传记性的情节。这一不雅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赞许。对此,本文认为,这一段是屈原在呼唤楚人先人祝融的降临。
详细而言,便是《离骚》第一、二、三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是屈原在呼唤先人祝融,是唤神之辞,这与以《九歌》为代表的巫术祭歌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呼唤祝融呢?由于“庚寅日”为吉日,在吉日敬拜先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庚寅日与祝融也有着分外关系。据《史记 楚世家》记载,庚寅日是祝融忌日。对祝融而言,庚寅日是一个很故意义的纪念日。
屈原与《离骚》
而后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是屈原呼唤楚人先人祝融降临之后的一番泣诉。此段中,他提起了大量的神祗,向不同神倾诉自己内心的悲愤。
第二段从“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不雅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这一段是在向神祗泣诉之后,仍心绪难平,而往“四荒”探求神灵,向重华陈词,开始了另一次敬拜。
第三段从“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到结尾“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这一段是两次神游,证明了历史上大量君臣际合的事例,抒发自己被离弃的哀愁,表达对故国和君王的留恋之情。
这三段都是一个相对完全的抒怀过程,在抒怀达意上也是相对独立,各自完全的。然而,连接三个段落之间的内在根据却是民间祭歌,是屈原自觉或不自觉的模拟了民间祭歌的构造。和一样平常祭歌在情节上分为三大段一样,《离骚》第一段先引出主祭之神祝融,第二段和第三断再索祭众神。
《离骚》
只不过,在《离骚》中却涌现了两个主祭之神祝融和舜。这是《离骚》不同一样平常祭歌的一个特点。这是由于一,作为楚国先人的祝融身份显赫,须要另一个较为显赫的神灵来陪祭,而屈原选中了地方大神舜;二,屈原身为楚族而生诸沅湘之间,涌现了文化交叉;三,屈原的忧愤深广,仅仅诉诸祝融,不敷以抒发其愤懑。
因此,总的来说,《离骚》在情节构造上,是对以《九歌》为代表的巫术祭歌的模拟,个中提及的神祗就相称于墨客的“起兴”。他通过“巫术祭歌”的形式,进入了一种宗教性的情愫,感情自然也会倾泻而出,这是《离骚》中祭歌构造的巨大浸染。
三、《离骚》在详细情节上采取了巫术祭歌的“人神恋爱”模式;表达和演出爱情是原始巫术敬拜的一个主要特色。详细而言便是以爱情或婚姻来诱降或娱乐神灵,从而得到神灵的庇佑,即所谓“人神恋爱”。这种巫术敬拜模式,已经被人类学的材料和现存的文化文籍证明了,而且在楚辞的《九歌》也得到了确证。
《九歌》不仅是楚地民间祭歌,而且还是感情浓郁的情歌。在个中,有很多感情的表白,是楚地公民根据自己的日常体会,在巫术敬拜仪式上采取的一种取媚神灵的敬拜手段,它不仅表现为婚姻事实,而是表现为“人神恋爱”,表现为对对方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
楚地敬拜歌舞
在楚地公民看来,男女彼此相思的感情过程远比婚姻事实更加美好,用苦苦的相思来表达“人神交卸”的困难是再得当不过的了。因此,用相思来朝神显然也是得当的。总之,在楚地的敬拜活动中,存在着和原始巫术敬拜中普遍存在的“人神恋爱”的敬拜办法。
那么,既然《九歌》中能以爱情来象征人神的交卸,那么屈原当然也可以用爱情来象征君臣的离合。显然这种象征手腕也是来自以《九歌》为代表的祭歌。详细而言,《九歌》中的“人神恋爱”模式表现为:(1)自炫装扮;(2)表达怨慕嫉恨之情;(3)爱情的表白;(4)神的阐述;(5)神的降临;(6)互赠信物。
这种“人神恋爱”的表达模式,在《九歌》的《云中君》和《湘君》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并不是每一篇都具备这些内容,也有是在以上内容之外的,如《大司命》和《少司命》中对神的礼赞,《东君》和《河伯》等分别的感伤等,或者前后次序有所不同,然而皆相差不大。
一样平常来说,敬拜是一项非常具有仪式化的活动。虽然所敬拜的神灵各有特点,但敬拜方法和程序还是相对稳定的。而在《离骚》中,我“人神恋爱”的表达模式也表现为:(1)自炫装扮;(2)表达怨慕嫉恨之情;(3)爱情的表白;(4)神的阐述;(5)神的降临;(6)互赠信物。
楚地敬拜仪式
详细来说,第一步“自炫装扮”的语句有“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薜芷兮,任秋兰以为佩”等;第二步“表达怨慕嫉恨之情的语句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等;第三步爱情的表白有“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第四步关于神的阐述的语句有“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日勉陞降以高下兮,求榘镬之朗同……”;第五步关于神的降临的语句有“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第六步关于互赠信物的语句有“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这些语句不能逐一列举,但基本上概括了《离骚》中有关爱情的情节,事实上,对爱情的追求构成了《离骚》的基本框架,将作者所要抒发的思想感情结为一体,只不过与《九歌》比较较而言,《离骚》中的哀怨感情悲剧气氛要更加浓郁,修辞浸染也更加明显,带有屈原强烈的个性色彩,这也是《离骚》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仅仅是一首程序性祭歌的明显差异。
四、《离骚》的文学意象和措辞风格也与巫术祭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离骚》在情节构造上和巫术祭歌非常相同,但是《离骚》毕竟不是程序性的祭歌,而是一首精彩的诗篇。那么,作为诗歌的另两大要素——意象和措辞,它与巫术祭歌是否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呢?
楚人敬拜
首先,在《离骚》中我们很随意马虎创造,它员一个由浩瀚喷鼻香草所组成的意象的天下。喷鼻香草的频繁涌现,一向被认为是屈原风致人格的外在表现,受到历代文人的推举。而《离骚》中这些“喷鼻香草形象”的来源便是巫术敬拜中的仪式。
其次,在《离骚》中涌现的喷鼻香草共有十八种:江蓠,芷,兰,莾,椒,菌,桂,蕙茝,荃,留荑,揭车,杜衡,菊,薜荔,胡绳,芰,荷,芙蓉。这十八种喷鼻香草,有11种与《九歌》中涌现的喷鼻香草是相同的。显然,这不是有时的巧合,而是来自同一种自然不雅观,由于在初民眼中,巫术与敬拜用品都是神圣的。
事实上,除了歌舞,喷鼻香草在巫术活动中也具有主要意义。在原始的敬拜活动中,除了歌舞之外,巫觋们反复吟唱着喷鼻香草的美洁,以达到娱乐众神的目的,因此,《离骚》中的喷鼻香草传统肯定也来自传统的巫术仪式:即《九歌》只是楚地祭歌中的一组,《离骚》中的喷鼻香草自然也是来自巫术祭歌。
再次,俏丽芬芳的花草是怎么用于敬拜的呢?对此,《九歌 东皇太一》中有记述:
“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扬枹兮才附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纭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喷鼻香草:兰
在这一段笔墨中非常完全的保留了楚地敬拜歌舞的场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女巫们在敬拜仪式上,一壁准备好用蕙兰桂椒制作的祭品,一壁手持喷鼻香草,或许身上也缀满鲜花,在纷繁的音乐声中尽情地歌舞,目的便是使神灵体会到快乐的气氛。
可以说,喷鼻香艳的花草是被作为巫术仪式的象征的。它即是敬拜歌舞的主要道具,又是招来神灵的祭品的主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花草就意味着敬拜行为,在一个特定的期间内,花草与巫术敬拜是不可分离的。
末了,花草为什么会成为敬拜的圣物呢?一样平常来说敬拜的目的便是通过各类手段来与神交通,并使神灵感到愉快,而献祭在任何文化阶段的敬拜中都是存在的。事实上,天下各民族都有用芬芳植物作为祭品的期间,喷鼻香草具有浓郁的喷鼻香味,人们用喷鼻香草来敬拜神灵,实在紧张也是源于气味的考虑。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离骚》之以是会利用大量的喷鼻香草,正是由于《离骚》是源于楚地的巫术祭歌。除了在意象上大量采取具有巫术祭歌特色的“喷鼻香草”以外,在措辞上,《离骚》也具有很强的巫术祭歌特点。
喷鼻香草:椒
关于楚辞的措辞特点,宋代学者黄伯思在《东不雅观余论 翼骚序》这样评论道: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侘傺者,楚语也。顿锉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
这段引文中,黄伯思所说的“楚语”,根据《左传》等文献记载,和中原并没有什么两样。以是这个“楚语”并不是楚国专用于敬拜和诗歌的措辞。事实上,真正用于《离骚》的“楚语”是带有很明显地方特色和韵味的楚地的语助词,即带有天然性的土著祭歌。而这些“措辞”才是屈原《离骚》的独特所在。
除了在措辞上大量采取敬拜词语以外,在《离骚》中还存在着一些很分外的句子,这些句子虽然不是十分清晰,但是在平衡诗歌构造上却有不小的浸染,而它们是来自巫术祭歌中的套语。这些套语是巫术敬拜仪式本身所固有的,只要仪式在进行,它就总要涌现。
换言之,这些套语是约定俗成的,有着自然的规定性,是巫术敬拜仪式在措辞方面的标志,是为了表明仪式的程序和细节,是为了唤起参与者的特定感情。而在《离骚》中就存在着不少这类套语。例如:
“来吾导夫先路”“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聊逍遥以相羊,聊浮游以逍遥”……
喷鼻香草:桂
总之,大量具有巫术祭歌色彩的喷鼻香草意象的利用,以及富有特色的土著祭歌的措辞,是构成《离骚》整体风格的主要成分。而敬拜套语的运用又使《离骚》回环反复,韵味悠长,加强了诗歌的抒怀效果,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使《离骚》显得绚丽多彩,神秘瑰伟。
五、结语:《离骚》是一部带有强烈巫术祭歌色彩的伟大诗篇在对《离骚》的构造,情节,意象,措辞等进行剖析往后,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离骚》在形式上正同于以《九歌》为代表的民间巫术祭歌。可以说,没有民间巫术祭歌,就没有《离骚》,即《离骚》的源头活水不是《诗经》以及其他先秦文学文籍,而是楚地特有的巫术祭歌。
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离骚》在没有文学传统和文学不雅观念的先秦时期,会溘然达到诗歌艺术的顶峰。由于它是属于另一个传统巫祭文化。只管我们不能断定《离骚》到底是真的为敬拜所用,还是仅仅出于屈原个人的仿照,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主人公,屈原在个中投入了自己的满腔激情。
而且,《离骚》采取民间祭歌的目的十分明确,便是要让神灵对自己的世俗遭遇给予一个公道的裁决,让自己悲哀的心灵得到抚慰。可以说,《离骚》之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由于它是屈原以“楚地巫术祭歌”为源头活水,是一部具有强烈巫术祭歌色彩的伟大诗篇。
(注文中图片皆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作者删除。在此,感谢图片的供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