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叙帖》
唐代的草书的发展切实其实至高无上。尤其是张旭、怀素、贺知章,还有当时的一些僧侣。怀素《自叙帖》《小草千字文》这两件风格迥异的作品都特殊好。《自叙帖》因此细线为主,捐躯了用笔的丰富性来营造空间和气势。
书法发展到后来涌现了一些指标,用笔、构造、用墨、篇章等等,对付唐以前的字,达成这些指标都不在话下。但是越到宋往后,尤其是明清,每每只突出一两个指标。而怀素的《自叙帖》,便是超前地捐躯了用笔的繁芜变革,而突出构造和气势、节奏。
书法的措辞既不能不足,又无必要强求面面俱到。突出一点,比如夸年夜构造,点画就不需太繁芜,比如说全体速率提升了,其他的细节便可捐躯一点,创作上要敢于取舍,突出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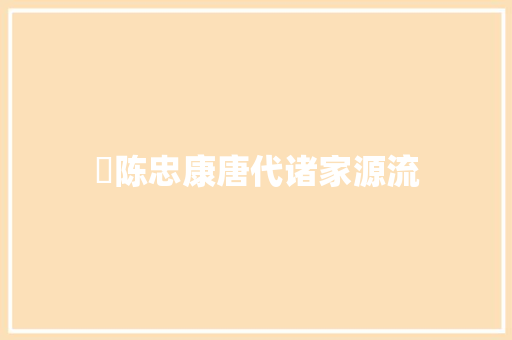
怀素《自叙帖》(局部)
怀素《小草千字文》(局部)
(二)《苦笋帖》
现在看到的这张《苦笋帖》妙不可言,这两行字把“二王”的精髓都学到了,以大草的气势,裹挟着小草的味道,作一笔书。一笔之中写出了最细的线条到最粗的线条,细的是一号线,粗的是十号线,怀素从一号线跳跃到十号线去写,看他构造之间的穿插,东奔西扑的觉得完美诠释了什么是“惊蛇入草,渴骥奔泉”。
怀素《苦笋帖》
孙过庭、贺知章————风规自可高
草书分为大草和小草,小草在唐代首推孙过庭的《书谱》为圭表标准,但是《书谱》的影响值得把稳,它在历史上传播有限,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往后,《书谱》才成为草书学习的根本范本。宋代人学草书必学《十七帖》。《书谱》一贯秘藏于皇宫内府,直到民国才通过印刷品传播出来。《书谱》毕竟字数多,在南宋和清代也刻过,但是流传不是太多。
孙过庭《书谱》(局部)
另一个小字草书大家是贺知章,极负狂客的盛名,他是初唐的皇室宗亲,他的《孝经》用淡墨写出来,类似其淡而有味的诗风,也是当时的高手。在唐代,小草有《书谱》和贺知章的《孝经》,大草就看张旭、怀素。
贺知章《孝经》(局部)
张旭——超脱于理性之外
张旭的《古诗四帖》,有人认定是宋代的字迹,有人推敲为五代的遗墨,难免给人以一种野路子的印象。但是这个帖的代价极高,是写狂草的人必须要过的关。尤其一笔过来,那种节奏起伏的剧烈程度,那种狂热的激情,是前无古人的。
狂草一定要超脱于理性之外一点,必须创造很多有时的效果,必须是正常思维下面写不出来的字才有味道。越出乎理性想象之外,就越有狂的精神,越有狂的味道。到了宋代,黄庭坚草书写得好,是绝品了。但是黄庭坚的字把草书当楷书写,掌握得很稳的,不像张旭的字完备放开了。
以是唐代狂草的形成成分之中,一是和酒文化有关,二是当时的书壁,除了写在纸上,还倾泻在白墙素壁之上,书壁的传统现在已失落传。很多书法家热衷在墙壁上写字,以是留下来的就不多,有的喜好在酒肆创作,就像歌手在酒吧演出一样。狂草在唐代是带着演出性子的。
张旭草书 《古诗四帖》
《草书古诗四首》(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墨迹本,五色笺,凡四十行,一百八十八字。传为张旭狂草之作,极为宝贵。其内容,前两首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疑为伪托)。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环抱,实乃草书颠峰之篇。今人郭子绪云:“《古诗四帖》,可以说是张旭全部生命的结晶,是天才美和自然美的范例,民族艺术的精华,永恒美的象征。
写字不能太理性,太理性必定写不好,有时也可以发扬狂草的精神。我们在培养自己“作意”本领的同时,也要培养自己“率意”的魄力。写字有时候要负责,有时候要特殊不负责,让一个负责的人做到特殊不负责是很难的。实在,放也是一种技巧。
《小草千字文》以蕴藉见称,恰好和《自叙帖》形成一种反差。当然写草书到底是要写得内敛,还是写得狂躁,可以自由选择,比如说《自叙帖》就写得狂放,《小草千字文》写得内敛,两种味道截然不同,但是都不可取代。
同一个字,要琢磨其在大草和小草之间如何转换。小草的范本只适用于小字,一写大字就得着意改造,借鉴大草的方法去处理。如《书谱》只适宜写成小字,这种风格写大了往后气势会退缩。现在很多人学草书从《书谱》入门,以节制字法为先未尝不可。但是《书谱》创作相对困难,有时候写大字不适用。
虞世南——君子藏器
对付虞世南的字,张怀瓘的书论曾经把他和欧阳询作了一个比较,说到“君子藏器,以虞为优”。“藏”便是收敛,便是内敛。
唐代诸家之中,欧阳询是险要的,颜真卿是雄壮的,柳公权是张扬的,褚遂良也像鲜花绽放、妖娆多姿,只有虞世南是内敛的。而内敛便是“藏器”。“藏器”一词又可以回到《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句话里找到归旨,便是单一个“藏”字。“藏”的思想见告人们很多锋锐和气焰都要暗藏起来,不能张扬,要低调,要内敛。低调、内敛的书法到底是若何的?《二十四诗品》有一个词——“冲淡”,虞派书法最根本的神理尽在于此。
明乎此,可以溯源一下,王羲之的哪些字是藏的?王羲之的字有没有藏的东西、内敛的东西?虞世南师承智永,虞世南又传给谁?陆柬之是他的外甥,陆再传给谁?这是一系列的问题。
在帖学体系里,虞世南一脉实在是相称弱势的,但是它在中国的书法文化里又霸占着极高的位置。由于它内敛、蕴藉。凡是内敛、蕴藉的东西,一下子抓不住人的眼球,须逐步品,每每品了不知道多少年往后,才以为平淡真是好。
以是从虞世南往后,平淡的境界一贯是书法家们所追求的。比如说,苏东坡晚年喜好陶渊明的诗歌,平淡之中,自然有一种书卷气。弘一法师追求残酷之极的平淡。以是平淡这一起正好是制衡很多张扬思想的利器,它成为了中国书法美学的一个主要空想。只有中国的文艺因此平淡为上的。
但是平淡的东西常常是不可思议的,任何美好的事物都因此平淡为上。比如清茶一杯,味淡而远。只有淡才能持久,才有风采。韵味是什么?绕梁三日叫作韵,是一种很悠长的味道。当下展览盛行的视觉张力,迅速给予不雅观众刺激,这种美感并不持久,第二次就麻木了,第三次就厌倦了。很多书法第一眼不怎么样,第二眼看看颇故意思,今后越看越耐人寻味,虞世南的书法就属于这一起。
自从虞世南涌现,把他往后的中国书法史跟隋以前的一比,跟“二王”一比。便创造“二王”用笔方法犹如冲锋陷阵,到虞世南这里一下子刹住车,他营造了其余一种气息和味道。这种气息和味道只能用作品本身去通报,措辞无法描述。我只能见告大家,琢磨“平和冲淡”这四个字就够了。能写出平和冲淡的人都不大略,他的心灵受过某种熏陶,一样平常的人办不到,暴躁的人、急功近利的人都无计可施。书法有一种功能,它不是给人以外在的美化,而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功效,学这路平淡的字,你的心性会得到修炼。只有心性修炼到某一种程度才能写成这样的字。中国的书法在古代从来都是教化的一个部分,现在变成纯艺术往后,就跟教化疏远了,是得还是失落呢?犹未可知。
从这一点来说,虞世南一脉便是给所有学书法的人的一味良药,是去俗的良药,是去张扬个性的良药。就我个人而言,特殊喜好这股气,但是我也很难写出来。
我们提倡的穷源竟流是什么意思?即是学体系,找出详尽的图像资料系统。楷书、行书、草书都是怎么样的,然后再打成一片。这便是书法临摹和艺术创造最主要的一种通感。必须打通感官,不能学一个是一个,比如在学《孔子庙堂碑》的时候,要想到《汝南公主墓志铭》和《曹娥碑》等。但是怎么产生遐想呢?这就得看个人的觉得了,每个人艺术的觉得是不同的。一样平常来说,如果写虞世南,上面的几本字帖的学习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一)虞世南临《兰亭序》
现在所谓的虞世南的《兰亭序》临本,我认为它虽出自唐代,但并非出自虞世南的手笔,作者另有其人,只不过它的气息像虞世南。像的缘故原由实际上很大略,经由无数次装裱往后,纸墨就变得破褴褛烂了,气息也就内敛了。比如汉碑,大家喜好看清清爽爽的还是有残破的?初学者肯定选择前者,但是会看的人一定更喜好残破。由于只有经由残破往后,它的气息才会内敛。
《曹全碑》便是太新了,随残破而来的是神秘感。有时候书法的美很是繁芜、有趣的,这件作品便是由于纸墨比较旧,经由多次揭裱往后,看上去很苍老,不如冯承素摹的《兰亭序》光鲜亮丽,青春抖擞。冯摹本像二十岁的人,所谓褚遂良临本像三十岁,所谓虞世南临本像四十岁,定武本像六十岁,它们的气息迥然有别。
虞世南临《兰亭序》(局部
(二)《孔子庙堂碑》
关于这一起风格类型,我现在供应给大家的一组图片,解释了这一书风脉络的特点。这些书风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比如虞世南现存的资料,第一个是《孔子庙堂碑》,此碑到底是真是假?保留了几分虞世南的真面孔?鉴于这些问题,我们还须知道石本的来历,不能直接认为它便是虞世南的,有时候都得打打折扣。虞世南是写过一件《孔子庙堂碑》,但是在唐代损毁了,经宋人重刻,这中间到底丢失了多少面孔?它肯定是有几分像的。那真正的虞世南书法到底是若何呢?全凭你来想象。中国历代的书法家,他们的形象都需靠图像去构成,然后从中进一步理解。这件碑刻或许算是百分之五十的虞世南。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局部)
(三)《汝南公主墓志》
虞世南留下来的第二个资料是墨迹《汝南公主墓志》。这件作品是不是虞世南的?我认为有百分之八十是,但是这件作品出自宋代人之手,并非真迹。古代的书家大都没有真迹流传,画家也一样,全凭想象。王羲之真迹全无,靠你去想象,证据摆在那里,有的证据充分,有的证据不敷。这件虞世南的作品,只管也经由了宋人之手,但一看便是唐人的味道,这里的平淡,不像其他的宋代墨迹,自有一种中庸的君子之风,文质彬彬,这便是内敛,这便是虞世南。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
(四)《文赋》
但内敛之外还是要有一点点张扬,否则内敛等同于无味了,表现最直接的是陆柬之《文赋》。《文赋》的这种写法,看上去优游恬淡,正直直正,一点都不张扬,但越看越以为它难写,越是火候老到。《文赋》我是看了二十年才以为它好,从前学书法的时候,以为《文赋》很诚笃,没意思,后来越看越有味道。比较一下赵孟頫,赵孟頫写了一辈子,末了创造他怎么写得还是不如《文赋》。《文赋》看上去平平正正,很内敛,淡而远,它是范例的虞世南一起的书风,而且是很真实的虞世南的味道。
当代人对《文赋》的评价各自为政,有人以为它是写字匠的作品。但中心美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认为《文赋》是最上乘的字,他以为《文赋》太难写了。写《文赋》时有以下三点值得把稳:第一,姿态很稳;第二,线质温润中带着苍茫;第三,它的速率很平稳,但不呆板,又很厚,构造特殊宽博。
《文赋》秀朗中带着平正,拿它和赵孟頫的字一比,赵孟頫的就巧了,短缺了厚实苍茫之感。《文赋》字里行间忽然会蹦出来一个很大的字,楷书里面也会忽然蹦出几个草书来,这是为什么?这一问题值得去思考。
陆柬之《文赋》(局部)
(五)《曹娥碑》
除此之外,虞世南一脉还有《曹娥碑》,此碑是研究者挖掘不尽的宝藏。据传为王羲之所写,但该当出于唐人手笔。此碑收入宣和内府,又经由宋高宗鉴藏。我刚才为什么说虞世南真正的传人在唐代往后逐步地消逝了,一贯要等到宋代才涌现呢?实际上到南宋的时候,宋高宗才是他真正的传人。宋高宗的书法写得极好,他是赵孟頫的精神导师。宋高宗从前学米芾和黄庭坚个性张扬一类的字,后来学了一段韶光虞世南,他有一个帖叫作《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
王羲之《曹娥碑》(局部)
(六)《养生论》
我们再看看赵构的《养生论》。赵构传世作品不少,比如题画的一些楷书,写得温润敦厚,没有一点火气,只流露出一种帝王式的贵气在那里,绝不张扬。《养生论》里的草书都是不紧不慢的,端严中不乏散逸的韵味,从这些写法里,可以看出他的风格便是学《曹娥碑》的。此碑末端有赵构的题跋,解释赵构对《曹娥碑》很感兴趣。仔细不雅观察《曹娥碑》其构造笔法和赵构相似。当然这种忖度很主不雅观,书法史有时候便是很主不雅观的。我以为这便是虞世南这一派书风的一种补充。可能虞世南未必这么写,但是这种气息便是虞世南的气息。这样的写法在唐代其他书法家之中颇为罕见。
赵构《养生论》(局部)
(七)王宠
明代有一些人,到某一个阶段都要向虞世南取经,以此提升格调。董其昌学了《多宝塔碑》往后,接下来就学了虞世南。由于《多宝塔碑》是匠体字,学起来随意马虎俗,只能拿它练根本。虞世南是提高一个书法家高格调的一个门槛。往学颜体、柳体,学到往后怎么写格调都会不高,什么叫高格调?高格调便是“冲淡平和”,便是“藏器”。当然这种高格调须经由足够的技巧演习往后才能触及。
高格调的平淡不是弱,平淡最随意马虎出的毛病便是弱。我这里再举一个王宠的例子,王宠是学魏晋的,他同时也学虞世南。这件《石湖八绝句》疏淡空灵,它看上去有一股清淡悠远的气息。董其昌有一部分小楷也直通虞世南。他的变革太多了,气脉绵密不绝。
王宠 小楷 石湖八绝句
纸今年夜小27.38x53.6厘米
王宠《石湖八绝句》(局部)
(八)《汉书·王莽传》与《辨亡论》
《汉书·王莽传》是唐人的抄书。这个本子的气息我以为也有点像虞世南,虽然不能说很像,但这种疏疏朗朗的构造,疏疏朗朗的章法,字的平平淡淡,还是相差无几的。况且它很耐看,在唐代的浩瀚抄书之中算是上品。
陆机的《辨亡论》我认为要赛过《灵飞经》,好在哪里?便是活,不匠气。
《汉书·王莽传》残卷(局部)
唐人书陆机《辨亡论》(局部)
(九)蒋善进临《真草千字文》
与怀素的《小草千字文》比较,蒋善进临的《真草千字文》气息更靠近虞世南。当然蒋跟虞世南并无瓜葛,但是我认为气息上有联系。怀素的《小草千字文》也是极蕴藉的,跟他的《自叙帖》和其他字帖有实质的差异,就在于它藏、内敛,以中锋为主,心不在焉地写过来,以柔性线条为主,而非以刚猛的线条为主。
(十)如何临虞世南?
有了这么多的资料,虞世南的形象就很立体了,你可以写楷书,也可以写行书,虔诚临摹或者变形都可以,资料已经自己会说话了。临摹的时候以先墨迹后碑刻为宜。练习可以有很多种办法,可以以虔诚的、变形的或者穿插的办法临摹,也可以以一种意象去写其余一个帖,这便是意临的办法。意临有很多种,我们要研究一下什么叫意临,意临有多少种办法?
写的时候,可以从《汝南公主墓志铭》上手,也可以从《文赋》《兰亭序》等,上手往后,再试着去写《孔子庙堂碑》,把它写活。假想虞世南有一件真迹,这个真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对付平淡的字,一定要把稳,它不是一潭去世水。任何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平淡深处必须具有活泼、灵气、苍老的后劲,否则平淡等同于乏味。比如写虞世南,它是露锋还是藏锋?它的姿态、速率、墨色、蓄墨量等如何?它的笔画以何种心态去写?常日我们写闇练时随意马虎夸年夜过分,这时候就要用平淡的手腕把它调回来。
中国书法的思想里,融通是必不可少的,是须要我们去培养的一种艺术觉得和能力。这几种字帖跨度很大,彷佛根本没办法融和,其实在经由永劫光演习之后才能打通。伟大的艺术家会把一些看上去不搭界的玩意联系起来,而且可能会莫名其妙地把它们联系起来。当然我们现在的视野还限于书法,而真正的书法家会把字跟做人、天地、自然以及生活里的各种道理和意境联系起来,然后形成一种觉得。以是古人看到担夫争道、划桨、蛇斗等会有所感悟,这便是通感。
写《文赋》要用半生偏熟一点的纸,带着些微毛涩感,捉住这种觉得去写。唐代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文赋》的字比较严谨、平正,笔画毛辣辣的,虚实相间。该圆的地方,该方的地方,该锋芒毕露的地方,该轻松的地方,该厚重的地方都需表现出来。笔墨的细节和变革一定要呈现,无论写什么字。就《文赋》而言,任何字之间的气质都是独特的。它看上去彷佛是统一的,但又有奇妙的差异,这便是“神”。我们面对范本,哪怕是再平正的字,也要区分出它不同的气质和神韵。就像三个人都戴眼镜,但是他们的表情和气质互异。三个字要分别写出三种人的味道,不能始终一种表情,这是写所有工稳一起书法的窍门,工稳之中必须带有一种写意的身分,否则便是匠体字。
苍老一点的怎么表现呢?《文赋》不像冯承素的《兰亭序》一样锋芒毕露,锋芒毕露有时候是令人很讨厌的。应避免过于粗糙,要笔笔温润。它也是秀中含苍,这点特殊值得把稳。中国的美学喜好把完备对立的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比如秀润苍茫、丑媚等。
乃至可以照着它写出行书的觉得。照着楷书变行书,或照着行书变楷书,书写时可以参照《汝南公主墓志铭》,再把字字端正的章法变掉。
《汝南公主墓志铭》需写得冰清玉润,没有火气,在速率上面要把稳,不要用枯笔,一丝不苟地每一笔送到。线条的中间都是有动作有起伏的,而非平铺直叙,相互之间穿插着练,环绕着这个中央去练,练一段韶光,笔性和思维肯定也会生动起来。
欧阳询——避免落入俗套
如何写欧体?我们举一反三。第一个是欧阳询,第二个是欧阳通。欧体也有墨迹和碑刻之分。欧和虞是两种完备对立的风格类型:张扬和收敛的、险要和平淡的。它们是很抵牾的两种风格,代表着两种措辞、两种技巧。
欧体的标准件不是《九成宫》,是《梦奠帖》。如果想学欧,《梦奠帖》的一笔一画都要非常清楚地印在你的脑筋里,滚瓜烂熟,统统以《梦奠帖》作为标准出发。
欧阳询《梦奠帖》
有人会说它是行书,我学楷书怎么办?一个人写的字,不管是写楷书、行书还是草书,都是相通的。有了标准件往后,熟习他的风格、尺度、笔墨,只不过写正一点,写慢一点便是楷书了。
所有纪念碑式的书法,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唐碑都是打格子的,它不这天常书写。大家学了很多石本往后,一创作就张罗打格子,这都像学生习作。格子到底怎么用,这是其余一个问题,牢记写唐楷要冲破格子意识。
虞世南、欧阳询只有在写碑的时候,下人替他在石头上面打了格子,他才会就着格子写,另日常平常写字会这么写吗?以是书法还有多种的利用功能,这只是它的一个侧面。日常书法是若何的呢?该当是像《梦奠帖》这样的。楷书该当怎么写得生动呢?该当像元代人往后或是像宋代人的那种楷书,才是真正的楷书,是在书斋里写的楷书,而不是为了写一个纪念碑。以是书法还分为书斋、纪念碑、大地书法,现在还有展览书法。随着功用的不同,写法也相应地改变。学他们的字,末了都要化出一种日常书写的格式,不要拘束在纪念碑上。
(一)辨别版本
至于欧阳询的字哪个碑好,见仁见智,一样平常最有名的是《九成宫》,《九成宫》有瘦本和肥本,一样平常称宋拓本为肥本,我对肥本很疑惑。其他还有《虞恭公碑》《化度寺》等。我个人最喜好《化度寺》。
每一个石本是怎么来的,属于什么拓本,这些知识大家都要理解。比如《化度寺》有多少个版本,哪个版本最好?不同的版本各有什么味道?关于《化度寺》的版本,常日我们说的是上海图书馆吴湖帆藏的“四欧堂”。当然还有敦煌的版本,以及清代留下来的版本。哪个版本好呢?
学欧体、颜体的时候大家有把不同的版本拿来研究一下吗?欧有几个面孔?他还有几个像北碑那样刷过去的字。欧的风格便是北派的一种气息,虞世南则是南派的气息,这两种气息截然不同。如果你学他们两家,你就要找到两个地盘,找到两根拐杖。
欧阳询《化度寺》(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
(二)《更漏长》
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敦煌创造的民间写的欧体《更漏长》,这一看便是欧体,便是书写体,不管大家喜好与否,这便是日常书写。它有打格子吗,它字的大小一样吗?它很张扬,笔画直来直去,没有一点点蕴藉,这是它的毛病,但也正由于如此,反而有自己的意义和代价。大家想想民国书法家郑孝胥,他的字便是直来直去。直来直去自然有直来直去的优点,就像少林拳一样沉着刚猛。武术里面既有少林拳那种很刚劲的拳法,也有太极拳一类以柔克刚的路数。怀素的《小草千字文》好比打的太极拳。郑孝胥这种字打出去便是用力的,脱手不容情,容情不脱手,是日然也是一种很好的风格,他肯定受到新资料启示,有了感悟往后才敢放笔去写这一起。他把笔画里的细节,那种柔性和矫揉造作统统去掉。每每我们顾及噜苏的一壁时,字就随意马虎显得矫揉造作,一照顾细节时就会失落客岁夜气。
《更漏长》
(三)变形与创造
写欧很随意马虎步入去世局,学唐代人的书法每每会失落去想象力,不会变形,这是学唐楷最麻烦的一个地方。大量学唐楷的人都有这个毛病。
以是我们有了一定根本往后就得变,把笔法、构造合理地改造,变得多姿多彩,变得活泼,逐步发展自己的路子,找到自己的个性。这些例子只是一部分,大家也大可去创造,还有很多,只是大部分人都
比如这件《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这些字造型太美了,何必都写得像《九成宫》那样呆呆板板的呢?一写就落入俗套,而这便是一个很好的启迪。这些字构造特殊结实,又很旷达、自由、有表现性。写唐楷学虞世南险些不可能写大,否则吃力不谄媚。然而学欧能写大字,怎么写呢?常日《九成宫》想写成大字基本上是弗成的,但是大家参考一下这件作品,写大就好看。虽不过三四页,对付行家、觉得好的人来说,足以创造出一个风格。古人看到三五行字就足以创造出一种风格来。谁真的把这三、四页存心去写,就能够写出你的一片天地,在写欧体的领域里你就鹤立鸡群了。
《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局部)
(四)欧阳通
欧阳通作品有两种,一种是《道因法师碑》,一种是《泉男生墓志》,两者各有千秋。一个字大一点,一个字小一点,但是写这些字随意马虎写去世掉,由于它雕刻痕迹太浓。从我个人来说更喜好《泉男生墓志》。
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局部)
欧阳通《泉男生墓志》(局部)
(五)嵯峨天皇
日本的嵯峨天皇是欧阳询体系的一个大总结,他把大欧、小欧以及其他干系风格全部总结出来,完美地保存了该体系的一些在中国失落传了的写法。也便是说欧体这一体系有一起写法,唐代往后失落传了,但日本保存下来了。日本人很规矩,学唐代人基本上都是按照唐代人的套路。
嵯峨天皇《李峤杂咏残卷》(局部)
褚遂良——极具开放性
大家现在学褚比较多,楷书入门什么字帖比较好?无疑是《大字阴符经》。《大字阴符经》作为入门实在是一个很得当的字帖,第一它是墨迹,第二它介于楷、行之间,对楷书和行书都有一定的帮助,第三它用笔很丰富,它的技巧相对其他字帖更繁芜些,经得起学。
褚遂良《大字阴符经》(局部)
褚到底有多少种风格?纵不雅观他的生平到底是若何的?他的前后有什么变革?《倪宽赞》《大字阴符经》到底是不是他的真迹?虽然目前尚无结论,但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该当引起我们的把稳。
《雁塔圣教序》是褚最范例的风格。在不同的风格流派当中,虞是属于中性的,欧是刚性的,褚是柔性的,如美女婵娟。在唐代,风格涌现了分解,隋以前风格的分解不明显,唐往后风格的类型越来越明确。褚遂良前半生便是从隋代过来,他早期的作品受隋代的影响,然后再创造出这种很范例的风格。褚遂良与薛稷同属一种风格,薛更瘦一点。这种风格可以理解为女性化,在书法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在书法中能表示一种柔性的、女性的姿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但是我们在学的时候应把稳取舍。
褚遂良《倪宽赞》(局部)
学褚到底学什么字帖好?现在很多人学唐代都存在一个问题,比如学《雁塔圣教序》《大字阴符经》往后,写作品时把两者一掺,格子一折,用四尺对开写条幅、绝句、律诗等,写出来往往档次弗成,像小学生习作。
其余一个问题,唐代这类字的风格是非常强的我们学了往后可能一辈子都很难走出来。它的某一种用笔习气,很可能是一种习气。凡是风格强的,大家越要把稳,越要谨慎。越是风格强的,我们学到的每每不是普遍性的营养。
比如明清、民国就有一些风格特殊强的书家,我很喜好弘一法师的字,现在有些人跟风写他晚年那种脱去火气的字,这种字不能轻易学,我们没达到高僧的心态,就不能写那种字。真正值得我们学的是什么?是弘一法师中期变革阶段的字,那种穿越于石本之间特殊有造型感的,构造安排特殊美术化的值得我们去学习。至于晚期的那种范例风格请谨慎考虑。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局部)
(一)《伊阙佛龛碑》
学褚遂良很难摆脱笔画纤细、弱、秀等问题。褚最有特色的风格是《雁塔圣教序》,但他真正有味道、带有古趣的,在古质和今妍之间倾向古质的,便是他从前的《伊阙佛龛碑》。构造宽博大度,类似《龙藏寺碑》《苏孝慈墓志》的那种觉得。
褚遂良《伊阙佛龛碑》(局部)
(二)《孟法师碑》
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这些人超过隋唐两代,他们大部分生活的时期都在隋代。褚遂良的所有作品中,我最喜好的还是《孟法师碑》,它介于今、古之间,既有新体的特色,又有古趣的特色,我们要从这种气质、气息的层面去把握。《孟法师碑》用笔的层次模糊,学了随意马虎变通,往前到隋代,往阁下到欧,乃至到柳都可以。它会演化出很多风格,这是它的特色。
褚遂良《孟法师碑》(局部)
(三)《飞鸟帖》和《枯树赋》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便是褚遂良的行书面貌到底是若何的?褚的体系后来有哪些人传承?欧、虞用笔比较朴实,越朴实的用笔越是直来直去,没有那么多花哨的动作。
褚现在留下来的《飞鸟帖》和《枯树赋》,后者相对真实一点,前者真伪存疑,但也是一个不错的范本。《枯树赋》,后人把它归到褚的名下。这件行书的手腕不便是范例的米芾风格吗?但它是不是米芾的呢?
褚遂良《飞鸟帖》
褚遂良《枯树赋》(局部)
(四)《向太后挽词》
米芾真正至高无上的是《向太后挽词》。现在很多人一写米芾,就去写尺牍。还有很多人放弃写《蜀素帖》,然而《蜀素帖》才真见功夫。那些尺牍都是一些花哨的动作,虽然尺牍也很有代价,但是现在太热门了。米芾的面貌很多,他真正学的有哪些呢?他肯定学过褚遂良、沈传师等。他在褚的流派里,可以和褚打通。《向太后挽词》大家一定要好好研究,它技巧丝丝入扣,笔尖用得太精妙了。米芾生平最得意的字是这种小楷,不轻易写与人。现在米芾传世有四五种题跋小楷,而最精彩的是这件。个中包含的技巧和风雅度是很高妙的。
同样学米芾,大家先学什么?比如《褚遂良摹兰亭序跋赞》就很靠近,但是尚不如《向太后挽词》。大家一定要多比较不同的字帖,自己的眼力就逐步提升了。它的形态,既接得上褚,又接得上米,介乎两者之间。这便是对褚遂良一脉的一个补充。据此,我们可以把褚和米打通。但是要如何打通呢?
米芾《向太后挽词》
这是米芾的大行楷书,他用笔的轨迹完备脱胎于褚,包括用笔的姿态和走势、松紧的关系等。但是米芾不止学褚遂良一家,还有颜真卿、柳公权等,以是会带有很多人的气质,这便是领悟。
光学一个书法家的尺牍是远远不足的。学米芾要只管即便去图书馆看故宫的三十本《米芾全集》。熟习了墨迹,再看他的碑刻、刻帖,有时候这些正好是被忽略的主要信息。米芾临颜真卿的作品就带有很多褚遂良、柳公权等人的觉得。学唐代诸家可以练框架,骨架才立得住。
米芾《褚遂良摹<兰亭序>跋赞》
(五)唐太宗
米芾是褚遂良系统中的一个很主要的书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书家。比如唐太宗,我特殊感兴趣。实在唐代有几个天子的字该当引起我们的把稳,这有时候是一条别人熟视无睹的路径。
唐太宗李世民最负盛名,他有《温泉铭》《晋祠铭》等。今后是唐高宗李治,末了是唐玄宗,他有《鹡鸰颂》。这三个天子代表了唐代风格流变的一个过程,帝王有时候会勾引某一种意见意义。中国历代帝王是怎么勾引书法意见意义的?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唐太宗《温泉铭》(局部)
唐太宗的《温泉铭》在唐代是独树一帜的。其他人的字都比较安静,带着文人气。而唐太宗的字是帝王气,胆魄过人。他的字敢于变形,跌宕起伏。『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个词用在唐太宗身上适可而止。
我们的字都偏安静,该怎么展现活力?首先字形要做一种龙虎之态,同时要能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敢于变形、张扬,敢于以势去写。唐太宗的字便是这样,把字形拉长,用笔、构造无奇不有。他学过王羲之,但气质上一看便是他自己的。字里行间的权奇飞动实凡人所无有,只有嵯峨天皇能靠近。
唐代肯定有一股书风,字字作飞扬的态势。古人常把书法比作龙蛇、飞鸟,这种自然的意象存在于书法之中。我们总以为这样写就过分了,不敢写,当然处理不好也随意马虎写野。唐太宗这类字可以给我们一个启迪。
南京的高二适有批点唐高宗的字。高二适的字受明代宋克的影响,但他最紧张的精神气质来源于唐高宗。这给我们一个启迪,当代的大家,比如沙孟海师长西席等,他们走的都不是平凡的路。
高二适从前学的是他的老师章士钊,到五十多岁还是写得稀松平常,但是之后为何忽然让人刮目相看了?可能他创造唐高宗书法的某一种精神恰好与他自己相契合,再加上自身强硬的诗人意气,就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样的,通过修炼我们能不能也找到自己的天地呢?
虽然高二适的字谈不上跟褚遂良有多么严密的关系,但是我多少以为它暗合于褚的某一种态势,只是更张扬罢了。褚的系统从气质上来说是柔性的,但不是纯柔。它的这种柔性奥妙地利用了腕,才能产生这种柔美和奥妙的映带关系,以及走势之间辩证起伏的关系。褚遂良的字有一种写法彷佛还靠近于冯承素的《兰亭序》摹本。
徐浩——唐法的本来面孔
中盛唐书法有两个至关主要的代表人物,徐浩和李邕。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个人风格特殊明显,但是这两个人的风格相对平凡,尤其是徐浩。所谓平凡便是在唐代的风格类型之中他不是最强烈的,包括李邕,他跟徐浩在总体风格上是一起的。
(一)《朱巨川告身》和《鹡鸰颂》
这种风格是什么呢?我们先看徐浩的《朱巨川告身》,这便是最范例的唐风。什么是唐代的风格?除了风格分明的大师级人物之外,这便是当时人最喜好、最普遍的一种意见意义,写得肥美茂盛。
徐浩《朱巨川告身》(局部)
唐代以肥为美,比如唐玄宗的《鹡鸰颂》,他的每个字都有杨贵妃的影子。以是一个时期的审美、风气跟字或多或少有内在的关系。《鹡鸰颂》看上去很正,但是用笔老到,大气、灵巧,是很难写的。他每个字都经得起放大。我很喜好这件作品,但是我写不出来。当然,唐代的字都难写。也可以说,如果想探求范例的唐法,这件字帖便是最范例的。如果看过更多的唐代普通人写的字,尤其是盛唐到晚唐这段期间,基本上便是这样一个面貌,比如敦煌的抄经、遗书等。这种肥美、端庄的风格,便是平正书法的极致,想做到平正而雍容大度是很难的,就像做人一样。当然有的人不以落落大方为美,甘心故作怪状。或者我们写字要变形,变得过度就随意马虎不大方。
大方这个词,大家逐步去体会,做到不随意马虎。
唐玄宗《鹡鸰颂》(局部)
(二)《不空和尚碑》
这是徐浩的《不空和尚碑》,从《朱巨川告身》我们可以推导出《不空和尚碑》的写法。《不空和尚碑》经由刊刻后,流失落了太多的魅力,以是这也是导致徐浩受人轻视的一个缘故原由。
我们插上想象的翅膀,把《朱巨川告身》的神采注入《不空和尚》的躯壳,这可能才是徐浩的本来面孔。给它的躯壳穿上衣服,披上皮毛,输上真实的血液,这便是写碑的一个方法,通过墨迹的感应往后,再把信息加入到碑中。我们要把细微的轨迹展现出来,而不是粉饰,这样才会学得更加立体。而且楷书里面每每带有行书的笔意,唐代真正的楷书本该如此。
徐浩《不空和尚碑》(局部)
李邕——宽博大度
接下来谈谈李邕。李邕传世最有名的是《岳麓寺碑》和《李思训碑》,一肥一瘦。李邕是唐代遍及行书入碑的人物,其书法紧张特色是宽博,比徐浩更宽博。董其昌评曰:『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把他跟王羲之相并而论,可见其地位和影响力。
李邕《岳麓寺碑》(局部)
李邕《李思训碑》(局部)
(一)《出师表》
《出师表》不一定是李邕的,这种气息可能是明代人的,但是很值得一学。通过这件字帖可以看出,赵孟頫的楷书便是学李邕的。怎么把字写得宽博、大度,同时又精到,且态势丰富?我们千万把稳不能把字写缩,尤其是唐楷,如果顺着唐楷的势,我们会越写越拘谨,一定要努力写出宽博的觉得来。
李邕《出师表》(局部)
(二)《端州石室记》
李邕还有《端州石室记》,令人爱不释手。它的残破产生了一种神秘美,给予我们想象的空间。它有点像魏碑,写大字的时候可供参照。它的每个字看上去很平正,但实在生龙活虎。我们可以把它和《朱巨川告身》放在一起学习。
中国古代的字讲究一种庙堂之气,为什么清代宰相写的字端庄雍容,这便是由于庙堂气。当代书法短缺庙堂气,更多靠近于一种野逸之气、山林之气。贵气和庙堂气之类在中国古代备受推崇。而真正的庙堂气的根基需立在唐人身上。
《端州石室记》是很故意思的字帖,它的模糊性为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不愿定的东西反而更精微。模糊的笔画加上我们自己的理解就比确定的更有意见意义。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临帖到底临几分像好呢?有人说三分像,有人说七分像,有人说十分像。如果是对着古人的真迹,一样平常来说是越像越好,由于它本身是很明确的。如果是模糊的碑刻,除非勾描出来,最多也只能写个六七分像,这当中自然有自己发挥的余地。
李邕《端州石室记》(局部)
(三)如何由小入大
当然徐浩、李邕、颜真卿他们是有关系的。颜真卿从前写的《多宝塔碑》《郭虚己墓志》等也是当时普遍的风气。自从到了中晚唐往后,字明显写大了,碑也刻大了,这是一大变革。
中国的书法从小字逐步到大字是一个了不起的过程,也是随着各方面成分的成熟而产生的,比如物质材料方面的羊毫、纸张等。从小字到大字是很困难的,常常写小字的人写不了大字,学褚、虞的字转变到写大字险些不可能,它便是小字系统的一种方法,包括学王羲之,除非变形能力特殊好。书法从小字到大字是一个缓慢变革的过程。小字和大字是各自相对独立的系统。
大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便是从颜真卿、柳公权、李邕这些人开始的,他们逐步创造了写大字的方法。
颜真卿《郭虚己墓志》(局部)
颜真卿——书写的三种状态
(一)《八关斋会报德记》
颜真卿的字普遍比较大,比如他的《八关斋会报德记》。《八关斋会报德记》气很足,他在庙堂之气里又加了古拙,跟徐浩、李邕的新媚不一样。《八关斋会报德记》越到字的下方越是沉着开阔。字的重心下移是笨拙的一种表现,颜的魅力就在于此。
颜真卿《八关斋会报德记》(局部)
(二)《颜勤礼碑》
《颜勤礼碑》是眼放学颜体的大热门,它的笔画脱节,横、竖不真实,学了往后写字难有骨骼,但是它的态势是好的。《颜勤礼碑》是晚清民国才出土的,真伪上还须多留点心。
颜真卿《颜勤礼碑》(局部)
(三)《麻姑仙坛记》
我们研究书法史时试着思考下,颜真卿在唐代写了多少字,唐宋人对他是怎么接管、认识的,到了宋代还留下他的哪些字帖,明代最盛行的是他的什么字帖,王铎、傅山曾经学过他的什么字帖……这就关系到一个书法家的传播史和接管史,这是很主要也是很故意思的。
颜真卿一贯以来都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大热门,他留下来的书迹也是极多的。明代最盛行的可能是《多宝塔碑》或是《麻姑仙坛记》。《麻姑仙坛记》有大字和小字两种,先找到宋拓本,还要看历代的金石条记和专门的金石学题跋的著作,才会弄清楚来龙去脉。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 · 大字本》(局部)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 · 小字本》(局部)
(四)《自书告身》
学颜真卿的楷书一定要对照一下《自书告身》和其他墨迹之间的关系。《自书告身》是宋代人勾摹出来的,不是真迹。《自书告身》跟颜其他的楷书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会创造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不正的,都是姿态万千的,这便是当时人的正常书写。这个问题需引起重视,在认识古代书法家的时候,尤其是唐代书法家,我们缺点地以为他们平时也保持了纪念碑的书写状态,而纪念碑是在特定的场合下利用的,比如西安碑林留下来的,它是书法的一个类型,但从某一方面来说它不是真正的书法,它是为了某一种纪念的功能而设计的,就像现在的广告牌、黑板报和美术字一样。
颜真卿的《自书告身》跟《朱巨川告身》一样,这才这天常书写的状态,才是书法。反之,学《多宝塔碑》《颜勤礼碑》,怎么把碑上的字变成日常的书写,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当然,人的日常又分为几种不同的状态,如负责的状态,放松的状态和极度随意的状态。
颜真卿《自书告身》(局部)
(五)书写的三种状态
《自书告身》的书写是比较严明持重的状态。其余一种,比如给他的朋友蔡明远写信,或是《湖州帖》和《刘中使帖》就处在放松的状态。还有《祭侄文稿》是在极度悲痛的情形下写就的,这种非正常状态是一种草稿状态。
实际上历代的书法家写字都有三种以上的状态,有时候乃至更多,这也是我们认识古代书法家的一个视角。由此我们就要认清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争座位帖》是在某一种极度的状态下的草稿。大家思考一下,假设颜真卿准备写一个立轴作品(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立轴),他会怎么写呢?明代王铎、董其昌等,他们就有各种各样的写法。王铎有一个很规整的馆阁体楷书是写给天子的,完备跟另日常平常不一样,这就很故意思。现在有些人写作品用颜真卿的草稿体,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这种草稿的字是否适宜一样平常正规的作品?何绍基有大量的草稿写得很精彩,但是他从来不拿草稿示人。一个书法家的书写分率意和作意。
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一个书法家的书写分率意和作意。这是任何一个书法家必须具备的两种本色。很多人写字都作意太浓,太负责,但有些人又率意过度。像米芾这些大书法家,我们既能找到他们很作意的字,也能找到他们很率意的字。
赵孟頫是作意的代表,日书万字犹能端正如初。率意的代表是董其昌,他曾经写一通《千字文》,兴之所至,断断续续用了几年的韶光才完成,这正好是他的特色,正如作意是赵孟頫的特色。一个书法家可以作意多一点,也可以率意多一点,但是必须两者都节制。两种不同的书写状态是两个很主要的书法技巧,这关系到两种心态。我们用这样的眼力去看颜真卿,他就立体了。
颜真卿的字逐步写大,富有意见意义,再加上他是忠臣义士,下笔就有堂正正的传染力,以是他能在历代赢得一个好名声。且他确实有创造性,以是在中国书法史上他一贯有着除『二王』之外的最高的地位。
这里要推举日本的空海,他的书法有一股唐风。他的《风信帖》给我们供应了其余一种类型的可能,它不是草稿,胜似草稿,不像《祭侄文稿》那么潦草。
空海《风信帖》(局部)
岔开说一下,我们要把稳,颜真卿最范例的行书风格该当是《蔡明远帖》《裴将军》这一类,而不是《祭侄文稿》。《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很多人喜好放大写,写得圆头圆脑。而《蔡明远帖》这种范例的风格跟他的楷书就比较靠近。反之,我们把它写成楷书,就找到另一个法门,这也是对颜体的一种创造性的书写。《湖州帖》也很好,但是一看便是米芾的笔调,还是不如《蔡明远帖》大度。
颜真卿《蔡明远帖》(局部)
回到空海的话题,《风信帖》杂糅了行、草书,用笔圆厚、滋润津润、松活,构造也宽博。他的草书充分表现他的直接和率意,这种率意反响了一种放松的状态,作意则是严明、自持、负责的状态。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联络、紧张、严明、活泼』,我们写字也应几种表情轮换着来。字是有表情的,心态变了,字的表情也就变了。
这里举个沈尹默和马一浮的例子。他们晚年眼睛都看不清,但是这时候写的字都比平时的好。这些人到了某个年纪,乃至衰朽之时写的字每每是最好的。比如弘一法师绝笔书『悲欣交集』这几个字冠绝平生。启功晚年拿不动羊毫就索性用钢笔写,但字的味道好得不得了。启功写字太负责了,但是在他晚年精力衰退的时候字的境界反而升华了。
弘一《悲欣交集》
以是不一定负责就能写好字,更要放松和游戏,通过炼心来达成这样一种状态。佛教里说『心无挂碍』,无挂碍的时候我们就能写出好字,当我们冒死想写一张好字的时候肯定揠苗助长,除非抗压能力特殊好。当然,写到忘我的程度时,肯定能写出好字来,忘却了得失落,忘却了统统功利,也就无挂碍了。正由于这样,字里行间就会涌现很多莫名其妙的变革,是一种理性无法达到的美。当行家人写出外行人的字的时候,那个字是最好的。
(六)名家若何学颜体
清代学颜学得好的有翁同龢,他的用笔有破破碎碎的、不规整的老辣感。他的字很端庄,骨骼坚实,又很放松、活泼,越到晚期越有黏黏糊糊、抖索索的味道。他中年的字太俊秀光洁,作意太浓。为什么他晚年的字好?这便是回归了天真,笔触在纸上的变革更多了,笔不同,尤其是写大字最关键的便是气势以及呈现出来丰富的笔墨信息。大字通过用墨往后须产生一种三维的立体感。这种立体感也可以理解为有厚度、有灵魂的块面感。所谓厚不是写得粗便是厚,有人写得粗,却显得笨,但是怎么做到粗又不笨,这是一个难题。
翁同龢《录苏轼论画语轴》
其余一个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伊秉绶,他用隶书的方法写颜体,线条非常纯洁。他是构造魔术师,像元代的柯九思、倪瓒,明代的八大隐士,清代的金农、伊秉绶,民国的弘一法师等,他们的构造处理、变形能力非常了得。他们很多都是画画的,对付造型格外敏锐,我们仅限于写字就短缺这种造型能力,这是须要把稳的。
伊秉绶最出名的是隶书,但是他学颜颇有心得,把颜体的框架借鉴过来,线条有时候写得很细,用笔特殊纯挚,还有些小字抖抖索索的,但是也很有味道。如果看真迹的话,那种圆厚、纯挚、没有一点火气的觉得会更直不雅观、更强烈,这也是对颜体的一种创造。
伊秉绶 隶书对联
清代写碑有一批妙手,但是在帖学这路,写得好的基本不多,刘墉算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他学谁呢?紧张是董其昌、苏东坡、颜真卿这三家。我们看他也有『二王』的洒脱随性,这种气质,不像伊秉绶宁静、结实,反而示人以慵
字是有精神气质的。当然刘墉的技巧也非常好,他楷书的变革很丰富,很活。他们都是理解透了的,看上去大略,实际上都不大略。他的这种自由之中又隐含庙堂气,是明代以前的人没有的,清代的高手才能办到。
刘墉《行书远景楼记轴》
宋初除了蔡襄之外,这一流派的要把稳的,便是宋初的李建中和林逋。李建中的《土母帖》要特殊把稳。林逋留下来的几个帖也很故意思,他写得很瘦,李建中写得很肥。他们之上还有一个杨凝式,他的每一个帖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他的精神境界之高,宋往后也没人写得出来。
李建中《土母帖》(局部)
柳公权——被『摈弃』的巨轮
接下来我们谈谈柳公权。如果现在有人问我,目前对唐代谁的书法最有觉得,那便是柳公权。
柳公权这块地经由一千多年的荒废,没什么人去耕耘,但我认为这个中的新意大有可为。他最有名的是《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初学唐楷,除了《大字阴符经》,柳体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由于它的这两个石本刻得很好,而且它笔画壮实,骨骼之强健,在唐代无出其右。
柳公权《玄秘塔碑》
柳公权《神策军碑》
我们学书法,无非是学字体的骨、肉、皮、血、脉,末了再到精神。学颜体的人每每随意马虎肥软,学欧体的如果构造失落准就差之千里,初学虞世南根本领悟不了它的味道。以是从柳开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柳体创作是很难发挥的,而柳公权也比较遗憾,不像欧阳询、颜真卿留下这么多作品。他留下的《蒙诏帖》尚且存疑。
(一)《圭峰禅师碑》
中国的大字法门实际上是从颜、柳开始开拓的。裴休的《圭峰禅师碑》便是学柳体的小字,彷佛还带有欧的味道。唐代有大量的字是杂交的,有欧、柳结合,有柳、颜结合,有褚、欧结合。比如日本嵯峨天皇既学欧又学颜,这个征象我们要把稳。唐代的字风格面貌很多,几个门派之间可以相互串门。
裴休《圭峰禅师碑》
(二)日常书写的楷书墨迹
我们看字一样平常透过它的形状去抓精神特点。柳体的精神便是骨骼耸立,字形细长,写的时候要捉住这个特点,不必拘泥于《玄秘塔碑》。在《淳化阁帖》《大不雅观帖》里仍旧保留着柳的行草书,虽然数量有限,但基于这些字帖,再加上《蒙诏帖》,再加上他的楷书,我们立时就能建构出柳体的楷、行、草的系统。
柳体有一种奇趣,除了骨骼耸立、结实、细长以外,还有一种很奇的精神魅力。他字的大小、穿插、错落等特点是统统好书法的共同特点,尤其是行草,必须大小错落,绝对不能统一,必须有走势、俯仰、节奏、墨色等。
柳公权现存有楷书墨迹一件,在看它之前我们先看柳公权《十六日帖》,这便是他的日常书写。再看这件楷书墨迹,这是一段《送梨帖》题跋,可以说如果参透这四行,也就参透了柳法,从中可以想象柳体的真实书写。《玄秘塔碑》是放在表面的屏风,而真正的柳公权躲在后面,就像这四行字。我们再把它跟徐浩等人的字联系起来,就能得到启示。
柳公权《十六日帖》
柳公权《送梨帖》跋
(三)《蒙诏帖》
把《蒙诏帖》跟王羲之比就能创造差别。它受唐楷影响往后提按多了,字的楷法多了。唐人擅用长线条,以是它仍给人一笔到底的觉得。下面再重点剖析一下这六行字的起伏。
中国书法紧张有手卷和立轴这两种形式,宋以前的书法基本上都是手卷,尺牍便是手卷的一种类型,三五行的尺牍随意马虎写,但长手卷就相对难办些。如何营造出一种波澜起伏的交响乐的觉得,这关乎中国书法手卷的精神。我们可以参看宋代黄庭坚、米芾的手卷,会更加磅礴彭湃。当然唐代亦有之,但从某一壁来说,还只是限于形式,没有太艺术性的表现。而《蒙诏帖》已经具有手卷的意识,顺着感情的起伏,展开持续串波澜壮阔的笔墨变革。就像音乐的重音和轻音,始终在交杂穿插地鸣奏,这是写手卷最须要的技巧。
柳公权《蒙诏帖》
到了宋代,黄庭坚用安定悄悄的行书写手卷,实在也是暗流彭湃的,他给苏东坡的题跋不得了。其余还可以不雅观阅辽宁博物馆藏陆游的《自书诗卷》,还有便是南宋赵孟坚的手卷,他们都写得高低起伏。至于写成单字排列的形式,一贯到清代人才这么写的。
赵孟坚《行书自书诗卷》(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