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即是一个地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这种地域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空的地域性。其地域背景,最初局限在崆峒地区。随着历史遗迹的不断创造和全国至少5-7处崆峒山的涌现,逐渐放大到平凉地区,之后又延伸扩大到同属陇东的庆阳地区,乃至更远的省市,平凉文化成了这一期间崆峒文化的主体。崆峒文化的地域背景随着玄门的迅速传播和发展,已经拓展到了平凉周边地区和天津、河南、广东、江西、浙江等广大地区,崆峒文化便是在这样的地域背景上发育、形成的。关于崆峒山的真假之争,除《尔雅》《庄子·在宥》和《史记》等文籍记载外,清代张伯魁《崆峒山辨》有“崆峒无可考,地之东西可考也;崆峒可假借,笄头、萧关不可假借也。”“今考史相方,则黄帝、广成之迹其为平凉崆峒也,必矣。蓟与汝俱不得而冒,别的四崆峒又无容冒也。”他以地理位置来回答不容质疑。二是内容和风格的地域性。首先为民情风尚的地域性。其反响的都是崆峒古代地域所发生的事情,都是西北边陲多民族聚拢区、中西方经济文化搜集地特有的社会生活及其民俗风情。其次为自然环境的地域性。其最突出的特点因此崆峒山为载体和凭借,崆峒胜景以山峰为主体,关中文化古迹遍布于层峦叠翠之间,琳宣梵刹以及浩瀚的碑碣石刻,砖塔摩崖,奇洞石客,多达七十余处。这种独特的文化景不雅观,既张扬了自然景不雅观的魅力,又永葆了深厚的人文景不雅观秘闻,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加之历代文人骚客以崆峒特定的地理环境为背景,赋陇上、萧关之雄壮,写边地景物之苍凉,发戍边壮士之悲壮,逼真生动地展示了崆峒地域的壮丽景致、人文环境。再次为方言词汇的地域性。其拥有大量崆峒及其周边地区独特的方言词汇。这是崆峒公民社会心理的长久积淀,是民间思想最朴素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一种语态,也是地域文化的一种分外载体。他承载了崆峒公民对生活、对社会、对自然的独特感悟,反响了崆峒公民的人生不雅观、代价不雅观、乡情乡俗、履历教训和喜怒哀乐等情绪,表示着地域认同感和地域凝聚力,构成了崆峒文化的措辞特色。
二、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这种生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因地气丰沛而千秋兴盛。南北走向的陇山是古都长安和关中大地的西大门和樊篱,崆峒山周围自然也具有这种不可替代的、分外的浸染。《尔雅·释地》有:“空同之人武”,晋郭璞注云:“地气使然”。崆峒人英武俊杰,是“地气”环境的造就。气,乃古代文化中一个主要的观点。东汉王充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气,是极细微幽深的东西,是构成天下万物的本源。崆峒为何千秋兴盛,其根由是“地气”丰沛,也便是老百姓所说的“风水宝地”。二是因美景机缘而充满活力。崆峒文化是在其范例的生态环境中发轫、发展的,它依存的崆峒山,西接六盘山,东望秦川,南依关山,北峙萧关,泾河与胭脂河回护前后,是由上三迭系紫赤色坚硬砾岩构成的丹霞地貌,总面积83.595平方公里。国务院第三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关照中有“区内有气势磅礴的马鬃山,奇特的喷鼻香山胜景,幽雅新奇的五台风光,神秘的玄鹤洞,引人入胜的弹筝峡、月石峡,风景旖旎的胭脂川等自然景致。”崆峒文化因这样的美景机缘,而拥有无尽的生气与活力。三是因关爱生态而不断勃发。崆峒山分外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为植物、动物生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明代《平凉府志》《崆峒山志》,都对崆峒山“物产”有记述。当代高维衡《崆峒山植物志》认定的植物有1000余种,其植被有光鲜的古老性和过渡性特点。赵明星《崆峒山动物》记述的动物有270种,种类、数量繁多的动物资源是崆峒山的主要基因库之一。当西方文化把其触角伸入大都邑,矗立起高大森严的教堂时,而中国玄门、佛教则走向烟霞弥漫黛青色的山林深处,精神生命与自然生命相呼应、同勃发。崆峒文化作为中华大地上范例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范例,当之无愧。
三、高度理性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佛教文化的传入增长了崆峒文化的无限魅力。古丝绸之路东西方交往,无非是精神和物质两大类。本日,物质交往的遗存已所见不多,但精神交往的遗存险些全息性地保留下来。崆峒文化自始至终受佛教文化影响,与其他文化比较,明显地富于理性和精神性。诸如,其更加看重人的精神天下的探索和描述,更加看重人的思想、意识的开掘和心灵的塑造。这种超然物外的空灵之美,让崆峒文化充满无穷魅力。二是活灵巧现的道文化印记增长了崆峒文化的神奇色彩。从崆峒山的两个生态徽记来看,站立在招鹤堂的“紫果云杉”,千年古树,松身柏叶,果实金黄,形似孔雀开屏,山上仅存此一株,在大西北是非常罕见的;玄鹤作为崆峒文化中非常刺目耀眼、亮丽的意象。东台绝壁有玄鹤洞,传说鹤栖息个中。中台建有招鹤堂,鹤是人们神往的图腾,道是人们企求的行为准则。元鹤,是大地的宠儿,与天地同成长,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生动表明。象征高洁、吉祥、俏丽,也是道所涵盖的境界。人们登临崆峒, 显性的是在视角层面上以希冀看到元鹤为幸,而隐性的则是在精神层面上发自心灵深处的悟道、得道。数千年纪月匆匆而逝,但崆峒山依然巍峨葱茏,笄头山风采依旧,回中古道旧貌换新颜,不变的是崆峒文化熠熠生辉的精神内核,越变越好、越变越美的则是崆峒山下、泾河渭河之滨的这片大好河山。
四、崇高唯美的艺术文化。这种艺术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范例的自然与人文完美契合的艺术。既有大自然的造化,也有人文胜迹,二者相契合,共融于一体。其八台、九宫、十二院、四十二座建筑、七十二处石府洞天中不可胜数的碑碣、石刻、雕塑、彩绘,都是人们长期心灵创造与文化积累的结果。东南折曲而下的乌青山脊上,沿山形走势建造的雷神庙宛若冷却的雷电,四面风来,天摇地动,仿佛立于訇訇的雷声之中,奇妙神奇至极。东西南北中台如莲花绽开,法轮禅寺矗立个中,颇有大唐遗风。崆峒山是一座天造地设人为的伟大建筑。“秦始皇西巡崆峒登笄头山”“魏征梦斩泾河龙”“姜子牙钓鱼渭河上”“柳毅传书”等已成为随处颂扬、妇孺皆知的千古嘉话。无论是道学、玄门发祥的古遗址,千古人物游踪以及保留下来的诗词文赋,都形成了一种极其范例的自然与文化契合的审美艺术。二是崆峒壁画艺术成绩空前绝后。崆峒山老君楼壁画特殊是“八十一化图”在壁画艺术上达到了空前的境界。壁画非常纯熟和精练的利用了色与线技艺,对人物的行、住、坐、卧等举止言谈从面部、眼神、姿态、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局部情节与主体人物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展示,表现出人物发自心灵的神采风情,塑造了富有艺术生命的人物形象和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创造了中国式的写实风格。三是古丝绸之路文化的刺目耀眼明珠。清代江皋在《崆峒怀古》中描述了黄帝问道与广成子修炼是相互关联映照的两个意象。历代文人骚客的作品也浩瀚如星辰,李白曾有 “世传崆峒勇”。杜甫借崆峒山既写国事时局,又写朋友境遇,还写赞词;“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笔下的崆峒景境高远,气韵畅快,淋漓尽致。当代肖华的诗词、《剑横崆峒》电视剧、《魅力平凉》拍照、《崆峒圣境》壁刻粉本和《崆峒山神话故事》以及以崆峒古镇为主体的文化家当开拓等,从历史遗存、本土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和旅游不雅观光文化,多方面多层次地崆峒文化培植,已成为丝绸之路文化残酷的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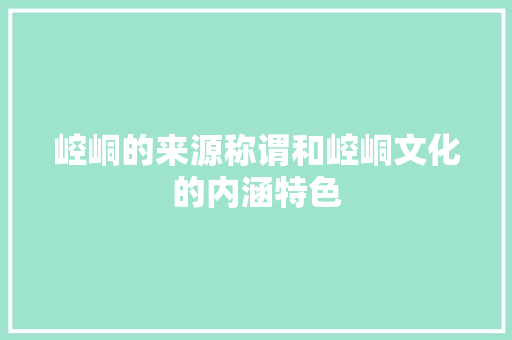
五、原谅开放的多元文化。这种多元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量的北方各民族文化元素。《尔雅》“北戴斗极为空桐”解释北斗星下面的一大片地方是崆峒。《汲冢周书》阐明为“正北的大夏、莎车、戎翟、月氏、空同”等十部族统归空同。浩瀚北方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先秦的戎族,如乌氏戎、卢人、犬戎、义渠戎、混夷等;汉魏的羌族、氐族;唐宋的吐蕃、党项;元明清以来的回族等。虽然历史上这里生活过许多少数民族群落,但汉民族一贯是该地区人口的主体,汉文化一贯在其经济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浸染。浩瀚北方民族在这里交错杂居,长期共处。各民族文化在崆峒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反复碰撞,终极走向领悟。最范例的是全国最大的“完颜部落”—泾川县王村落镇完颜村落金兀术的后裔们早已结束了马背上的生涯,与当地的汉民族相领悟,从事着农耕生活。女真族的后裔们在当地汉族人的收受接管下,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大超过。二是大量的中原文化元素。崆峒文化的基因来源于中原文化。崆峒族活动的区域,正好处在羌人文化的中央地带。崆峒山为六盘山之余脉,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伏羲,是渔猎社会时期的领导者。而渔猎社会的生活,是由西北高原即黄河上游流域渐次发展的。崆峒山周围数百里是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伏羲、炎帝、轩辕 都先后在这片热土上出身、容身或埋葬。这是伏羲为中华人文开山祖师的根本意义所在,也是黄帝问道于崆峒的根源所在。崆峒文化的源头在中原,是中原文化在崆峒本土文化的土壤中发育、发展起来的。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接管中原文化的营养,使各个期间的崆峒文化,都融入了大量各个历史期间中原前辈文化的元素。三是大量的宗教文化元素。崆峒山道释儒三教合一的“三教洞”便是最好的例证。这是有别于其他名山的独特征象,这种“集大成”文化充分地反响了“和谐”思想,这种道佛儒并存,人与自然的领悟,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是崆峒文化的灵魂所在。
六、以道家文化为主导的和谐文化。这种和谐性,表现在:崆峒山是三教合一共尊共荣的宗教摇篮。它以玄门为主宗,传说容成公、赤松子与广成子一起修炼,在西周有长桑子、韦震修炼。《史记》《庄子·在宥》都记载黄帝在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的史实,阐述“道”乃无形无象,无为而无不为,达到无欲之境,回归生命的本体,倡导“抱神以静”的人生不雅观,认为人与自然界实质上是相通的,人性与神性通过对话,理喻泰否、祸福、损益的乾坤运行变革,从而倡导“阴阳有藏”的天下不雅观。认为养生是“至道”的根本,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进行“外丹”和“内丹”的修炼,以求人体生理、生理与精神的和谐统一,从而倡导“以处其和”的生命代价不雅观。南怀瑾《禅宗与道家》中有:“黄帝曾经拜过七十二个老师,遍学各种学问,末了西上甘肃的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 “那么广成子,便是集个中国文化大成的意思。”可见广成子和崆峒山都是独特的文化元素。秦汉期间黄老盛行,秦始皇、汉武帝拜访崆峒。唐代已有问道宫,北宋建真武殿,天圣七年,羽士陈宗秀与铜匠陈训铸天圣铜钟,后有披云真人游居并著书。明代羽士张三丰在此修道五年,清初龙门洞羽士苗清阳前来住持重修皇城,将崆峒列为全国玄门十二大常驻之一。佛教也很兴盛,以中台真乘寺为中枢,建有文珠庵、七佛阁、弥陀庵、茶庵寺等佛寺。加之 “三教洞”,在飞仙阁上数十步,洞内奉祀老子、释佛、孔子彩塑坐像。玄门以“有容乃大”的胸襟,领悟“和而不同”的佛、儒、道,创意地构建了入世、出世、超世的灵魂栖地,提升了崆峒玄门文化的品位。
七、向善守正的正道文化。这种正道性,表现在:处于拱卫帝京和边关沙场分外地理位置的崆峒地区,在其成为各种军事力量争夺的焦点的同时,也匆匆使公民养成了崇尚勇武、大胆善战的传统习气。《汉书地理志》所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切近亲近蛮夷,修习战备,高尚力气,以射猎为先。”西方的宗教绘画中不乏痛楚、邪恶、血腥等悲剧性题材,其世俗绘画中也有很多悲观主题。但在崆峒山和其附近的南、北石窟寺的塑像壁画中却很少看到这些东西。在崆峒文化的发育过程中,也有过战役、屠戮、贫穷、饥饿等,但其文化的基调和内容永久是康健向善、从容乐不雅观、积极向上的。无论崆峒山外的自然环境怎么变换、何等严厉,崆峒山内总是色彩万千、活力无限,山内山形状成巨大的反差。崆峒文化淋漓尽致地表示在其玄门、佛教活动中,《礼记·曲法》有:“斋者,精明之至也,以是交于神明。”讲究养生修炼,表示了道源深厚,玄风广被的风采。佛教仪规殊胜庄严,庙会尤为精彩。“四月八”佛诞节,天南海北数万僧众云集,同唱佛宝赞佛偈,“九龙口吐喷鼻香水”洗澡佛像。“七月十五”盂兰盆会,佛教徒为超度先人亡灵所举行的仪式。《梵网经》有:“孝名为戒,亦名制止”“孝顺至道之法”。崆峒武术也是用于健体防身,《尔雅·释地》之“空同之人武”,因此广成子“抱神以静”“阴阳有藏”为魂魄,善于“雌雄剑”“落魂钟”,善使“番天印”,山上宫不雅观悬挂“混元鞭”“蛟龙鞭”“镇山鞭”等等,透示一种神武之气,给人以阳刚和力量。千百年来,崆峒公民便是这样自始至终惊人同等地坚守着崆峒文化的正面性代价,在不断地过滤勃发中,崆峒文化所积累的永久是向善守正的正能量。
八、与时俱进的动态文化。这种动态性,表现在:崆峒文化的地域背景是动态的,它由最初的崆峒山周围,逐渐放大到东起河南汝阳,西至甘肃河西地区,后又拓展全国六、七个省市。崆峒文化的时限是动态的。其时限延续,已经延伸到远古期间。不仅有三皇女娲夸父出身地之传说,而且有远在新石器时期晚期崆峒山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1984年崆峒山管理所在崾岘至中台建筑所址时,曾挖掘出属于新石器晚期仰韶文化的墓葬,并出土了当时人们利用的陶器。崆峒文化地域背景和时限延续的不断变革,决定了对崆峒文化的体系构造无法一次性定型,只能在不断创造、挖掘、研究的动态行为中使之逐步充足和完善起来,这种动态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连续,这也是崆峒文化的无限魅力和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总之,崆峒文化与一样平常意义上的文化比较,在文化形态的布局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常见的方法只把文化设计成“靶环式”布局。即以一种文化为核心层,其他文化依次分层环抱在外。在社会构造不断扁平化的趋势中,这种“靶环式”的文化布局,随意马虎在客不雅观年夜将一些小文化边缘化,形成利害之分。崆峒文化打破了“靶环式”布局,而成为像奥运会徽标那样的“五环式”布局。奥运会徽标最实质的内涵是平等、和谐。崆峒文化的“五环式”布局表示的正好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和谐。崆峒文化讲差异,但不讲利害,作为集大成者,它保留不同文化的独立性,又表示不同文化间的互换领悟。这种文化构造是历史形成的,但却有着范例的时期特色。
来源:市舆志办/朱克雄
制作:中共平凉市委网信办
审核:雷勇 李一宁 杨涛
编辑:邓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