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难行 先行狂狷
这一章是孔子讲“中庸之道”。
“中行”的“中”便是“中庸”,中庸是圣德;
“行”是依照中庸之道而行,这叫中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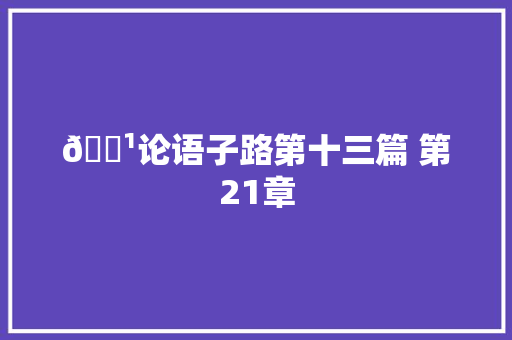
中庸之道,是贤人所行的道,大略来讲,叫“无过无不及”,但是这个境界很高,凡夫达不到这个境界。
佛法里也讲中道,“中道第一义谛”,不仅凡夫做不到,二乘人也做不到,阿罗汉、辟支佛都达不到。
凡夫偏在有,二乘人偏在空,都不是中道。空、有二边都不落,你要落了个中道,也不是中道,以是“中道也不存”,才是真正的中道。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李炳南先生长西席在《论语讲要》里引北宋大儒邢昺的《论语注疏》说,“中行,行能得个中者也”,能够依中庸之道而行的人,
“言既不得中行之人而与之同处”,这样的人很难找到了,“与之”便是与之同处,有称许的意思,
“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这是求其次,得不到一个行中庸之道的人,得一个狂狷之人也行,也值得称许了。
“狂狷”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李先生长西席引包咸的批注说,“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有所不为也”,“狷”是“守节无为”的意思,这个人很谨慎、很小心,与狂相对。
狂者、狷者,两者都不符合中道,都是落二边,但是这二边都是好的。
“狂者”有进取心,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儿狂妄,可能口气很大,有些志大才疏,眼高手低;
“狷者”有所不为,他所不为的是不善的事情,他以不善的事为耻,他有可耻之心,“行己有耻”,以是他有所不为。
这两者并不是不好,只是没有中道之人这样难得,他们还不是贤人,可是也难能名贵了。
换句话说,我们想要达成贤人,“狂狷”这两个方面我们也该当做到。
“狂”是进取,我们要立志,立志成圣成贤。没有这个志向,我们永久做不到圣贤。以是,甘心有这个志向,虽然我们还达不到,好过我们做得很好,但是没有志向。
“狷”是我们能够负责修行,有所不为,知道哪些错了,就不要去干了,改过悛改,去世守善道。
狂为进取 狷为有耻
蕅益大师批注说,“狂狷,便是狂简,狂则必简,简即有所不为。有所不为,只是行己有耻耳。孟子分作两人阐明,孔子不分作两人也。若狂而不狷、狷而不狂,有何可取?”这个评议好!
蕅益大师讲,“狂简”便是“行己有耻”,有耻心,以是有所不为;如果任意妄为,便是不知耻。
孟子把“狂狷”当作两人,实在不是,孔子真正的意思,蕅益大师给我们点出来了,该当是一个人,同时具有“狂”和“狷”。如果分成两人,狂是狂,狷是狷,狂而不狷,狷而不狂,这有何可取?
如果一味地去狂,任意妄为、胡作非为,当然不可取;
如果一味地去狷,什么事都不敢做,懦弱、自卑,没有进取心,这两种人,都不可能成为圣贤。
以是,孔子所说的“必也狂狷乎”,这个人是可取的,正是由于他具有“狂”和“狷”这两方面的性情。
“狂狷,便是狂简”,“狂简”这个词出自《论语》第五篇,“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孔子在陈国的时候,他思念家乡了,就说归与归与,回归鲁国吧,“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以是裁之”。
“吾党之小子”,“党”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便是讲孔子的弟子们;“狂简”,他们都很有进取心,他们有所不为;
“斐然成章”,他们写的文章已经相称不错了,可以阅读,很可不雅观了。
但是,“不知以是裁之”,他们还没有悟来岁夜道,以是不知道若何来裁定,也便是说,他们的功夫还没到家。但是,他们已经具备“狂狷”这个成圣成贤的根本了,只要孔子回去点拨、教养他们,他们就能得中庸之道,就能成贤人。以是,孔子在陈国的时候说要回去了,他念念想着弟子们,希望帮助弟子提升。
孔子说,得不到有中庸之道的贤人,能够得到“狂狷”的人也很好,孔子为什么这么说?蕅益大师引《孟子·尽心下》篇里,孟子跟弟子万章的一段对话,把这个意思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从这里去体会圣贤所讴歌的人品是什么样的,不讴歌的人品又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可以学习和反省。
“万章问曰”,弟子万章问孟子,“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
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
孔子在陈国的时候说,“盍归乎来”,何不回家呢?我的那些学生,“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他们的志气很大,很进取,但是有一点志大才疏,有一点狂妄,我须要回去调理他们,“不忘其初”,他们很难得,没有忘本。孔子在陈国的时候,为什么会思念鲁国这些狂简之士?
孟子回答说,“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孔子哪里说不想得到一个有中庸之道的贤人呢?是弟子里面没有,“不可必得”,得不到,以是“思其次”,次一等也好。
万章问,“敢问:何如此可谓狂矣”,什么人叫做狂?“狂”是指狂放的人。
“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孟子举出孔子的三位弟子,这三位弟子狂放。
万章问,“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孟子说,这些人的志向很大,“嘐嘐然”是口气很大的样子。“曰:古之人,古之人”,这是孟子在演出他们说话,他们的嘴里总喊着古人哪,古人哪,“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夷是语气助词,没故意思,便是“考其行”,如果你去稽核一下他们的行为,“不掩焉者也”,与他们的言语并不相符合,便是说得很大,行得不足。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与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如果得不到狂放的人,这是孟子把狂者和狷者分开了,这不是孔子真正的意思,但是孟子也引出了一个更好的意思,“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与之,是獧也”,在孟子的眼中,认为“狷者”是“洁身自好的人”,有所不为,对付不净洁的言行心态,他不屑去做,这是狷者,属于又其次了。实际上,狂者和狷者这两个是一不是二,该当合在一起,当同一个人来讲。
底下才引出真正的意思,孟子又说,“孔子曰”,孟子引孔子的话,“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
乡原,德之贼也”。
孔子讲过,经由我的家门,却不进我的屋里来的这种人,我并不遗憾。这种人是什么人?什么人孔子不以为遗憾?“乡原之人”,便是现在所谓的“好好师长西席”。“原”是谨慎的意思,原通愿,有的也写成乡愿,这种人表面上看起来虔诚老成,干事很谨慎,像个老迈大好人,实际上内心里却是有欺世盗名之心,孔子称这种人为“德之贼也”,“贼”便是偷,偷道德的人。由于这种人,每每看不出他的不好的一壁,挑不有缺点,但是他又不能够真正树立一个好的风尚,以是叫德之贼,孔子不屑一顾,过我门不入我室,就随他去,孔子根本不会理他,也不会遗憾。
万章问,“曰:何如此可谓之乡原矣”,什么人叫乡原?“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作甚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
“乡原之人”,这些所谓的好好师长西席、老迈大好人,他们会批评那些狂者,“何以是嘐嘐也”,你们为什么要讲大话?由于狂者比较喜好说“贤人这样讲”,“古人这样讲”,以古人为榜样,但是他自己没做到。以是好好师长西席就批评他们,你为什么这么大口气?“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你们的言语与行为不能相应,“则曰:古之人,古之人”,动不动就讲古人,这是孟子学着乡原之人的口吻来批评狂者。下面是批评狷者,行为谨慎,有所不为者,“行作甚踽踽凉凉”,“踽踽凉凉”是孤独的样子,“踽踽”是独行而不进,他们不能进取;“凉凉”是很冷漠,狷者由于有所不为,他爱独善其身,以是给人的觉得彷佛有点儿冷漠,自己干自己的。这些老迈大好人,他也去批评这些狷者,你们为什么这样落落寡和?不能够跟这个天下融成一体?“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你生在这个天下上,该当为这个天下做点事,怎么能够独善其身,自己好就行了呢?
这些好好师长西席,彷佛八面玲珑,狂者、狷者他都批评,显示他便是最好的。以是孟子说,“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阉”是指寺人、阉官,这种人每每给人一种巴结奉迎的印象,“阉然”是形容爱巴结奉迎的样子,他是“媚于世”,奉迎众人,让众人以为这个好好师长西席什么都好。
万章问,“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这话问得好,乡里的人都说这个人是好好师长西席,跟所有人的关系都不错,“无所往而不为原人”,“无所往”便是到处,到处他都是一个年夜大好人,人家都说他好,他谁都不得罪,“孔子以为德之贼”,孔子反而说他是德之贼,这是为什么?
孟子回答说,“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这种人确实连狂狷之人都比不上,他是“非之无举也”,“非之”便是你要批评他,彷佛又举不出什么事例,他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他也不得罪人;“刺之无刺也”,“刺”便是你要责怪他,要讨伐他,可是又挑不出他的毛病,“无刺也”,没什么可责怪的。“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与世上的人与世浮沉,随波逐流,以是大家自然就觉得他好,由于他能随着大家的意思。可是世上的人,大部分都是“流俗众,仁者希”,这种好好师长西席“不能够移风易俗”。“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居之”是他的为人彷佛很忠实、很诚信,“行为”看起来又彷佛很廉明,“众皆悦之”,大家都挺喜好他的,“自以为是”,他还自己以为自己不错,这种人“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他的所作所为与圣贤之道反而是背离的,以是孔子讲这种人是德之贼,这种人真有。
真正学习圣贤之道的人,不能以世俗之心为心,便是不能用世俗的代价不雅观,作为自己的代价不雅观。如果我们以世俗的代价不雅观,作为自己的代价不雅观,就肯定跟众人都打成一片。但是众人的代价不雅观是什么?贪嗔痴慢、好名好利,我们也就随波逐流,当然“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虽然我们没能做到像圣贤这样的一种境界,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个进取的人,做一个狂狷之士,“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我们不想只为自己活着了,有所不为,做一个狂狷之士也不错。孔子说,这种人也能够做弟子,虽然境界不高,但是逐步地,末了也能够达到圣贤境界。如果是随波逐流,在这个世间去流落,大家都说你好,你也很孝顺,经济也不错,再给你找一个很好的配偶,将来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各方面都跟众人一样,大家都这么做,你也这么做,这种人,孔子认为是乡原之人,德之贼也。
“孔子曰”,孟子引孔子的话,“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孔子说,他厌恶那些似是而非的人和事,当然,孔子不会真的厌恶谁,他是不与他们打交道,换句话说,孔子不会收这种人做弟子。我们关键是要想想自己,我们会不会落到这种人当中?
“恶莠,恐其乱苗也”,“莠”是禾田里的杂草,与禾苗长在一起,长得还有点儿像,但是它结不了稻谷,反而把土里的营养给吸走了,这种东西是值得厌恶的,要把它锄掉。
“恶佞,恐其乱义也”,“佞”是很会说话,所谓辩口利辞、夸夸其谈,讲的彷佛都是大道理,实际上,他不符合道义。如果我们不能用聪慧辨别,以为他讲得条理分明,很有道理,信以为真,就会被他害了。
“恶利口,恐其乱信也”,“利口”也很会说话,与佞的意思差不多,讲话讲得很多,喜好夸夸其谈,但这种人没有诚信。没有诚信的人,每每会说这类话,“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口头上爱说诚信,实际上反而不诚信。真正诚信的人,反而慎言,没有那么多的山盟海誓,没有那么多的承诺,但是“言必信,行必果”。
“恶郑声,恐其乱乐也”,“乐”是雅乐,美好的音乐;“郑声”,是当时郑国的音乐,孔子斥之以淫乐,靡靡之音,这一类音乐听了让人精神不振,乃至神魂颠倒,以是说“郑声乱雅乐”。我们要听正乐,不要听淫声。
“恶紫,恐其乱朱也”,“朱”是赤色,是正色,紫色与赤色很相像,殽杂在赤色里,反而使正色不显了。
“恶乡原,恐其乱德也”,这才是讲入了正题,乡原之人,所谓的好好师长西席,这一种人是德之贼,他会败坏社会道德风尚,他不能坚持原则,不能鼓励正道,只是随波逐流。
孟子说,“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是正道,“反”是返回,君子是回归到正道而已。“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天真慧矣”,经正了,回归到正道上了,老百姓自然就振作起来了。以是,圣贤在世间,他的浸染在于移风易俗,导民以正,而不是随波逐流。他能为世间做一个好榜样,“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乃至他是反众人之道而行。譬如众人都贪财,他就演出一个舍财的样子;众人都追求名利,他把名利统统放下;众人都追求享受,他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众人都崇尚所谓的拜金主义的代价不雅观,他崇尚的是“利他忘我的代价不雅观”。这是“回归正道”,这是“符合性德”。我们如果能真的这样坚持,老百姓们逐步地就能看出来,为什么?人皆有好善好德之心,“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给他演出善的样子,他一开始可能不理解,他乃至会诬蔑、批评我们,可是过一段韶光,他看看我们做的是对的,他就会对我们佩服,会向我们学习,这便是“庶民兴”,大家就振作起来了,回归善道,这是“贤人移风易俗”。
孔子当年,他提倡仁义礼智信,道德仁义,这是伦常大道,当时没人接管他,可是他一味地去实行,他一辈子没有得到重用,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用他的学说。可是,到了汉朝汉武帝,董仲舒推举儒家,汉武帝就把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正教,正式的教诲,之后所有的官员考试都是用儒家的学说。孔子的圣贤之道,没想到在汉朝,几百年往后被重用了,以是那个时候才庶民兴,才振作起来。以是贤人无怨无悔地去努力,但问耕耘,不问收成,总有一天能够将这社会导正。“庶民兴则天真慧”,就没有邪恶了,这个社会必定是回归和谐了。以是,孔子以为可取之人,该当是狂狷之人,他们末了也能够造诣圣贤之道。但是,须要圣贤、善知识的教导,以是孔子说他要从陈国回到鲁国去教自己的那一批学生,他们都有很好的根基,他们都不是乡原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