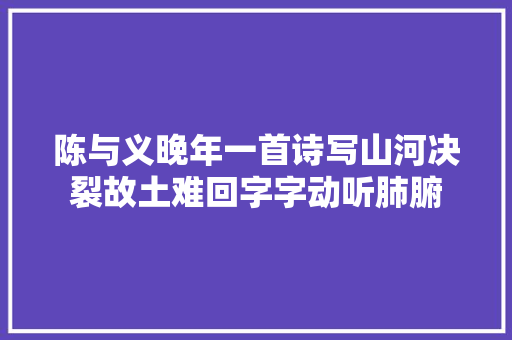提到陈与义,我们最先想到的该当是他的《临江仙》。这是他在晚年退居青墩时追忆过往光阴写下的,“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往事如烟,如此美好,此时回望,物不是人也非,只令人久久怅惘。
除了这首《临江仙》,陈与义晚年还有一首《咏牡丹》也值得一读,诗仅4句,将人到老年,面临山河破碎、故土难回的思乡之情写得动听肺腑,令人唏嘘不已。
《咏牡丹》
宋·陈与义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诗同样写于他南渡后居住在青墩时,此时距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恰好10年光阴。前两句用沉痛的笔调写出这一背景:间隔金人入关,已经10年纪月,可我回望故乡洛阳,却依然是长路漫漫,归期无望。
异域十年,山河破碎,故土难回,满心无力,失落望痛楚。现在我们很难再体会到这种情绪了,但当时的陈与义,却是怀着这样满腔难言的痛楚情绪,只能靠诉诸诗文来排解。
后两句写自己身在异域,已经老去,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立在东风之中,看那青墩溪畔的牡丹花开,想着迢遥故乡的牡丹花开。
墨客思乡,都有寄托,或是天上的明月升起,或是秋风乍起,黄叶飘落,在此时的陈与义眼里,是青墩溪畔绽放的牡丹花——看到它,就想发迹乡,由于故乡这时节,也开遍了牡丹花吧。
可哪里又只是牡丹呢?漫永劫间里,墨客或许有无数次面对着明月、秋风、花开与叶落,想起自己的故乡,想回不能回。可还不但是故乡,还有国与家,以及那过往的再不能回的岁月。
字里行间,我们能读到墨客深切无尽的思乡之情与沉郁难遣的家国之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