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后住在天津老城的城西义和斗店、孙家大院、吴家大院等处,也有时常住宜障后。当时他以剃头为业,是住在很多人伙居的小店儿。白天出去串胡同剃头,晚上休闲时唱上一段在家乡喜好的大鼓书消遣。在屯子种地时,他边干活边哼着小曲,已经学会了许多小段和长篇鼓书,像什么《刘公案》、《拆西厢》、《洪月娥做梦》等。当时下层的贫苦百姓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故此他唱的大鼓深受伙伴们的喜好。有些人听得韶光长了,以为大家生存都不随意马虎,白听也不得当,有时就主动地多少给些零星钱。随着不雅观众不断增加,攒起来的零钱反比剃头赚的钱还多,以是他也就逐渐地以唱大鼓作为另一条谋生之路了。由于平时总唱,自己也就自然地久练久熟了。自此往后他带着大鼓走街串巷演唱,常常活动在大沽路的小营市场一带。
“撂地”演出的条件很差,支个大布篷,用木板钉上几条板凳。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刮风一半,下雨满完。”刘文彬还常说:“人歇工,牙挂队,肠子肚子活受罪。”由于刘文斌没有江湖门户,进天津城后曾受到城里的艺人和地头蛇们的排斥,在演出时被人家踢了场子搅局,还没收了大鼓。这是由于他没有江湖师父带道,也不睬解“春典”(江湖术语)与他们盘道。在天津城干这行是不成了,只好回到店中向老乡们告帮。
要想再干这行就必须拜师,他带着行李回到宝坻后通过老乡先容,在庙会上拜了宋恩德先生长西席为师。宋师长西席还专门向他传授了艺人们用的“春典”、门户规矩,据回顾他还在庙会上请了许多艺人们吃了一顿驴肉、烙饼,花去了他整整一年赚的钱。宋恩德先生长西席是个半盲人,外号叫“宋瞎糠”。按辈分刘应是“文”字辈,取艺名叫“文斌”。刘文斌的这一支祖师是“梅”家门,排字是按“继、承、龙、元、玉、唐、文、书、化、其”。刘文斌的同辈师兄弟很多,天津的齐文洲、李文俊、唐山的靳文然、齐文丰、刘文迅等都是“文”字辈。
经由一番周折的学徒之后,刘文斌闯过江湖关后又再到天津献艺。这时还结交了许多各行艺人,又进一步地开阔了艺术眼界。他对京东大鼓的演唱进行大胆改革,先把上场的那一句唱词抹去,改为:“表的是……”开门见山,直接入活。在简洁的根本上再加上嗓音宽厚,字正腔圆且韵味十足。通过不断演出,还固定了许多基本唱腔。加上他演唱的曲词准确、通畅,在唱腔方面还接管了一些屯子小曲、地头调。他还有一种唱法,便是接管老学究儿背诵古诗词的平仄韵味,这种演唱嗡声嗡气,用的是背工嗓(头腔兼脑后音),被人戏称“坛子大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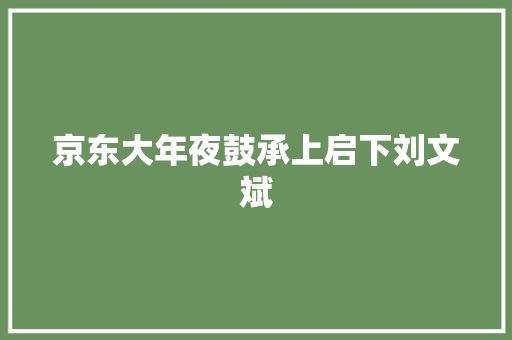
这时他除了搭布篷“撂地”演唱外,还坚持走街串巷,进大宅门、私邸演唱。他说第一次演唱是和师弟李文俊去答允的。当时是阔家主人点唱,点了他师弟李文俊一段《罗成算卦》,正巧他师弟不会唱这段。李文俊则推举师兄刘文斌代唱,主家不愿意,便拿刘文斌愉快,说;“他长的那样子,哪能唱得了呀?”当时刘文斌正有病,穿着也不讲究。后来经别人说情,还是让他唱了。头几句京东大鼓唱得声音洪亮,各个楼里和附近的人都围拢过来,掌声不断。大家都交头接耳问唱者是谁?因此刘文斌的名字不胫而走,响彻津门。
后来听他的人越来越多,请他演出的戏院也越来越多了。过了一段韶光广播电台约他长期直播演唱,因演唱技艺博识被电台长期任命。通过广播,刘文斌声振天津以及北京、河北等地。当时天津的广播电台都是私人开设,有“中华电台”、“仁昌电台”、“东方电台”、“青年会电台”。这些电台都是为商业做事,电台开播之前都由演员播上一段商品广告。那时经刘文斌报播的广告有延寿堂的药品广告:“调经养血,一元钱。白喉蛾子,一世福,一家乐。”同时还先容天津东马路药店的生乳灵。
当时经济大战,也都利用电台宣扬商品增加效益,在把商品推出去的同时,也把演员推上了市场。当时拥有收音机的人家很少,有的大买卖家为了招揽买卖,店铺门口放一个大喇叭,每逢早晚,人们都到店铺门前听刘文斌演唱。有的干着半截活把活停下来,也有的正在生着炉子,因听唱把炉子给弄灭了,拿板凳坐店铺门前听。
这时刘文斌红了,京东大鼓的名声在天津也越来越大了。由于他的演唱有独特的风格,词曲又普通易懂,适宜广大贫苦市民听众接管,尤其是那些反响家庭生活的唱段,深受城乡妇女们的喜好。由于他演唱的曲目中,在描写爱情以及平民生活中的悲、喜情节方面特殊见长。这些曲目能像谈天叙家常那样自然朴实,也有些警众人生富有哲理的曲词。后来在茶园演出、电台播出频繁的情形下,对方问他唱的是什么大鼓?刘文斌坦诚地说:“我们是京东人(京东是指通县、三河、武清、宝坻、蓟县、喷鼻香河、宁河等县),就叫京东大鼓吧!
”这便是“京东大鼓”之名产生的经由。
刘文斌唱红津门之后,随之也就有了些关于买卖上的抵牾,按刘文斌的话说:“树大招风了!
”这是由于他的节目受到听众欢迎,同时有“中华”、“仁昌”两个电台抢着让他演唱并申报白。“中华电台”要给他提高播出费让他只在此独家电台演播,并说要付多出几倍的报酬。刘文斌为讲信义,毅然谢绝了“中华”的哀求。他坚持在“仁昌”、“中华”两个电台演出,因此引起了双方电台抵牾和冲突。“中华”为了抢他,利用地痞帮派势力给刘文斌写了几封匿名信,并在每封信中都画着小刀子,写着要杀去世刘文斌,曾经在一天里接到了40多封信。这样一来,闹得一塌糊涂,空气十分紧张。
刘文斌再也无法去演唱,于是和同行们商量,他们发起找延寿堂的乐老板商谋对策。这位乐老板是河北省大城县人,在天津做生意多年并且还有些威望。他反复考虑后说:“我去外边走动走动,拜求各方看是否有转机。假如不造诣也只能回老家宝坻县再谋生路,天津卫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了!
”他还把刘文斌留在后院暂避,亲自去西北角拜访王三爷(青红帮头目),要求他给予关照办理。乐老板叫刘文斌前来向王三爷陈说起因,王三爷听罢立时拿起电话向警察局说:“谁想成心生事……”接着又说了些让他们关照的话,警察局的官员们当然答应对这件事给予照顾。后来刘文斌费钱宴客才平息了这场事端,连续在两家电台演唱。
在他演唱的兴盛期间,正是奉军驻守天津。由于刘文斌唱的是略带乡音的普通话,与东北的方言随意马虎沟通,以是这些东北人也特殊喜好京东大鼓。随着他的艺龄增长,在演唱技艺方面也不断地升华提高。又因他为人也非常朴实淳厚,能与许多艺人们同台献艺并成为良朋。
在天津曾与花四宝、张寿臣、陈士和、马连登、马宝山、翟青山、刘宝全一起同台演出,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曾在南市燕乐茶园(解放后改称红旗戏院)先后与刘文霞、常旭久、于瑞凤、程玉兰、郑蝶影、曹宝禄、高德明、陶湘如、花四宝、白云鹏、戴少甫、于俊波、侯宝林、郭启儒等一起演出。在南市庆云茶园(解放后改称共和戏院)先后与常连安、常宝堃、常澍田、金万昌、马三立、侯一尘、张寿臣、王佩臣等一起演出,从在前几园地位一贯到能攒底演唱。20世纪40年代,他在安然茶园(今称长城影剧院)长期攒底演出,此时正是京东大鼓扬眉吐气之日。
1938年,由国乐唱片公司邀刘文斌灌制唱片12张,计有《郭子仪庆寿》2张、《拆西厢》1张、《隋炀帝下扬州》2张、《庄子扇坟》1张、《王二姐思夫》2张、《刘公案》4张。唱片灌制完成发行后使京东大鼓传遍全国各地,在社会造成一定影响。有些唱片还流传于港、澳、日本等地,使之成为北方曲艺中紧张曲种之一。当时有一行专门做唱片买卖的小商贩,人们叫“放话匣子的”。他们是背着留声机走街串巷,放上唱片叫大家欣赏。常有人点名要听刘文斌的京东大鼓,因此有时在大街小巷时时也能听到他的唱段。那时是按唱片听得多少收费,36个小铜子儿能听6张唱片,60个小铜子儿能听12张。
刘文斌在天津唱红后,在各个电台的演唱应接不暇,同时还到戏院演出。他为人虔诚激情亲切且仗义豪侠,曾先容他的老乡齐文洲、魏喜庚、马宝山等艺人到电台演唱,还把自己的演唱韶光长期让给了他们。当时他们都是从屯子来的小商贩或以身为业的劳动者,生活很是艰巨。魏喜庚是宝坻县东广林木村落人,到天津做弹棉花打被套事情。他在家乡会唱平谷调,到电台演唱过《龙潭鲍骆》。齐文洲是宝坻县崔黄口乡西老鸦口村落人,原是到天津拉胶皮的搬运工,能说《马潜龙走国》。
李文俊是宝坻县崔黄口乡东老鸦口村落人,到天津是做卖扫帚的小买卖的。刘文斌不忘旧情,把自己的买卖路让给了他们并支持他们走上了艺术道路。齐文洲文化较高,虽然唱腔粗犷但说的文理性强,曲词句较为讲究。只管刘文斌让出了很多电台演出,还是有很多电台愿请其演唱并做广告。先后有“仁昌”、“东方”、“青年会”、“新中心”以及“天津分外广播电台”等,他一天要赶包到几个电台演唱,京东大鼓在听众当中自然会有巨大影响。
刘文斌的演唱能受到社会各阶层听众欢迎,这与他的弦师合营默契是分不开的。他的弦师李景山师长西席,也是他的同乡。李景山师长西席是自学成才,小时候因个子矮够不着弦子的上把,便把弦子挂在窗户棱儿上练习。他伴奏刘文斌的京东大鼓有独到之处,在演出时常常有听众给伴奏喝采。他的三弦弹奏得快、稳、准、活,且能托腔保调,尤其是李师长西席独创的跪弦弹奏“学舌”绝活。在书场演出前,他常常用三弦摹仿笙、管、笛、箫等民族乐器的演奏、合奏以及动物家禽的鸣叫,很受听众欣赏。天津解放后,李师长西席住在南开区南大道白屋子胡同良朋里8号。刘老师在幼年时他俩就搭伴演唱,几十年来没有分开过,直至李景山师长西席于1960年病故为止。因李景山师长西席病故,刘文斌也就退出舞台不再演唱了。
刘文斌的京东大鼓能受到听众的喜好,并达到日臻完美的艺术造诣,紧张缘故原由便是没来津前,在屯子有很长一段韶光的磨炼。他幼年时就爱听大鼓书,受张瘸老、霍亮的影响,已经学会一些小段和长篇鼓书,边干农活儿边哼唱,同时也买些唱本改编演唱。比起其他艺人他能识字,但文化水平并不高。有一次唱《拆西厢》时,个中有一句“咱们老爷贪赃图了贿,屈了人家的好文才。”错把“图了贿”唱成“图了有”,让有文化的人喝了倒彩,结果闹出了笑话。这一次失落败成了他的动力,一方面他又连续学习文化,另一方面在农闲或荒年旱月,去口外做些小买卖,开阔眼界闯荡磨炼。
当时北口外是古北口、喜峰口的长城以外,那时人们“常去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地方。有时骑着毛驴,有时挑着挑,带些日用小商品,如针、线、顶针、火镰、灶王神马儿、年画、皮鞭梢儿等东西赚些小钱。有时到山里田舍支起大鼓连说带唱,挣些粮食到集上换些铜钱。这样他既得到了磨炼又增加了阅历,也可赚些钱养家糊口。当时艺人演唱很艰辛,他有时连续唱五六个小时。唱得韶光长了,嗓子哑了,没有什么灵丹灵药。由于唱不出了声音心里焦急,就用听别人传的偏方,用辣椒熬水一喝便是半碗。以是他的嗓子后来变成沙哑,因此他又坚持苦练,终于练出一条利用头腔和脑后音共鸣的坛子味。这种味道最有特点,一样平常人难以模拟,由于有了这些经历给他来天津演出奠定踏实的根本。
刘文斌在来天津前,原有说评书、唱大鼓的艺人都各占一方。评书艺人张杰鑫编演《三侠剑》,木板大鼓艺人“舍命杨”说唱《呼家将》以及西河大鼓艺人朱大官等都在天津献艺。刘文斌在电台、书场演出,越来越以为曲目不足用。他有个盟兄弟见告他说:“天津到处都是财,你便是没有取财的工具,工具便是新书。”于是刘老师就自己改编创作,边看书边演唱新书,很快增加了许多新曲目。他累得头晕脑胀把眼睛都熬红了,排练后的新曲目还请名人辅导。因此他的曲目很宽,书目唱段越来越多。后来他在书场演出一个月,能做到每天唱两段从不重复。
他当时的常演曲目有《十字坡》、《双锁山》、《刘金定不雅观星》、《朱买臣休妻》、《诸葛亮招亲》、《诸葛亮押宝》、《借女吊孝》、《铁冠图》、《韩湘子上寿》、《郭子仪庆寿》、《昭君出塞》、《洪月娥做梦》、《探窑送米》、《倒娶连科》、《大西厢》、《王二姐思夫》、《罗成算卦》、《渔樵耕读》、《肃六篡位》、《隋炀帝下扬州》等上百段。中长篇大鼓书有《刘公案》、《呼家将》、《小八义》、《盗贼传》、《十粒金丹》、《回标记》、《玉杯记》等,这些都曾在电台演唱过。他生前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虽然在广播电台留有很多唱段录音,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都被破坏,现在天津电台只保留他一段《王三姐剜菜》以及那些唱片传世。
刘文斌从前没有收过专业弟子,只在日伪期间亲传一名徒弟。他按本门户传“书”字辈取艺名卢书中,三年习艺期满后颇有发展。可惜英年早逝,刘文斌因弟子去世而伤感,再加上平时演出繁忙也就没有再连续收徒。他的儿子叫刘少斌,幼年学习弹弦专门为京东大鼓伴奏,弹得很有特色颇具其父遗风。曾在电台为先容刘文斌的艺术平生,还请刘文斌的弟子们帮忙回顾刘文斌的业绩并整理出文稿播放,已辞世。刘文斌在社会上以及工矿企业的徒弟却是桃李满天下,虽然这些弟子们的唱法各有不同,确实都是向刘文斌学过艺。他的业余弟子有李承秀、董湘昆、王辑馨、刘汉武、岳金义、宋万峰、张梁、孙志华等,个中董湘昆造诣最大。
董湘昆生于1927年,原名董庆永,天津宝坻人。从1952年开始在印刷行业基层工会文工团以相声、曲艺剧、单弦、京东大鼓、清唱、河南坠子等形式进行演出。1953年参加天津广播电台业余广播曲艺组学习演唱。同年,他担当文化宫和平区工人俱乐部业余曲艺团团长。
1954年拜刘文斌为师,专攻京东大鼓。他不仅在继续老一辈艺人的唱腔和演出风格方面成绩显著,而且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他嗓音宽厚、发音甜润、字眼清楚、乡土味浓,赶板、垛字、闪眼、落字、窍口机动。他的演唱朴实朴拙,刚健端庄,充分表现了京东大鼓淳厚康健、豪放豁达、抑扬分明、抑扬有度的艺术特点。为了使这一曲种更好地反响现实生活,他还对唱腔不断进行加工和丰富,发展出了一种能够适应新事物的“董派京东大鼓”。二十多年来,在天津市历届职工业余文艺演出中,他的演出都赢得了广大不雅观众的夸奖。1956年董湘昆参加全国职工曲艺会演和全国会演、全国调演,《模范孙桂珍》、《白雪红心》、《送女上大学》获奖后出版唱片。
2010年3月1日,他以83岁高龄参加了河西区文化局主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鼓曲专场,在演出上演唱了京东大鼓传统曲目《拆西厢》。2010年6月14日,他当年二度登台,参加了群众艺术馆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专场,演出了全国听众耳熟能详的一段作品《送女上大学》的选段,得到了台下不雅观众强烈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