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诗史上,孟郊与韩愈并称“韩孟”,皆以构思奇特见长。不同之处在于,孟郊诗境清苦,不似韩愈,每每横放精彩;文从字顺,不似韩愈,时或佶屈聱牙;至于洗练之功,则较后者犹有过之。施补华《岘佣说诗》称:“孟东野奇杰之笔万不及韩,而坚瘦特甚,譬之偪阳之城,小而愈固,不易攻破也。”可谓知言。
孟郊有一首《游子吟》,是名篇中的名篇,祖传户诵,似不难懂,实则浅貌深衷,值得细品。诗云: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游子吟》系乐府古题(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七“杂曲歌辞七”),顾名思义,抒写久客思乡之情。孟诗虽依旧以游子为言,而主题在母爱,重点有所偏移。同时顾况、李益同题乐府,颇事铺陈,相较之下,孟诗一发即收,短小精悍,风格显然有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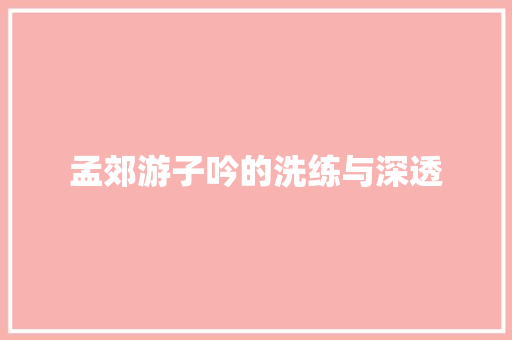
起笔就来了一个跳接:上句方拈线在手,下句已成衣在身;上句方处家中,下句已至他乡。时空迅速转换,发轫挺立。三、四句又从他乡折返家中,从目前折返往昔,追忆临行之际缝衣环境,诗笔往来来往盘旋。所谓“密密缝”,施蛰存师长西席指出:“第三、四句从来没有表明,但如果不知道这里隐蔽着一种民间风尚,就不能阐明得精确。家里有人出远门,母亲或妻子为出门人做衣服,必须做得针脚周详,要不然,出门人的归期就会延迟,在吴越乡间,老辈人还知道这种习俗。”(《唐诗百话》六三《孟郊:诗三首》)可备一说。若仅理解为慈母唯恐游子滞留异地,日久衣物磨损,因而特意做得耐穿些,一样可通。无论如何,均是表现慈母之“慈”。然而这两句浸染尚不止于此。一、二句把稳母亲手制衣物,犹属泛泛而谈;三、四句承接上文,进而把稳到针脚之绵密,则非细审此衣不能看出。游子有此动作,正见得念母心切。这两句字面上虽写慈母,但游子心绪,自不难于言外得之。母与子,昔与今,两条线索一隐一显,融贯合一。
再看末了两句。游子既感念高堂,按常规想法,接下去该亟思有以报之了。不料墨客另辟路子,不说如何报答,而说纵然存心报答,也必报答不尽。立意跳过一层,翻进一层,愈觉深透警拔。衣物功用之一在保暖,前面经由缝衣这一详细事例展现母爱,这里便取春阳之温煦作拟,贴切而语意正符合会。这个譬喻也曾费心推敲,并非随意落笔。
此诗有往来来往,有隐显,有跳接,有翻进,寥寥六句,笔势波折若此,而意脉仍一气贯穿,极见精思。内容温情脉脉,与孟郊平日的“喜为贫苦之句”(欧阳修《六一诗话》)不同;构思之深折,却是一脉相通。《全唐诗》题下有注:“迎母溧上作。”贞元十六年(800年),墨客50岁,至洛阳应铨选,授溧阳(在今江苏省)县尉,《初于洛中选》诗有“青云不我与,白首方选书”之慨。如此年事出而仕宦,正因奉母命使然。他履职后,便迎母奉养,赋《游子吟》即是明志。而诗作只在此事前后旁边盘旋,刻意不犯正题,不雅观此益见墨客的长于用笔。清初岳端选孟郊、贾岛两家诗,取苏轼“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语意,编为《寒瘦集》一卷。这首诗后加评:“此诗从苦吟中得来,故辞不烦而意尽,务外者不雅观之,翻似不经意。”斯言得之。本篇宛若信口道来,让人险些忘却寻其内在的肌理。遇见这类作品,尤宜细细吟味,不可掉以轻心。作者掩蔽技巧,读者揣摩技巧,高质量的阅读,从来都是读者与作者的角力。(成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