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韩国著名导演金基德因新冠病毒肺炎并发症去世。他生前执导的影片,不乏超越常规伦理的情节设计,被冠以“重口味”的标签。与这些影片比较,《弓》算是一部难得的清新之作。碧海蓝天、朝霞落日、胡琴弓箭、秋千木船,幽美的景物为影片增长了诗情画意。但如果仅仅从影像画面和故事层面去看待,片尾弓箭与少女交合的场景就成了不合逻辑的怪诞影像。或许,只有把《弓》视为一部文化寓言来解读,才更加契合本意。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阔别尘嚣的茫茫大海,老年男人和少女住在海中的一条木船上,靠给游客算命及供应垂钓场所为生。老人偶尔驾着另一条小船接送游客,或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少女则一刻不离居住的那条船。他们并非像不雅观众一开始预测的那样是祖孙关系。正好相反,少女是老人捡来的预备妻子,等到她十七岁的时候,老人就要按照古老的传统习俗和她成亲。为此,每过完一天,老人就在日历上划掉一道,迫不及待地盼着成亲的日子到来。老人常常拿着一张弓,白天,用弓箭警告那些骚扰少女的游客,或用弓箭给游客算命;晚上,则拿着用弓弦改制成的分外乐器演奏幽美的乐曲。每晚入睡前,老人都会给少女沐浴,然后握着她的手进入梦乡。
飘在大海上的小船,与世隔绝,唯一的联系是表面来船上钓鱼的游人。游人总是调戏少女,想要霸占她,彷佛暗示着外来的异族入侵。直到有一天,一个少年来到船上。少年清爽、干净、通亮,洋溢着当代文明的青春朝气与勃勃活气。他送给少女一件当代性的东西——MP3,少女被他深深地吸引了。在少年离开的日子,少女穿着传统礼服,手拿望远镜,听着MP3中播放的音乐,向远方眺望。她渴望少年再次涌现,也渴望着表面的天下。或者说,她在渴望着当代文明。 她开始反抗老人,在老人为她沐浴的时候第一次不合营,并主动向陌生男子示好,故意惹老人生气;早上起床后,她拿着弓箭假装射向老人,把老人吓了一跳。
传统民族文化该何去何从?少女是随着少年离开,走向当代文明,还是跟老人结婚,恪守传统?导演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感情是非常繁芜的。一方面,影片对少年所代表的当代文明持肯定和讴歌的态度;另一方面,对老人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又充满抵牾暧昧的心态,既有批驳,又有留恋,既是告别,又是思念。这种繁芜的感情,犹如一曲挽歌,回环往来来往,一唱三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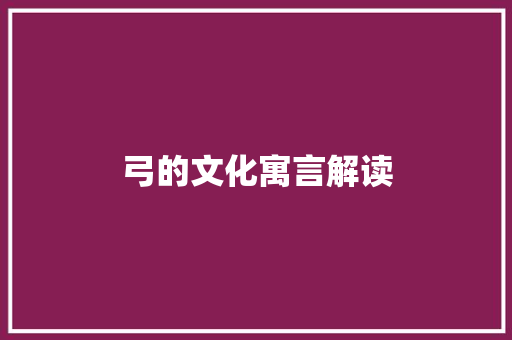
少年的再次到来,令少女大喜过望,她乃至半夜钻进少年被窝主动示爱。但是他们的爱情,受到了老人的干涉和阻挡。妒忌的老人用弓箭警告少年,并在夜里驱赶少年离开。愤怒的少女则把箭一折两段,表达了追求自由爱情和走向当代文明的决心。
少年和少女的刚毅感情,终于使老人决定放手,让两人坐船离开。然而与此同时,老人把绳索套上了自己的脖颈,选择自尽。电影以永劫光的特写画面表现老人极度痛楚的面部表情,解释解脱羁绊和走向新生是伴随着巨大痛楚的。银幕上老人痛楚的表情,是民族变革中捐躯和阵痛的具象化。老人在濒临窒息前拿起刀,开始割脖颈上的绳索——他选择生存下去。在经历痛楚挣扎之后,不仅这个民族走向了新生,传统文化也同样走向了新生。
少女意识到了老人的痛楚,她去而复返,伴随着欢畅的音乐,和老人一起穿上吉服,举行了传统的结婚仪式。老人和少女驾小船离开,留少年一个人在较大的那艘船上。在脱去了衣服之后,少女仰面平躺,老人把箭射向天空,自己投水消逝。这时,少年彷佛意识到了什么,驾船来寻少女,却创造少女两腿伸开,先前射向天空的那支箭溘然从天而降,插在少女两腿之间的船板上。少年走到少女跟前,趴下身子问道:“你没事吧?”少女则牢牢搂住少年,陶醉在交合的愉悦中。
这一情节是不雅观众最难明得的地方,实在是个彻彻底底的隐喻。导演想要解释,弓箭是传统文化的精魂,唯有它可以真正霸占少女的处女之身,为这个民族打上深深的烙印。而作为当代文明表示者的少年,在这场交合中只是察看犹豫者,徒具其表,有形无实。在情绪上,导演还是方向于传统的,尽管理智上知道这个国家走向当代化是一定趋势,但仍旧无法遏制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和追怀。
影片的演出很有特色,老人和少女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偶尔有些悄悄的耳语,不雅观众也听不到。他们完备凭着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眼神等,来表达喜怒哀乐的感情和丰富的内心天下。而且,片中有许多重复的动作,如射箭、沐浴、弹奏音乐、划去日历上的数字等等。大海中一叶孤舟的视觉意象和颇具民族韵味的音乐,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末了要说的,是片中“弓”的含义。“弓”有着繁芜的意蕴、多样的用场。它是武器,少女用弓箭射伤了企图凌辱她的游客;它是乐器,老人在夜间用它奏出凄婉美妙的音乐;它是神示,可以用来占卜;它又是传统文化的象征,为民族和国家打下了深刻烙印。同时,它还寄寓了导演的审美空想,如片尾字幕所说,“在弓的张弛伸缩之间蕴含着力和美,我宁愿这样生活,直到生命终老。”(周仲谋)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