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书入碑的,唐太宗李世民开了先河。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不仅重金求购,命人临摹,还亲自书写,摹刻上石,如《晋祠铭》,书法固然好,但是以碑刻作品欣赏,略显孱弱。以行书入碑得到全面成功的,实在首推李邕。
李邕(675——747年),字泰和,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祖籍江夏(今湖北武昌),唐代书法家。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人称“李北海”。
李北海《岳麓寺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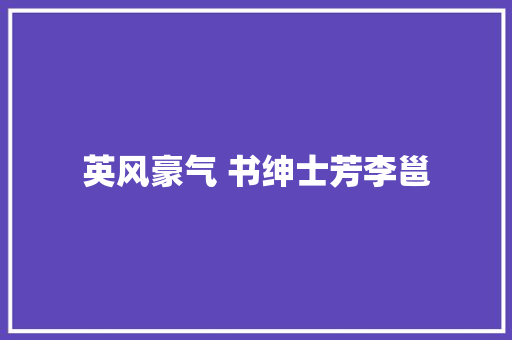
李邕出身世族,其父李善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所注《文选》60卷,至今依然是主要的学术资料。李善在唐初历任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潞王府记室参军,秘书郎,泾城令等职。晚年因事被流放云南,后遇赦放还,隐居于河南开封的等地,做起了老师, 讲述《文选》。从者如云。
李邕自小聪颖,秉承家学,把稳文字,学问根基踏实。听说《文选》有些部分作注时,李善请李邕参与。邕作“附事见义”之释,与其父之注一起刊行,时年李邕十五岁。二十岁时得“文章四友”之一的李峤赏识和帮助,入秘阁读书,学识大进,以文章有名,独步天下四十年。后又为监察御史张庭珪所赏识 ,认为其“词高行直,堪为诤谏之臣”,推举李邕入仕。长安四年(704年), 在张庭珪等引荐下,为左拾遗。刚刚踏入仕途的李邕,不避祸福,直言敢谏。对武则天宠臣张氏、权臣韦巨源的不轨言行,大胆谏言。李邕曾言:“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称也。”这种英风英气,同寅称其“如干将、莫邪,难以争锋。” 杜甫作《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否臧太常仪,面折两张势。然而,锋芒毕露的李邕在封建官场极易受到猜忌和打击。在权贵的排挤下,终极被奸臣李林甫所害。李白作诗感叹曰: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英气今何在?……
李北海《少林寺戒坛铭》
李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究竟不能算是一位精通官场的人物,虽时时有惊人之举,也难以改变其政治命运。李邕喜好敛财,孤高自傲,“好是非改变”,这些可视为其污点和不敷,令人惋惜。不过,人无完人,李邕的刚毅忠烈,和他的文章、书法一样,是不存在争议的。“论诗则王维、崔颢,论笔则曰王缙、李邕,祖咏、张说不得预焉。” “邕象彼马迁(司马迁),法其班氏(班固)。”这是赞赏其文采;也有人将李邕视为全能:“文章、书翰,公直,词辨、义烈、英迈为一时之杰”。
李邕《古诗十七首》
说到书法,其造诣不得不提。唐代书坛,大师云集,前期的欧虞褚薛,并称初唐四家,中期的颜鲁公,颠张醉素,后期的柳公权,可谓群星残酷,皆为大师级的人物。那么,李邕的造诣在哪里?他是怎么占得一席之地的呢?
李邕最善于的是行书。他的成绩,一是行书入碑;二是结字的独特。
李北海《婆罗树碑记》
李邕书学二王,其字形结体和《集字圣教序》相仿,笔势又和王大令附近。《集字圣教序》已是碑刻,单字不失落王羲之神韵,然终归集字,没什么章法可言,其余,该碑刻目的是在于对王羲之的继续,并非变革,后学者也是为了“透过刀锋看笔锋”,回归到帖学上去,要实现行书入碑,还需琢磨。不过,这也为有心者留下了发挥的空间。李邕以楷书笔画写行书,参之以王献之的豪放,一转业书入碑的羸弱。 笔力沉雄,字势跌宕。虽然字距较大,丝毫不影响气势,笔断意连,势不可挡,字里行间,英风英气,动人心魄。
李邕书法的另一个特点是,改变了字的结体。从李斯开始,我们见到的字都是上紧下松,给人以或庄严、或洒脱之感。到李邕这里,彻底冲破这一规律,结字上松下紧,重心下移。单字左摇右摆,然而细细不雅观看,岿然不动。
李北海《叶有道碑》
李邕变革是成功的。李阳冰称邕乃“书中仙手”,吕总《续书评》称李邕书法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据记载,当时碑刻出自李邕之手的有800多通。比如《叶有道师长西席碑》、《端州石室记》、《麓山寺碑》、《东林寺碑》、《法华寺碑》、《李思训碑》、《李秀碑》等,个中以《李思训碑》、《麓山寺碑》碑最为著名。
《李思训碑》,全称《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该碑立于开元八年(720年),现在陕西蒲城县。行书,30行,每行最多70字。用笔清瘦豪迈,弯曲迅疾,抑扬有力。用笔清瘦,周遭兼施,字体纵长、欹侧。 险要中见稳健之态。有风骚洒脱韵,更见豪迈奇崛态。 清人王文治说:“前人评李北海书,病在欹侧,似专指此碑而言。子敬(王献之)妙传字法,而欹侧尤甚。北海全从子敬得笔.仰契右军……以荒率为沉厚,以欹侧为端凝,北海所独,尤《云麾》所独。”王文治找到了李邕欹侧的渊源,并指出此非病,是继续和创新,是美。抑扬有致,骨势洞达;行气贯通,收放自若,令人线人一新。
李北海《李思训碑》
杨慎以《李思训碑》为李邕最好的作品,他借用王恽的话说:“融液屈衍,纡徐妍溢,一法兰亭。但放笔羞增其豪,丰体使益其媚,如卢询下朝,风皮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三郎顾之,不觉叹美。”
《麓山寺碑》别号《岳麓寺碑》,碑额有篆书“麓山寺碑”四字,原石在长沙岳麓书院。此碑晚于《李思训碑》10年,风格趋于沉稳。 明代董其昌关于“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的说法,个顶用这个“如象” 来概括李邕的书风,《麓山寺碑》该当是最合乎哀求的。此碑结体整饬,笔力雄强 ,苍茫雄浑。李邕作此碑时政治上已经失落意,加上年事已高,像《李思训碑》那样的跳荡的造型已不再明显,代之以“沉着劲栗”(何绍基语)。“书者,心画也。”作为心灵的写照,该碑一派雄强蕴藉的气候。王文治则盛赞此碑“气骨峥嵘,如泰山卓立,觉驯象巍然,……”
李北海《出师表》
历史上,书法大家林立,钟、张、二王,欧、虞、褚、薛,都是百代模范;然而,善行书者,入碑便弱,能入碑传世的,又多为楷书。李邕是将行书入碑取获胜利的第一人。他成功的将二王一起行书的秀致与碑版的厚重相结合,伟岸又不失落灵动。
李邕曾言:“似我者俗,学我者去世。”不下一番功夫研究,还真不能贸然学习。欧阳修的一段话颇能解释问题;“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为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犹结交,其始也难,则其合也必久。余虽因邕书得笔法,然为字绝不相类,岂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见邕书,追求锺、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然邕书未必独然。凡学书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馀,余偶从邕书而得之耳。(《试笔》) 六一公的学书体验或容许以解读李邕当年留下的“狠话”,只是蕴藉了些。
明代杨士奇提要挈领:“北海书矩度森严,筋骨雄浑,沉着飞动,引笔有千钧之力,故可宝也。”
李北海《端州石室記》
清代的刘熙载将这点说的更为明白:“李北海书气体高异,所难尤在一点一画皆如抛砖落地,使人不敢以虚憍之意拟之。李北海书以拗峭胜,而落落不涉作为。昧其解者,故意低昂,走入佻巧一起,此北海所谓‘似我者俗,学我者去世’也。李北海、徐季海书多得异势,然所恃全在笔力。”(《艺概》)可见,“似”——徒有其形便入俗格,并强调了北海书法的秘密:全在笔力。
从书法实践上看,不少人却是“明知山有虎,倾向虎山行”。如宋代的苏东坡,明代的董其昌,元代的赵孟頫等。
苏东坡学过徐浩,学过颜真卿,到了后来,不论分辨地学起了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苏东坡自己也说:“予书初学李江夏(邕),后来自成一家。” 董其昌自称平生最喜好李邕的书法,并将王羲之和李邕放在一起评价:“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然后自傲地说,众人一定有赞许我董其昌的说法的。这些历史大家敢于学习,敢于“去世”,无异于凤凰涅槃,如果他们在学书之路上真的去世过一次,历史看到苏、董们时,他们已经成功蜕变,华美转身。
李北海《晴热帖》
杜甫和李邕交情不浅, 诗圣在《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一诗中写道:“忆昔李公存,词林有根底。声华当笔健,洒落富清制。风骚散金石,追琢山峰锐。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名满深望还,森然起凡例。”
是啊,作碑八百多通的李邕,碑版便是他活生生的代言,一块块石碑便是他生命的一张张写真。人倒下了,碑却竖了起来,“如象”一样平常地站着,百代流芳。
(转自《书法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