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既亡,《春秋》作。
寓褒贬,别善恶。
三传者,有《公羊》。
有《左氏》,有《穀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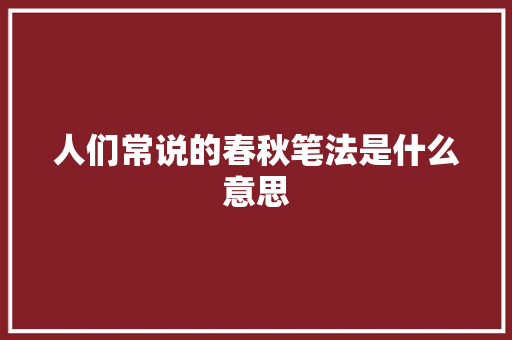
《三字经》这一段说,“诗既亡,《春秋作》”。“诗”即《诗经》。作为文学长河的源头,《诗经》文脉绵长,吟诵至今。那么,是什么亡了呢?
《孟子·离娄下》里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意思是:圣王采诗的事情破除了,诗也就没有了;诗没有了,孔子便作了《春秋》。在周朝壮大之时,周天子会常常委派一些官吏到各诸侯国稽核民情,把各地的诗歌抄录后送到朝廷,以帮助周王室通过理解各地的现实情形。《诗经》正是从这些抄送朝廷的诗歌中编选出来的。可是,到了春秋期间,诸侯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周王室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朝廷也不再派人到民间采集诗歌了,乐师不陈诗而《风》亡,诸侯不觐天子而《小雅》亡,天子不享诸侯而《大雅》亡,诸侯不助祭而《颂》亡。由此,“诗既亡”实质上指的是与王权相始终的礼乐制度的崩坏。
再说“《春秋》作”。孔子带着弟子漫游列国14年,到了晚年回到了鲁国,紧张从事教诲讲学、著书立说。为了表达自己的道德空想和治国理念,他对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进行了整理修订,“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仪式”,写成了新的《春秋》。孟子为什么会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呢?如果从文化和历史的逻辑考量,就能找到二者之间紧密的关联性。
《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正由于周道衰败,身处春秋浊世,孔子以斯文自任,当仁不让地作《春秋》来“正王道”,把已经失落道政治给扶正了,为天下正名,客不雅观上继续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家治史以“劝善劝善”的崇高空想。
这就说到“寓褒贬,别善恶”。在《春秋》中,孔子确立了著名的“春秋笔法”也便是“微言大义”“春秋大义”,以准确而特殊的用字表达作者的褒贬好恶,“笔则笔,削则削”,“笔”是书,“削”是不书,都有大道理在内,所谓“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孔子将自己的一套礼义规范和是非标准寄托在了对史事的陈述之中,借此鼓吹他所崇尚的伦理道德不雅观念,秉笔直书、善恶必录,旨在磋商祸乱之根源,进一步授予史学以“资治”功能。
接着说“三传者”。古代经自经,传自传,各自单行。传是对经加以阐明的著作,而不是现在所说的人物传记的意思。《春秋》的经文,实际上是孔子借史阐理的一部历史教科书提要,只简要记载了各种事宜,并没有交代事宜的原委。孔子去世后,传习《春秋》者因不雅观点不同、角度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他们都爱崇孔子所作《春秋》为“经”,而把各种解读阐明《春秋》内涵或补注《春秋》详细事宜原委果作品,称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春秋》学,共有5家“传”传世,分别是:《左氏传》30卷;《公羊传》11卷;《穀梁传》11 篇;《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后来,《邹氏传》与《夹氏传》先后亡佚,余下的三种,后人通称为“《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
《公羊》相传战国时公羊高受之于孔门子夏,其后子孙口耳相传,至汉景帝时,由公羊高玄孙公羊寿等以今文书写成书,看重对《春秋》经文中“微言大义”的理论阐释,采取对答体,逐句逐字,设问作答,层层推进,以阐发个中所蕴涵的政治哲学涵义。从战国期间一贯写到汉代初年,也叫《公羊传》或者《春秋公羊传》。
《左氏》相传由春秋时左丘明所作,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通过详尽的史实阐述,揭示了列国兴衰背后的历史规律,笔墨幽美,影响甚广,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造诣,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期间历史的主要文献,特殊是对确立编年体史籍的地位起了很大浸染。
《穀梁》,又称作《春秋穀梁传》,始传者为鲁国穀梁赤,传至何时,由何人写定成书,史无明文。其强调必须尊重君王的威信,但不限定王权;君臣各有职分,各有行为准则;主见必须严格对待贵贱尊卑之别,同时希望君王要把稳自己的行为。
古人评《春秋》三传的特色:“《左氏》艳而富,其失落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落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落也俗。”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汉代往后,《春秋》的流传及其政治浸染的发挥,紧张是借助《春秋》三传完成的。因此,涌现了经传合编趋势,《春秋》经与《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逐渐融为一体,影响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政治伦理及不雅观念意识等各个领域,是透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分外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