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体诗歌一向讲究押韵。严格的押韵,便是韵脚字的韵母和音调都相同,以此来形成一种音律的回环美感。最早的诗歌押韵,自然没有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该当都是作者以母语方言为标准。在音值上,不同方言对某个字的读音会有差别,但对字音的归类,却可能相同。例如《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个中“鸠”“洲”“逑”不仅在当时是押韵的,用本日的普通话和许多方言朗读,也是押韵的。
当然,这种情形并不是普遍的,不同方言对字音的归类有时也不完备相同。因此,每每就会涌现一种情形:用甲方言读一首诗是押韵的,而用乙方言去读却不押韵了。由此产生了“共同标准”的诉求,即哀求人们都按一个标准押韵,而不是按照任何一种方言的标准押韵。表示“共同标准”的,便是韵书。
韵书涌如今魏晋期间,它首先按照音调标准将汉字归类;同一音调的字,再按韵母标准归类;同一韵母的字,又按声母标准归类。唐代往后,韵书成了人们写作格律诗赋的统一标准。这一标准是书面上的硬性规定,与社会口语的实际情形并不完备符合,后来更是渐行渐远了。本日,人们并不知道一个字在韵书中的实际音值,只知道在当时的读音分类情形。
本日人们用普通话读古体诗歌时,常会碰着韵脚字不押韵的情形。例如白居易《续古诗》:“戚戚复戚戚,送君远行役。行役非中原,外洋黄沙碛。伶俜独居妾,迢递长征客。君望功名归,妾忧死活隔。谁家无夫妇?何人不离拆?所恨薄命身,嫁迟别日迫。妾身有存殁,妾心无改易。生为闺中妇,去世作山头石。”诗中的“役、碛、客、隔、拆、迫、易、石”是一组在韵书中都属于同一韵的字,但用普通话来读,便不押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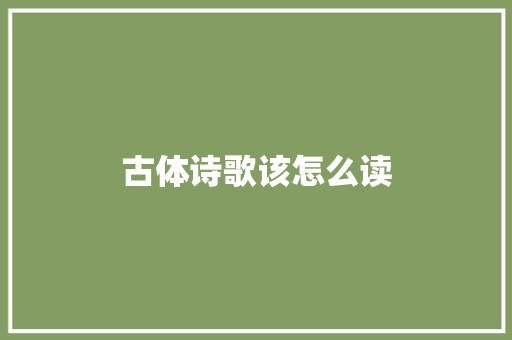
有些人不甘心于无法感想熏染韵律的回环美,便采取了类推读音的做法。比如,“斜”在平水韵中归“下平六麻”,常常被用作韵脚。例如,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凡百姓家。”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月红于仲春花。”这些诗都用“花”“家”与“斜”押韵,而“斜”在普通话中读“”,与“花”“家”韵母的音值不同。于是有人主见用“花”“家”的读音类推,将“斜”读为“”,以求和谐。这一做法在很长一段韶光里很盛行。
但是问题来了,这种类推的做法能不能贯彻到其他诗歌中呢?
例如,刘禹锡《台城》:“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夏竦《廷试》:“殿上衮衣嫡月,砚中旗影动龙蛇。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碰着这种情形,可不可以将个中的“奢”和“蛇”都读为“”呢?再如,“下平六麻”韵中还有“车、邪、遮、赊、耶、嗟、蜗、爷、些”等字,如果它们涌如今诗歌的韵脚上,是不是也要将韵母改读为“ā”呢?
汉字古音的音值确实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各种拟测都只能聊备一说。古人用当时的语音读《诗经》,创造韵律不和谐,就提出“叶韵”一说,受到后来的研究者诟病。实际上,将“斜”类推而读为“”,和“叶韵”险些是一样的。如果这种“类推”被容许,古诗韵脚的读音可就要乱成一锅粥了。
明代陈第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我们只能笼统推测诗歌韵脚读音在当时是和谐的。进一步穷究的话,乃至在当时也未必和谐。由于中古以来人们按照韵书的规定押韵,并不照顾韵脚字在当时口语中的音值。笔者认为,在古体诗歌阅读中,知道这些韵脚字在韵书中是一个韵类,是具备韵律回环美的,这就够了;而不宜采纳将“斜”读为“”一样的做法。
到南北朝,文人开始把稳并重视到,在行文中将字音的调节作为一个主要的审美标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其讲究已经十分周详了。这种对韵脚字以外笔墨的音律讲究,导致了律诗的产生。律诗的平仄模式,是古人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得到的平仄最佳匹配状态,利用字音的平仄对立,营造了声律的起伏变革美感。
例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喷鼻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首诗所用的平仄模式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个中“生”在第五个字的位置,可平可仄,别的字音都符合模板规定。这里的“看”读平声“”,才符合模板的规定,如实传达声律效果。“看”在当代汉语普通话中是多音字,读“”时,指“使视线打仗人或物”;读“”时,意为“守护照料”。因而,人们根据意义随意马虎将“遥看瀑布挂前川”的“看”读成去声“”。
此外,像“过、思、听、忘、望、叹、论、醒、凭”等,在古体诗歌中都有平仄两读的环境,涌现频率很高,该当引起把稳,随时辨识。
古体诗歌有一套知识系统,教和学都该当尊重它,碰着有关问题,应该予以足够的解释,使循规蹈矩的知识积累保持一向性。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4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