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春节档,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节档。这波电影,再次表示了我国电影亘古不变的战斗主题:《猖獗的外星人》打外星人,《神探蒲松龄》打妖怪,《廉政风云》打大老虎……
于是,不打仗的《流浪地球》从一票打打杀杀中脱颖而出,成功霸榜春节档期。这部电影紧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为了躲避太阳毁灭的灾害,人类在地球表面建立上万座行星发动机,试图将地球推离太阳系,探求新家园。地球在靠近木星时遭遇失守危急,关键时候,刘培强、刘启父子成功点燃木星,拯救地球!
不得不说,《流浪地球》作为中国科幻片的开山之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从剧情到殊效也都可圈可点。然而,当屏幕上涌现,那颗蔚蓝的星球在茫茫宇宙中流落的时候,我却恍惚在想——在我们之前的古人,是否也曾仰望着天空中某个天体,抱负过这样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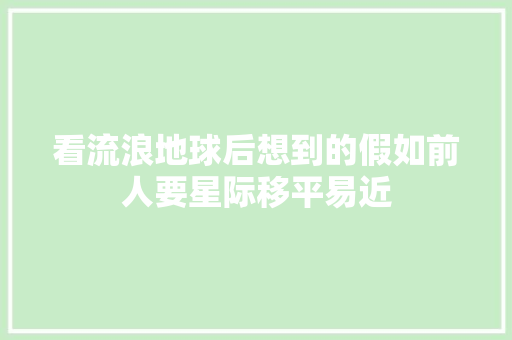
或者说,他们是否曾想象过,去往其他的星球上生活?
那么,他们会想要去太阳上吗?
或者玉轮?
或许是其他星球?
为了得到一个答案,古人们大胆猜想,小心求证,进行了千百年来不断的想象与探索……
【以下内容为脑洞产物,由干系神话传说及史料合理改编而成,切勿完备当真!
】
图片来源电影《流浪地球》
01玉轮基本资料
星球名:月球
与地球间隔:约38.4万公里(折合410-7光年,约1.2光秒)
性子:地球的卫星,环绕地球迁徙改变。由于月、地、日的相对位置不同,在地球上不雅观察月球会有满月/缺月的变革,周期约为29.53天。
良久良久之前的中原民族,彷佛曾经节制一种超自然力量。那段韶光的他们,具有着连当代人都望尘莫及的科技水平与身体力量,险些是“超进化状态“。
具有这种力量的他们,完成了很多连当代人都弗成思议的事:移山、填海、熔化石子修补大气层、凭一人之力撞断山脉、与神灵和神兽相沟通……
当然,拥有这种力量的他们,自然也想过,往其他星球上移民。
而且,有人成功了。
那位成功移民的女性宇航员,叫嫦娥。
传说中,嫦娥女士能够成功凭一己之力进行地月航行,得益于他们当时高超的医药学技能。据猜想,嫦娥能够飞往月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吃了西王母所赠与的两粒药,从而改变了身体布局,使得其不但可以独立产生可以摆脱地球引力的升力,而且对月球上极热、极寒、无氧等恶劣生存条件都有了很强的抗性。
这也是,中原民族在星际移民的考试测验中,第一个,也是唯一成功的案例。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通讯技能尚不发达,嫦娥女士在移民成功后,并未与地球进行任何有效的联结。再加之后来人们损失了与神灵沟通的能力,那两粒药的有效化学身分也不得而知,令人惋惜不已。
后期人们忽然失落去了那种超自然力量,文明一下子跌落回奴隶制社会。在掉队的科技水平条件下,由于无法与嫦娥进行互换,人们只能通过对月球进行不雅观察,来探索可能有效的信息。
一位天文不雅观察者站了出来,说出了他的迷惑与猜想:
夜光何德,去世则又育?
厥利维何,而顾兔在腹?
翻译成当代汉语便是:
玉轮有着什么德行,竟能去世了又再重生?
月中黑点那是何物,是否兔子腹中藏身?
可以想象,在那个天文知识匮乏的时期,对付公转征象知之不深的他们,很难对第一个问题给出合理的答案。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年代久远,我们也无从考证。
这位天文不雅观察者虽然没有本色性的打破,但他的涌现依然有着重要意义——他开辟了中原民族对付月球,乃至于对付宇宙探索的道路。
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屈原。
良久良久以的宋朝,在一个中秋之夜,我们的辛弃疾辛大爷,望着夜空中的满月,不禁想起了一千多年前,同样不雅观察过玉轮的屈原老前辈。他决定模拟屈原《天问》的手腕写一首词,连珠炮似的问出自己关于玉轮的迷惑: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
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逐渐如钩?
这组问句可不得了,它立足于文学和神话传说,却向着科学的方向迈了一大步。“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险些可以说是隐约猜到了月球环绕地球转的自然征象;“飞镜无根谁系”,乃至有着对引力的预测与迷惑。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对此大加讴歌:“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我倒是以为,“神悟”倒是未必,有端预测还是很有可能的——当然,他所说的,就连他自己也未必在意。但毕竟,间隔原形,已经不远了。
有屈原、辛弃疾这样的考据派,自然也有迫不及待的行动派——就你们这么每天瞎琢磨,哪天能真正上到玉轮上去呢?
一位墨客站了出来,他一手拿着酒盅,一手拿剑指着玉轮,醉醺醺地喊着:
“我,李白,现在,就要,到玉轮上去!
”
实在对付李白这种想象力丰富的人来说,想要上玉轮,实在不算个什么事。动不动就“手可摘星辰”,一愉快就“耐可乘流直上天”的他,想要上个玉轮,算什么呢?
问题在于,这次他,真的动身了。
那个晚上,李白喝了不少酒,乘着醉意,划着一叶小舟来到江上。看着水中倒映着的明月倒影,李白大笑:
“都道‘海底月是天上月’,天上的我上不去,捞个水里的玉轮,问题该当不大吧?“
说着,李白一手伸到水底,却不料没稳住身形,翻身落水…一代诗仙,就此陨落。
李白这种为探求真理而献身的探索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在五代期间就有人以诗记述:
“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宫锦坐钓船。
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
这种对玉轮的探索与追求,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传承。没有他们,就没有“嫦娥”系列探月卫星和“玉兔”号月球车,更不会有一篇篇不朽的“明月几时有”和“床前明月光”。
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02太阳基本资料
星球名:太阳
与地球间隔:约15000万公里(折合约498光秒,约1.510-5光年)
性子:地球以其为中央迁徙改变;发光放热;地日间隔远大于地月间隔。
作为天空中最通亮的天体,太阳,自然也很早就进入了人类的视线。
险些和嫦娥同一时期,一个同样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人——夸父,开始向太阳进军。
这个男人,没有嫦娥手中的灵丹灵药,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跑!
这个男人的体力是惊人的,乃至可以说是恐怖的。他凭借一双具有超自然力量的腿,生生跑下过了名山大川,跨过了丘陵与山谷,直奔太阳而去——
别忘了,他的目的是追逐太阳!
太阳落山了他追谁去啊!
也便是说,他那么远的路,都是在一天之内跑下来的……
然而,他的速率还是远远不足。我们知道,想要分开地球,奔向太阳,最少也要先超过地球的第二宇宙速率,即11.2km/s,否则不是被地球的引力拽回来,便是像玉轮一样成为地球的卫星。
看夸父跑了这么久还没跑出中国,显然是属于前者…看来他的超自然力量还不足强大。
更绝望的是,这种力量只强化了他的身体,并没能改变他的其他特性——跑了这么久,他不渴的啊!
这时候,这个男人强大的体魄再次表示了出来——能跑的他,同样格外能喝。
“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敷,北饮大泽。”
这个男人,为了完成他的太阳航行操持,生生喝干了两条两条河流,而且还没喝够。
令人嗟叹的是,他还没找到下一个水源,就在半路上渴去世了,成为了一位悲剧英雄。
实在这真不怪夸父。太阳和玉轮,在天上看着差不多大的两个天体,谁能想到一个与地球的间隔是另一个的390倍,质量更是另一个的2.7107倍?
放在那个年代,神话都不敢这么写。
尤其是这个日地间隔的问题,世世代代困扰着中国公民。早在春秋期间,纵然博学如孔子,也不能办理太阳是早上离我们近还是中午离我们近的深刻问题,更遑论那两个辩论的小屁孩。
而到了唐代,这个日地间隔的科学问题又带上了一种政治色彩。身处江南的晋朝天子们,开始思考另一个深刻的问题:
是太阳远,还是长安远?
这个问题迅速得到了年幼的晋明帝的回答:
“当然是太阳远辣!
听说有人从长安来,可没听说谁从太阳来。”
然而未曾想,这孩子第二天转身就改了口:
“当然是长安远辣!
举头就能瞥见太阳,可是看不见长安。”
即将向南京迁都的明帝他爸晋元帝,宠溺地摸了摸明帝的头,叹了口气:
“孩子你说的可真好,可“举目见日,不见长安”,爸听着咋就这么扎心呢?”
自此往后,“日近长安远”成了一个千古流传的梗,说的便是想去首都而不得的环境。
由于日地弘大间隔的限定,我国公民向太阳进行移民的操持被迫几次再三搁置,至今也未能成功。只有传说中的三足金乌,孤独地蹲在太阳里,等待着未来可能会来的人。
但是,人们对付太阳与玉轮的探索,从未停滞。
一波又一波的猜想与考试测验,仍在连续……
图片来源电影《流浪地球》
03星辰大海人们探索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太阳与玉轮,中华民族的目标,始终是星辰大海。
“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的北斗七星,“迢迢牵牛星,皎皎天河女“的牛郎星、织女星,乃至于金木水火土五星、二十八宿……无不在古人的不雅观测范围之内。古人在记述”荧惑守心“”星孛入于北斗“之时,也未必未曾对它们心生神往。
这些星星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那里是否也有着山川于江河,丘陵与山谷,或者,一个更大的“九州“?
它们上面,是否也居住着像我们一样的人?是否有着一样的宫殿,楼阁,田地,那儿的街市,是否也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
这是千万代人的疑问。
这是千万代人的梦。
图片来源电影《流浪地球》
04比邻星在《流浪地球》中,我们迁移的终极目标,是4.2光年外的比邻星。
我忽然想起王勃的一句诗:
海内存心腹,天涯若比邻。
这句诗如果反过来说,也可以说成是,比邻,若天涯。
天涯是什么?《流浪地球》给出了答案:
天涯,是4.2光年外的比邻星,是2500年的迢遥旅程,是整整一百代人努力的终点,是所有人终极的梦。
2500年前的我们,可以凭借一人之力移山堙海,2500年之后的我们,依然绝不畏惧下一个长达2500年的旅程。
或许有人会问:为了人类文明的延续,直接乘坐飞船离开,岂不比背着这么一个沉甸甸的地球随意马虎的多?
的确是这样。如果真的到了死活存亡那一天,理性会见告我选择飞船。
然而,只要有一丝可能,感情上,我依然希望能够带着地球一起。
由于,那上面承载着我们的家国故土,承载着我们的五岳江河,承载着我们几千年来祖祖辈辈们所有的感情与影象。
几千年来,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舞于斯。离开了这片我们成长的大地,我们的感情与笔墨都将变得苍白。我们将无法理解“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由于”岱宗“与“齐鲁”,都将被打上一个“曾经“的标签。
那是我们的家。
那是我们的文化影象。
因此,千万年之后的人们,我有一个小小的欲望——假若你们有能力走出太阳系乃至于银河系,去探索更广阔的宇宙,如果可能的话,请带着地球一起。
或者至少,当你们在宇宙的其他角落发达发展,繁衍生息之时,请不要忘却——
地球,是我们的故乡。
-作者-
老王,清华大学在读本科生,年十八,喜古文,迩诗词。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大吃一顿。故自傲人生二百斤,会当撰文三千笔。因此浅题四五诗词,闲作六七文章,若承蒙不弃,愿与八九好友共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