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盛行的程度,不亚于如今乐坛之“霸榜金曲”。后来,宋朝的苏轼途经西塞山前,写下了一首《浣溪沙·渔父》,险些是通盘照抄了张志和的原作。
进行如此程度的“洗稿”,苏轼怎么还美意思将其收录进自己的作品集呢?原来,他在词前写了个序见告大家:我写这首词是“为往圣继绝学”,它原来的曲子失落传了,我重新给它配了。
但是,改编之词始终还是“未若原句之妙通造化”。于是大墨客黄庭坚借着《渔歌子》的母题进行原创,不料苏轼却说黄庭坚把张志和写出了“人品问题”。
结果,苏轼、黄庭坚二人为此大吵了一架,从盛年一贯吵到了晚年,仍是谁也说不服谁。同时,黄庭坚晚年仍旧坚持“洗稿”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力证“我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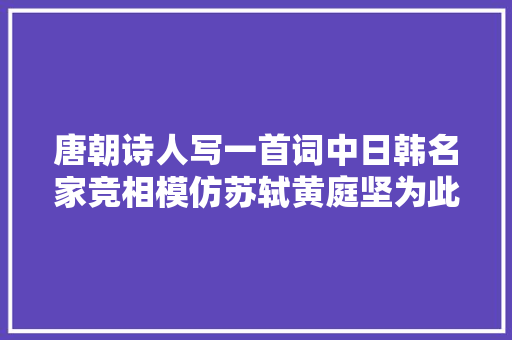
全体吵架的过程,也被察看犹豫者全程记录了下来,末了这个记录者自己也“手痒”难耐了,忍不住了局将张志和的原作,也改写了一遍……
一、“词祖”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唐·张志和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小雨不须归。
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非常有名,大多数人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背过这首词了。由于这首词意思的浅近易懂,以是就不作口语翻译了。
个人非常喜好词中描写的美景,以及“桃花流水鳜鱼肥”中的“鳜鱼”。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词在唐代,实在是一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盛行歌曲”。
这首词一经问世,立马就轰动了全体大唐。听说唐玄宗看到它往后,曾经敕令四处去探求作者张志和,但是那个时候的张志和,已经出家当了羽士了,以是大家都找不到他了。
《渔歌子》原来是一个词牌名,以是《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一词刚出来的时候,实在是可以配乐进行演唱的。后来,它还传到了日本和韩国。
日本的嵯峨天皇看到这首词往后,内心非常喜好,还调集王公大臣一起开会谈论,并且写了五首《和张志和渔歌子》,个中第五首是这样的:
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
日本的萩原正树教授认为:最早流传到日本的中国词作,便是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除了日本以外,古代的韩国人也非常喜好张志和的这首词。
不过,跟宋朝的人喜好把唐诗的意蕴,直接挪用到词作里不同,韩国人是把词中的意思,用到了诗里面去,他们还特殊喜好把张志和杜甫并列。
高丽的金克己在七律《南浦》中写道:
黄鹂啭处杜工部,白鹭飞边张志和。泽畔恐遭渔父笑,朱颜颓玉莫辞酡。
高丽的李仁老七言绝句《西塞风雨》中写道:
秋深笠泽紫鳞肥,云尽西山片月辉。十幅蒲帆千顷玉,尘凡应不到蓑衣。
除了上面这两首诗,当时高美人还有“绿蓑青蒻桃花水,苦忆山阴张志和”、“浮萍莫是杜子美,蒻笠还如张志和”、“孤舟风雨一青蓑,西塞依然张志和”等句子,都是和张志和干系的。
其余,高美人还有一些诗里不用张志和的名字,却用了道号“玄真子”。可想而知,当时除了中国人以外,日、韩等国的人,一样非常喜好张志和。
苏轼本身就特殊爱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他被贬官之后,在途经黄石一带的时候,看到了西塞山,于是就想起了张志和的这首词。
但是,当时《渔歌子》原来的曲子,早就已经失落传了,也就无法进行演唱了。苏轼心想,这么好的词,却没有曲子可以来演唱,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
于是苏轼为了填补这种遗憾,就借了《浣溪沙》的曲子,来唱张志和的名作。但是为了能够合辙押韵,以是他在作词的时候就改动明晰一点点。
二、苏轼、黄庭坚二人环绕《渔歌子》的干架前面我们曾经说到,苏轼是由于有时看到了西塞山,才遐想到了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想把他的艺术经典传承下去,末了才填下面这首《浣溪沙·渔父》:
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
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小雨不须归。
苏轼这首《浣溪沙·渔父》,意思和张志和的原作基本附近。只是加了一个七字句——散花洲外片帆微。其余,他还在“青若笠、绿蓑衣”这两个短句前面,各加了一个四字短句。
由于苏轼以为张志和的原句已经非常完美了,本身并不须要去进行改动。他之以是要改,只不过是为了让这首词能够合辙押韵,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同时,古代的诗词人也并不认为这种改动是抄袭。清人贺裳在《皱水轩词筌》里面说:“词家多翻诗意入词,虽名流不免。”以是,苏轼只是干了当时所有名人都爱干的一件事。
可是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实在是太有名和出彩了,《艺概》的作者读了苏轼的词往后,就认为苏轼是把原来已经“妙通造化”的句子,改得不那么灵光了。
当时江西诗派的首领,大名鼎鼎的黄庭坚知道往后,就批评苏轼改得太差。他认为:“渔船哪里会有帆”?“散花”与“桃花”用重复了!
于是,他就原创了一首《浣溪沙·新妇矶头眉黛愁》: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沈钩。
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吹雨转船头。
黄庭坚这首词的大意是说:新妇滩就彷佛是一位美女一样,黛眉轻蹙,眼中含愁,女儿浦口的水,又像是一位妙龄少女眼中的秋波。
月光倒映在清澈的江面之上,让水中的鱼儿错把水中月,算作了天上月;嘴唇刚刚碰到了吊钩,它就冒死地向水下倒着游去,结果反而还上了钩。
渔父头上戴一个青色的笠帽,身上披着一件绿色的蓑衣,安定悄悄地坐在船边,不知道过了多久。所有的事,都彷佛是转瞬间发生的一样。这时,一阵斜风将小雨吹过了他的船头。
黄庭坚这首词本来写得是相称不错的,但是他遇上了“杠精”苏轼。苏轼就挑他的毛病说:刚刚还在“新妇矶”,一下子又去了“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
意思是说,这个渔夫难道是一个花心的浪子吗?结果,两个人就这样吵了起来。苏轼、黄庭坚二人对张志和原作的改编,在后世大多受到了批评。
可是黄庭坚却一贯不服气,到了晚年,他听他侄儿说《浣溪沙》的调子实在和《渔歌子》是不合的,还是《鹧鸪天》更像一些,于是他又用《鹧鸪天》填了一首《渔歌子》。
苏轼看到了往后,有一些气又有一些想笑,于是就送了他一句话说:“鲁直乃欲平地起风波耶?”意思是说:别了吧,这都多少年了啊,你还想和我连续吵架啊,我真是服了你了!
结语听说,李清照曾经批评苏轼填词,多不合音律。但是谁也料不到,苏轼这一回和黄庭坚“大动兵戈”,竟然是由于想让张志和的《渔歌子》“合音律”,才弄失事来。
苏轼本身的性情就比较粗放,而且他原来填词的时候,也不太讲究什么“避复”等等。他在填写《浣溪沙·渔父》的时候,显然也没有掠人之美的心思,以是就填得更加随意了。
“自庇一身”、“相随到处”,的确也是有一些“多此一举”了。至于宋代的渔船上面,到底有没有船帆,现在的人也无从得知了。
当然,黄庭坚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由于他坚持要改写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而他和苏轼“干嘴仗”的全体过程,也被他侄儿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末了,弄得他的侄儿实在是“技痒难耐”了,也跑出来,用《浣溪沙》和《鹧鸪天》各填写了两首词,但是都不是太出名,以是很多人也就不知道了。
后来,当时的诗词人也纷纭效法,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风气。而且改写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的作品,也多如过江之鲫,就算是说上个三天三夜,那也是说不完的。
在这些改编之作中,咱们中国自己的词人写得怎么样,就不用多说了。不过让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日本和韩国的诗词人,居然也还写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