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有一篇文章记载西伯戡黎后的一场庆功宴,席间君臣且饮且歌,风雅无比,令人悠然憧憬。
简文开篇说道: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介,周公叔旦为主,辛公甲为位,作册逸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
周文王、周武王期间的纪年办法是从文王受命开始。“武王八年,征伐耆”实为“(文王受命)八年,武王征伐耆”。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推算,文王受命在公元前1056年,文王七年(公元前1050年)而卒,文王八年(公元前1049年)武王伐黎(亦即“征伐耆”),文王十一年(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耆,亦即“西伯戡黎”之“黎”,地在今山西长治西南之上党,子姓,与富商王朝关系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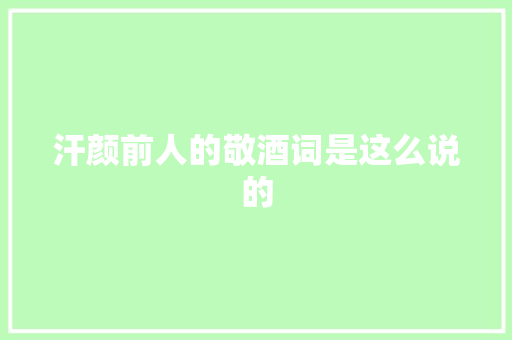
这场庆功宴,用西周礼仪的术语来说,叫“饮至”。饮至,是征战凯旋之后在宗庙举行的祭告先人、慰劳元勋仪式。包括献俘、舍爵、策勋等环节。舍爵,即饮酒。饮至的地点也很特殊,是在“文太室”,亦即周文王的宗庙。之以是放在先王的宗庙,是由当时的“军礼”决定的:战役发动前,要到先王的宗庙祈祷;战役过程中,要随军带上先王的牌位;战役结束后,要到先王的宗庙报告。
参加这次庆功宴的,可都是千古留名的伟大人物。毕公高,文王之子,名高,武王伐纣后封于毕,系魏国先祖。毕公高当为伐耆主将,故在饮至礼中为客。召公保奭,官太保,名奭。周公叔旦,叔是排行,名旦。辛公甲,即辛甲,故殷之臣,事纣,七十五谏而不听,后归附周。作册逸,史官,名逸。吕尚父,姜太公,其先祖封于吕,名尚。还有一位,周武王。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看重酒席上的位次和礼仪。这场庆功宴,对照如今民间仍旧存在的八仙桌的坐法,毕公高当是主宾,坐在坐北朝南的右首(从对面看,右为上),召公保奭作陪。有宾就有主,那么,谁是主人呢?按理该当是周武王,但君臣有别,不可分庭抗礼,于是由周公旦作为主,辛公甲作为主人的帮手。他俩,按照八仙桌的坐法,当坐在毕公高、召公保奭的对面,坐南朝北。饮酒总是须要酒司令,吕尚父便是这场酒宴的酒司令。他在酒席上的临时身份是“司正”,所谓正宾主之礼者。虽说是酒司令,但肯定不是后世卖力斟酒的角色。吕尚父,按照八仙桌的坐法,应该坐在东首,坐东朝西。坐在他阁下的,是作册逸。在古代,君王的言行均要记录在册,于是作册逸作为“东堂之客”坐在姜太公的阁下。周武王呢,可能最得体的位置是在“八仙桌”的西边,坐西朝东,一个人坐一壁,宽坐。按理说,周武王的地位最高,但在这个庆功宴上,他不好坐在嘉宾的位置,也不好作为主人坐在嘉宾的对面,于是这个朝东的位置就最适宜他了。长者者的这种灵巧变通而不失落尊贵的坐法,在后世民间的酒席上,还能见到。
当然,我这里一口一个八仙桌,只是一种类比的说法。在西周初年,可能还没有八仙桌,君臣也并不一定像后人那样围坐在一张方桌四周猜拳行令、把酒言欢。他们或许实施分餐制,一人一座一案,外加一套餐具酒具。他们这几个人的实际座次,后世学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此处不说也罢。
今人敬酒,常常是站起身,端起斟满的羽觞,伸向被敬酒者,说上一番话,譬如,“我敬您!
干了!
”、“我对您是最敬佩了!
您……(一样平常为德高望重、风华绝代之类的词语),以是,我一定要敬您一杯酒!
您务必赏光!
”、“这么多年,承蒙您……,知恩不报非君子!
我敬您!
先干为敬!
”如果连这些话都不会说或者
周武王和他的股肱之臣们是如何相互敬酒的呢?他们是赋诗敬酒。
只管毕公高为客,周公旦为主,但这个酒席上还是周武王最尊,以是,最先发话的还是周武王。他端起羽觞敬毕公高,作诗一首:
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
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後爵乃从。
他的祝酒词实际上夸了两个人:毕公高和周公旦。在伐耆这场战役中,可能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都是最大的元勋。“庶民和同”,夸文治。“方壮方武”,夸武功。有这样能文能武的好兄弟辅佐,天下肯定安定恭顺——“穆穆克邦”。古人敬酒辞跟今人差不多的,也会说“快喝快喝,立时还有人等着敬你们”,用诗歌的措辞,便是“嘉爵速饮,後爵乃从”。
敬了毕公高,周武王接着敬周公旦,也作诗一首:
輶乘既饬,人服余不胄。士奋刃,繄民之秀。
方壮方武,克燮仇雠。嘉爵速饮,後爵乃复。
从周武王所作的诗看,彷佛周公旦也出征了,由于这几句描写的都是戎马征战。
周武王敬了酒,给全体庆功宴定了基调。接下来,就该周公旦起身敬酒了。他先敬毕公高,作诗一首:
贔贔戎服,壮武赳赳。毖靖谋猷,裕德乃求。
王有旨酒,我忧以浮。既醉又侑,嫡勿慆。
诗歌描写的,依然是戎马征战,只不过多了对毕公高的赞颂。他夸赞毕公高指挥若定,深谋远虑,心想事成——“毖靖谋猷,裕德乃求”。他劝毕公高,既然大王赏酒,就多喝一点,喝醉了也没紧要,来日诰日不喝便是了——“王有旨酒,我忧以浮。既醉又侑,嫡勿慆”。
周公先敬毕公高,这是对的。由于毕公高是本日庆功宴的主角。敬了主角,接下来,当敬“主公”了。他给周武王敬酒,作诗一首:
明来日诰日主,临下之光。丕显来格,歆厥禋明。呜呼!
月有成辙,岁有臬行。作兹祝诵,万寿无疆。
周武王是天子,以是,周公的诗从上帝讲起,境界顿时阔大起来:上帝看到我们庆功宴这么热闹,也从天高下来享用我们敬拜的馨喷鼻香了。跟周武王讲话,泛泛的称颂赞颂是拙劣的,周公没有这么差劲,他讲的是宇宙运行规律——“月有成辙,岁有臬行”,这里,对周王朝未来的发展有更深远的考虑。作为臣子,他祝愿他的兄长周武王“万寿无疆”。
祝酒词说完,正常是要一饮而尽的。但就在这时,一只蟋蟀跳到了堂上。周公见状,有感而发,又作诗一首:
蟋蟀在堂,役车其行。今夫君子,丕喜丕乐。日月其往 ,从朔及望 。毋已大乐,则终以康。康乐而毋荒,是惟吉人之䢍䢍。
蟋蟀在席,岁聿云暮。今夫君子,丕喜丕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作。康乐而毋荒,是惟吉人之瞿瞿。
蟋蟀在序,岁聿云徂。今夫君子,丕喜丕乐。日月其除,从冬及夏。毋已大康,则终以怙。康乐而毋荒,是惟吉人之瞿瞿。
此时,周文王刚刚去世,周武王刚刚继位,天下虽然岌岌可危,但还是商纣王的天下,周王室仍偏处周原。只管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试探性地伐耆,取得了胜利,但离真正攫取天下还有相称困难的路要走。看着酒席上君臣愉快地高歌酣饮,他不禁忧从中来,借助蟋蟀这个话题,告诫他的兄弟君臣,打了胜仗,可以高兴,但不要太高兴——“毋已大乐”“康乐而毋荒”,一定要有所戒惧,非常谨慎地走好今后的路——“惟吉人之䢍䢍”“惟吉人之瞿瞿”。周公旦的居安思危、深谋远虑、见微知著,令人敬佩。
清华简的这篇文章取名《耆夜》。耆,是这次战役所征伐的工具。夜的含义,学者争议很多。不过,从文中所附的几首诗看,所描述的场景的确是在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