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三位终审评委果评比,主竞赛及互助赛道的终选结果已经揭晓。感谢我们的互助伙伴:CathayPlay、后浪电影、和不雅观映像、IM两岸青年影展、FIGURE,为这次影评大赛设置了不同奖项,为参与者供应丰富的奖品。
接下来,凹凸镜DOC会选登这次影评大赛的获奖作品,本日揭橥的是得到凹凸镜DOC影评大赛一等奖的作品《掬水月在手》:词的祀礼,这篇影评同时还得到了IM华语记录影评奖。
颁奖评语:
影评兼具文学和电影理论的融通性,论述了影片《掬水月在手》如何以当代电影措辞和手腕来表现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美学, 深入而富有创造性地诠释了古典诗词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在陈传兴的电影中相得益彰:电影空间具象化了诗词的意境,词人及其词则授予了电影灵魂和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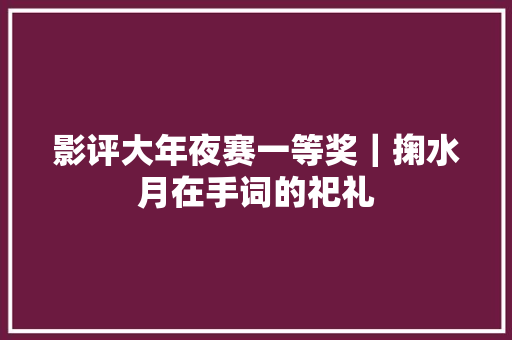
李啸洋的获奖感言为:
布罗茨基说:“美学是伦理学之母。”这句话适用于文学,但并不适用于记录片。记录片不是光杆棕榈树,记录片是一丛茂密的荆棘——记录片不是非黑即白的垂直判断,它永久将最茂密、最丰富的枝叶向不雅观众洞开,这些又和扎在地下的根系、思想、理念等密切缠绕在一起。记录片是连接文学与社会学的影像中介,不雅观众能从记录片中创造最意外但又最合理的东西,这便是记录片的魅力。记录片是社会历史薄薄的切片,不仅可以看到社会细微的肌理,还能看到刀切下时的痕迹。感谢记录片,感谢凹凸镜。希望记录片的火种能代代相传,希望活动越办越好。
1
空间、影象与诗的仪式
“回顾不仅是词的模式,而且是词偏爱的主题。”这是宇文所安研究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词时做出的判断。不仅词作如此,陈传兴执导的人物志的记录片也是如此。《掬水月在手》和《他们在岛屿写作:如雾起时》《他们在岛屿写作:化城再来人》一起构成了陈传兴的“诗词三部曲”——《如雾起时》拍的是台湾墨客郑愁予,讲述“当代诗与历史”;《化城再来人》以台湾墨客周梦蝶拍摄为工具,呈现“诗与崇奉”;《掬水月在手》拍摄墨客、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叶嘉莹,思考“诗与存在”。陈传兴用附近的路径拍摄三位墨客:以现在为出发点追忆往昔,进行编年叙事。
“格局”是用来描述空间的。大格局的墨客记录片拍空间,小格局的墨客记录片拍事宜。由于空间可以授予诗学,而事宜只能授予阐明。《掬水月在手》的阐述是从空间展开的。陈传兴以叶嘉莹北京的家宅故居为回顾出发点,将记录片分为“大门”“脉房”“内院”“庭院”“西厢房”“空无”六个篇章,以此来呼应叶嘉莹的人生阶段:“大门”讲日军侵华大破中国国门,叶嘉莹逢浊世降生;“脉房”讲祖父对叶嘉莹的诗词启蒙与性情影响;“内院”讲叶嘉莹师从顾随学诗,步入文学殿堂的低级阶段;“庭院”和“西厢房”则讲叶嘉莹在大陆与台湾两地飘零以及在西方讲学的经历(“西厢房”中的“西”对应的是西方)。末章“空无”则对应叶嘉莹老年的寂空境界——家宅的六重空间由内而外,重叠了诗词史和生命史,用陈传兴的话来说便是“古诗词的历史”和“一个女人的历史”。
记录片《掬水月在手》以家宅空间来分引篇章,是有深意的。家宅供应了分散的形象,同时又凝聚了精神的整体。对中国人而言,家既是详细的实在空间,又是形而上的归宿比喻。海德格尔说,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居”是只有家宅才有的功能。加斯东·巴什拉认为,家宅是母性的。家宅是反应的几何学,家垂直进入内心,对天下进行朦胧的重组。安家立业、一家之言、家国天下……中国人的家通达奇迹、人生、宇宙,家是天下的雏形。《掬水月在手》正是在“家”的集体意识层面上展开的,空间被提至主题层次。陈传兴阐明到,家宅空间是一所影象“宫殿”,空间里有分缘“会见”。不雅观众不仅与叶师长西席会见,更通过叶师长西席与诗词会见,与更迢遥的韶光影象会见。以诗和空间贯通全片,使空间成为具有想象力的形象的架构。经由诗化的空间,不雅观众聆听了一场词的电影阐述,感想熏染词的仪式。
弗朗索瓦·若斯特认为,任何叙事都是建立在两种韶光性之上的:“被讲述事宜的韶光性和讲述本身的韶光性。”通过空间布局,《掬水月在手》带不雅观众会见了两重韶光。第一重韶光,不雅观众与古典诗词的发展史会见。词在五代时为“歌辞之词”,宋代为“诗化之词”,后来朝着“要眇宜修”的方向蜕变。词的发展轨迹和诗的言志传统、道德化方向极为不同,文人可以用是非调的歌词去表达幽深弯曲的私人情绪,这是诗所不具备的功能。宋词可以写的很小(比如温庭筠),也可以写的很大(比如苏轼),收放自若。词脱胎于诗,又超越诗有了自己的特色,这便是词的双重性。
第二重韶光,不雅观众与叶嘉莹的私人精神史会见。叶嘉莹提出“弱德之美”(beauty of passive virture),“弱德”不是懦弱,而是指弱者也该当有倔强的信念操守,这种品质操守为处于困境中的人供应精神力量。《掬水月在手》考试测验回答叶嘉莹如何屡渡难关。答案是诗词——并非笔墨、词语层面的诗词,而是诗词的精神、诗化的人格。王国维讲“天以百凶造诣一词人”,尼采言“统统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这是为何?由于流亡、去世亡、苦难、孤独等各种不幸喂养着墨客。宋词中很少涌现“血”字,涌现更多的意象是“泪”,比如“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苏幕遮》);“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苏轼《江城子》);“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秦不雅观《江城子》)。诗词净化了各种苦难,将其“轻而化之”。“泪”使苦难化为悲切的情绪,这便是诗词的品质与力量。电影中利用了一些船只摆渡意象,亦是此意。朗西埃认为,诗歌依赖措辞的混沌力量,谢绝自身被意义穿越。为了补偿它失落去的形式的力量,诗会跃到界线的另一边,将思想的力量收归己有。陈传兴不但是在电影中呈现诗,而且让诗词与叶嘉莹的人生境遇相缔盟,以诗格来写墨客。
天下是诗中的详细。海德格尔认为,措辞的实质是道说(sagen),海德格尔将道说阐明为显示、显现,诗歌在“既澄明又遮蔽之际”,将天下“端呈出来”。诗是宗教之外靠近历史的一种措辞办法,藉由诗歌,民族文化的集体影象被唤起。哈拉尔德·韦尔策认为,文化影象有两个特色:一是认同的详细性,二是重构性。文化影象是对过去有组织、有仪式的沟通和交往,通过对一些形象的剖析与改造,影象的内容被持久地固定下来。文化影象依赖集体意识,依赖集体知识。《掬水月在手》中利用了很多文化痕迹,比如寺庙、石窟等,这些都是引发文化影象的空间场所,这些建筑从过去的时空摘过来,挪用到电影里,得到了意义的闪烁。
人生无韵便是诗。电影的末了一个篇章是“空无”,对应着叶嘉莹生命中的的老年阶段。不论是佛教中的空色之辩,还是诗歌中的空寂境界,“无”和“空”最难被授予意义,由于它须要从“有”和“详细”来出发。《人间词话》第五十五则提到一个主要的命题:“词无题。”王国维阐明道:“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 “无题之空”不仅是词的终极指涉,也是人生的终极指涉。电影后半段,叶嘉莹回到了蒙古原乡,回到了叶赫那拉部族从前的居住地地叶赫古城。电影末端有佛像落雪的镜头,也有雪地爪痕的镜头,这是物留下的痕迹,是标准的影像用典,它对应的正是苏轼的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依赖蒙太奇规则,依赖用典,依赖空间修辞和二度润色原则,电影为不雅观众呈现了一场诗词的影像仪式。
2
物的韶光与文学的“景深”
残荷、铜镜、壁画、石本、墓志铭、浮雕、瓦当、佛像、雪景、水波、照片、书信、染布……《掬水月在手》从宋词中汲取了物之元素,词中景物与叶嘉莹的个人生活史天生对影、荡漾。这些物镜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景物、文物(器物)、旧物件。电影利用物的空镜头进行表意。物镜头有何叙事含义?陈传兴这样阐明:“(这些物)展现了诗很主要的存在面向:咏诵,礼赞。”按陈传兴的阐明,电影中的美典化的物象即是诗本身,它们是文化的源始。
物是诗的显像,诗词用措辞为物重新命名。墨客召唤物,令物到来。墨客利用词语,召唤人进入词语当中。归天之际,物才对文学洞开;归天之际,物才实现天下、展开天下。物语,是宋词语,也是电影境语。《掬水月在手》中,物不仅仅是物本身,更承载了用典和咏史背景。例如,电影中涌现的铜镜即是对花间词鼻祖温庭筠《菩萨蛮》的文化投射:“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再如,电影中涌现的水上“枯荷”,意在召唤古代汉语里的“菡萏”。“菡萏”是诗词对荷花的别称,“小荷”是叶嘉莹的乳名。“水中枯荷”对应的是南唐中主李璟的词作:“菡萏喷鼻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这首词在叶嘉莹所著书中被反复提及。枯荷的镜头用在此处,便有了一种与吊唁、失落落有关的感情,有了一种哀婉的氛围。
掬水月在手,弄花喷鼻香满衣”是唐代墨客于良史《春山夜月》中的诗句,这是一种美典体验。高友工提出了“抒怀美典”(lyric aesthetics),所谓“美典”即是一种美学履历,它进入文化传统和集体意识中,被内化、传承。美典化的景物,不仅是宋词的面纱,也是影像透明的身体。落花、流水、寒草、谢月、冬雪、轻烟,景物分开了自然之意,进入到宋词的美典布局中。《人间词话》里,王国维花了很大精力来阐释景物之于宋词的意义。比如“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人间词话》第六则)那么,该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写景物呢?王国维答道:“墨客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仆众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人间词话》第六一则)然而,态度上轻与重,又该如何把握呢?王国维又言,对自然景物要抱着“半出半入”的态度:“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入乎其外,故能不雅观之。”(《人间词话》第六〇则)“境界”即是建立在词人对景物的处理之上的。
宋词对景物的处理很奇妙,王国维说要以自然之眼不雅观物,以自然之言说情。景物若没有被纳入到艺术构造中来,便和走马不雅观花式的旅游没什么差异:“词人之虔诚,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虔诚之意,否则所谓游词。” 宋词中若何“虔诚”处理景物,才算一种合理的办法呢?王国维阐明到:“合乎自然”——写境和造境中的景物,要做到主不雅观化的自然而然,就像自然界之物相互相干、相互限定那样。王国维对景物的这评论,触发了宋词中虚实关系的思辨,也引发了张炎在《词源》中“词要清空,不要质实”的思考。
电影利用物与景象,依据的并非履历天下的法则,而是蒙太奇的原则。物搬离生活场景,被电影重新组织,抖擞出新的神采。看似无序排列的物,实在有精心的构思,有深刻的寓意形式。朗西埃认为,诗歌措辞“处于形象的详细性和物质材料的韶光厚度中。”物沉淀了历史,旧物与诗的目光相遇时,历史得以复活。当器物、诗词和影像相遇时,“影象”的主题和诗的实质便得以显现,物唤醒了典故和形象,让诗词的花火四处迸溅。
记录片《掬水月在手》中,景物和器物不再纯挚是道具或者印迹,而是裹挟了韶光的力量。罗兰·巴特提出了“物的韶光性”,这个韶光“意味着后来有个韶光”,使物“如宿命般运动”。在罗兰·巴特的阐述中,物有韶光的深度。物在韶光的长河中淘洗,它们是完全的过去消逝之后的痕迹与证据,隐伏于典故、碎片和审美影象中。《掬水月在手》的紧张情节是叶嘉莹的平生业绩(出生、婚姻、家庭、奇迹),景物是次要的、偏离正题的内容。景物镜头是环抱天体运动的行星,它属于“宋词”这个天体。可以说,诗词才是《掬水月在手》的始动力量,环绕它展开的紧张情节、次要镜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掬水月在手》的构片思维用的正是诗性聪慧,景物具有高度的隐喻性。电影架构的意义路径是“以己度物,以物渡人”,影片中涌现的“渡船”和“菩萨”便是例证:刘秉松说叶嘉莹生平波折,是诗词救了她。“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诗词将叶师长西席的苦难都化淡了,诗词是她命中的渡船人。
《电影是什么?》中,巴赞基于长镜头和景深镜头的技能理念,提出了韶光的“木乃伊神话”。物作为过去的媒介,使韶光“布满缝隙的透视镜”。 物用断片进行招魂,它的四周是韶光的吸引力,它与《圣经》中的太初有同样的含义。影像中,壁画、碑拓、雕像等物象和宋词关联在一起,便拥有了完全的美学韶光。空镜头本身便是美学瞩目,它带领不雅观众回溯韶光之河,变成怀古之辞里的韵脚、断句。蒙太奇的功能之一便是装置,当物与宋词、声音组装在一起时,物便有了别样意义:物是诗的寂静之音,是词的敬拜礼,是文学的“景深”。
3
吟诵与声音诗学
“若欲相见,只须于悄无人处,呼名。”记录片《化城再来人》中,周梦蝶朗诵了《善哉十行》中的这句诗。周梦蝶生于河南,内战时随军撤到台湾,在台北闹市摆书摊为生,生平悲苦。声音是一种分外的媒材,通过周梦蝶念诗的声音和其飘零的生命境遇,陈传兴呈现出他是一个有崇奉的人。记录片《掬水月在手》中,吟诵和雅乐是电影创作的一个主要特色,陈传兴这样阐明:“声音,让措辞成为了象征的一种可能性,而非象征的载体。”
银幕上朗诵诗词意味着什么?声音与诗歌起兴、创作有什么关系?声音和美学有何关系?本雅明在谈到欧洲视觉艺术(油画、摄影等)进行媒介复制、空间转移时,思考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光晕”的消逝。那么,电影中吟诵诗词,是否也会使诗词文本损失原真性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由于,诗歌起源于声音,而非源于视觉或者笔墨。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提到,集体劳动的号子声“杭育杭育”是早期的文学创作。诗出身之初,已经埋藏了声音的种子。“杭育杭育”是声音的歌谣化呈现,它使劳动合营着身体的节奏。
对诗的感知,首先是由声音打开的。汉乐府如是,宋词亦如是。宋词出身于酒宴之间,是文人交给歌女的酬唱歌词,内容多为相思别离,与《诗经》中的伦理教养相去甚远。 温庭筠的词集《花间集》内容描写俏丽的女性,比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闪动,鬓云欲度喷鼻香腮雪”。宋词经历了诗化的过程后,才逐渐走出女性题材,将书写扩展到更广袤的生命境界,逐渐有了诗的气度胸襟,比如苏轼、辛弃疾的词。宋词最初是邪狎淫靡的“喷鼻香歌艳曲”,但是经由雅正之后,逐渐变成全新的文学文体,从写秀语深情,开始写情绪境界。叶嘉莹认为,词至柳永时便开启了“慢词长调”时期,柳词以声音作为媒介流传。宋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这样评价其词:“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新诗割裂了诗的声音传统,去掉了押韵平仄的束缚,去掉了形式规制,让声音的基因休眠。消灭声音的维度后,新诗变为纯粹的视觉文本,只能以目得诗,不能以声得诗;只可不雅观看,不可吟诵。
诗是玄学的措辞,玄学每每追求本源性的东西,声音便是中国古诗的本源。声音,最贴近于人的存在实质。亚里士多德在《阐明篇》开篇写到:“声音是心灵体验的符号,而笔墨是声音的符号。” 以声印心,正是中国古诗的特色。陈传兴以“墨客忧生”的基调来做电影配乐。根据杜甫的律诗《秋兴八首》,日本作曲家佐藤聰明为本片创作了雅乐。雅乐以哀歌的形式,怀想孤悲的远古韶光。《掬水月在手》中的雅乐和吟诵,如萨满召唤神灵——声音将自身许诺给墨客,以此来唤醒影象。叶嘉莹说:“墨客的生命在你的声音里复活。”吟诵是抒兴最直接的形式,吟诵授予诗词以声音的持重感、仪式感。西方的诗可念可读,但不可吟诵。吟诵是中国式特有的办法,它保存了中国人说话特有的声息。法国象征主义墨客保罗·瓦莱里认为,诗歌是“徘徊在意义与声音之间的一种若即若离的觉得。”瓦莱里称法诗是“高等交响乐”,法诗稠浊了散文和诗的双重措辞,它不因此声音为中央的,而是通过措辞交响,逐渐埋伏意义的。瓦莱里利用交响乐这个比喻,意在解释声音是西诗文本的遮盖物。
南宋词人张炎说:“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择曲名,然后命意。”写词的工序中,声音在先,笔墨在后。中国古诗词讲究声音规律,环绕声音的诗词格律著作就有《切韵》《广韵》《平水韵》《佩文韵府》等,它们是独立于汉字字典的“声典”。这些声典韵作将韵部标准化,是做诗用词的声音依据。韵浸染声音规定了平仄与押韵,也将措辞的形式规格固定下来,形成规制:字数(四字、五字、六字、七字、九字、参差杂言)、句数(四句绝句,八句律诗、多于八句的长律等)。宋词起初被称为“诗余”和“是非句”,被打消在诗的范畴之外,后来才为自己的文学合法性正名。宋词发明了是非调,形式上参差错落,和去世板的诗歌形式比较,宋词唱起来更灵巧。如梦令、苏幕遮、忆江南、鹧鸪天、水龙吟等皆非词题,而是词牌名,即用什么歌调来唱。作词首先要选择声音程序,其次才进行笔墨创作。《毛诗序》中写到:“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敷,故太息之;太息之不敷,故咏歌之;咏歌之不敷,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作者接着写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由此可见,在笔墨、声音、舞蹈的排序里,声音的表达层次比笔墨更丰富。
借助于电影媒介,吟诵重新创造了声音,诗词实现了声音的复活。记录片《掬水月在手》中,陈传兴创造了新的聆听关系,使谛听归本于寂静之音。影片通过雅乐与吟诵,宋词在笔墨层面的意义外,回到了韶光的观点。正是有了声音的条件,才有了清代词学家张惠言对宋词的评价:《<词选>序》“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冲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 “低徊要眇”便是是非句的声音气息,弯曲反复,一唱三叹。吟诵使诗词回到了正宗的声音源头,回到了“兴”。吟诵,使诗词活色生喷鼻香,有声,有息。有声有息才有了词牌名“声声慢”,才有了“慢词长调”的呼吸节奏。
阿多诺说,艺术品的实质是否定的。墨客作甚,苦难的时期为什么要有墨客?海德格尔给了一个模糊回答:孤寂。孤寂是人在世界的位置,也是墨客的精神。墨客忧生,词人忧世。墨客的职责,便是用措辞的艺术见告众人在世的孤独。朗西埃认为,诗是一种思想,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能够无限反思自身。 朗西埃所说的,正是诗的内生力量——诗词中可归隐。墨客和词人用作品建立起一座座寺院,引着词语的烛火,带领众人走上遁隐之路,来到笔墨的寺院修行,进行灵魂避难。
柏拉图要将墨客逐出空想国,情由是诗不能认识真理,只是徒增真理的幻影。诗词是模拟,是理念的影子,但词之言长,词之境阔。 《华严经》将人际关系比作众生照镜,镜照过程中“逐一影中复见众影,重重现影,成其无尽复无尽。”诗词是一壁鉴照众生的镜子,诗词是中国过去时期的大众文化,中国曾以诗词来代宗教、代美学、代哲学的。布罗茨基认为,美学才是伦理学之母。 "大众可以不知社会律法,但是无法避免日常文化的感化。诗词超过了边界,兼具了文学与哲学的双重功能。诗歌是措辞最纯净的火焰,诗歌所言既是天下的开端,又是天下纯粹的完成。通过墨客,天下的意义不再被封闭于现世、此刻、当下,而是被词语带入美学体系进行净化,见证“不灭”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