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该当是姜太公姜子牙,他隐居渭水,直钩垂钓,愿者中计,以80岁高龄得遇周文王,首创了周朝800年基业。
他虽具隐者之形,钓的却是功名。
还有一个便是在《史记》中与屈原对话的渔夫,他劝屈原“全球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醴?全球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
可见这是一位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看破尘凡的渔夫形象;当然也很有可能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反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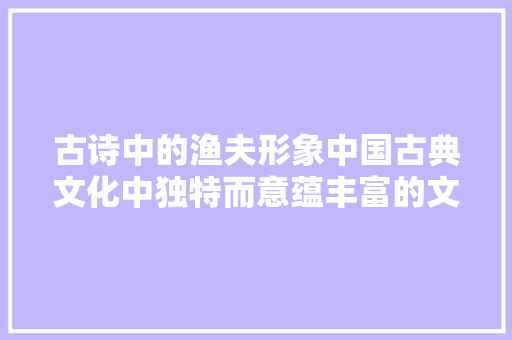
还有一位便是在古代诗歌中常常涌现的严子陵的形象。他是汉光武帝刘秀年少时的同窗好友,刘秀得天下后对他优礼有加,与他相见都是分庭抗礼。而他终极选择了谢绝高官厚禄,垂钓富春江,留下了古钓台的遗迹,隽誉千古流传。
那么,这三个人可以说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渔翁”,而是带有政治色彩的隐士高人的形象。可以说,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渔翁形象大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那么就让我们欣赏几首这样的诗词,来详细地感想熏染一下。
首先便是柳宗元的《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涯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你看,这位渔翁他阔别尘嚣,独来独往,自由清闲。他独自住在西山之下,连日常生活都是那样的充满诗意:清晨汲取的是清澈的清江水,烧火做饭都是用的翠绿的、曾经浸透过娥皇女英泪水的楚竹。他的生活环境是多么的寂静雅洁,他处身于青山绿水之间,就像那山上的白云一样随意飘浮,无欲无求,悠然自得。
同样的还有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在柳宗元笔下,这个渔翁的形象显得更加的孤芳自赏,高洁孤傲。
实在,这类形象正是墨客自我的写照,透露出寄情山水的思想,寄寓着政治失落意的孤愤。
再欣赏一首我们非常熟习的《三国演义》的卷首词《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东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滚滚的历史年夜水,淘尽了多少英雄的劳苦功高。一个个王朝兴亡盛衰,悲恨相续,只有大自然是永恒不变的。而长江边白发的渔樵们,他们看惯了这些历史的沧桑变革,古今的英雄业绩都付于他们的笑谈之中。
可见,这首词中的渔人樵夫形象又是一种看破尘凡、看淡世事、唾弃功名、无拘无束的隐者形象。
总而言之,古诗中的渔夫形象有一定的共性,都是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隐士高人、世外之人的形象。
他们每每是文人在经历官场坎坷失落意后,转而选择淡泊明志,归隐田园,而在诗歌中将其生活态度寄托于渔夫。他们的生活是自由清闲、无拘无束、散逸恬淡的;他们的脾气是高洁孤傲、超然物外、旷达乐不雅观的;他们对待功名利禄的态度是看破尘凡,看淡世事,唾弃功名。
再如陆游的《鹊桥仙》: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壮举。醉翁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君恩赐与。
当年豪放热烈的军旅生涯还有谁记得?那些只知饮酒享乐的醉翁大都封侯拜爵了,而“我”却只能去做一个闲散的渔夫。但那又若何?“我”独自享受这美好的镜湖烟雨,哪里用得着你官家恩赐。
这首诗作于陆游被弃置不用的期间,结合当时的时期背景,很随意马虎理解陆游的思想情绪:对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对时期不公的不平之气和愤世嫉俗之情以及被迫归隐的无奈和牢骚。末了一句更是将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表达了对“君恩赐予”的不屑。
可见,虽然古诗中的渔翁形象有很多的共性,但在不同的诗歌中,又具有不同的个性。这首诗中的“渔夫”虽然所处环境依然是幽美的,生活依然是闲适的,但二心坎却并不是完备抛却尘凡的,由于他肚量胸襟大志,却遭弃置,是无奈归隐,以是表现得满腹牢骚。
以是,我们鉴赏渔夫形象既要节制共性,又要关注个性。
请再看下面这首《渔家傲引》(宋·洪适):
子月水寒风又烈。巨鱼漏网成虚设。圉圉从它归丙穴。谋自拙。空归不管旁人说。昨夜醉眠西浦月。今宵独钓南溪雪。妻子一船衣百结。长欢悦。不知人间多离去。
显然,这首词中的渔夫形象与前几首中的有所不同,不同于直钩垂钓、志不在鱼的隐士,他是一位真实的劳动者的形象。“妻子一船衣百结”,生活是艰辛的,纵然水寒风烈,也要下水捕鱼,否则一家的生存可能就没有着落。
可是,他又是旷达乐不雅观的,也能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和难得的闲适,尤其是结尾写出了渔家生活“虽贫也乐”的特点,他们一家团圆,尽享明日亲,不必为名为利奔波,这时的渔夫就又有了一些隐士高人的风格了。
以是说,古典诗歌中,“渔人”形象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中独特而意蕴丰富的文化符号,看到这个意象词就会引起人们很多丰富的遐想,这大概是西方文化中没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