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章值得学习,一起看看吧。
感激您的阅读。
原创: 边地星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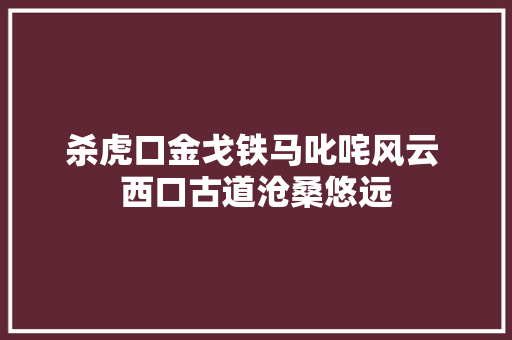
黄土高原博大雄浑,在山西北部逶迤绵延,与蒙古高原携手一起走来,透露出气概的风骨,张扬着桀骜不驯的个性,给人一种伟岸高大、苍凉悠远的觉得。在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晋蒙交界处,一座雄关巍然耸立,它北倚古长城,西临苍头河,扼守要冲,俯视苍生,气吞山河,千百年来,它见证了胡汉和亲,金戈铁马的激情岁月,体恤了晋商艰巨创业,驰骋他乡的激荡肚量胸襟;记录下一代代背井离乡走西口人的心伤和忧伤。
雄关险隘
杀虎口距右玉县西北35公里处,是外长城一个主要天然关口。据《朔平府志》载:“长城以外,蒙古诸蕃,部落数百,种分为四十九旗。而杀虎口乃县直北之要冲也,其地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要。”杀虎口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北依雷公山、庙头山,两山之间是开阔的苍头河谷地,万里长城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而去,像个半圆形围墙将杀虎口围在里边,东西两侧山岭崖陡壁立,苍头河由南向北贯穿个中,构成一道宽200多米,长3000多米的天然关隘。杀虎口作为一代雄关,有名遐迩,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因其分外的地理位置,自古便是南北主要通道,历代王朝都在此屯兵遣将,设置防守。
杀
杀虎口古称参合口,也称西口,历代叫法不同。唐称白狼关,宋名牙狼关,明称杀胡口,清改杀虎口,民国叫杀虎关。杀虎口是雁北外长城最为主要的关隘之一。山西北部自古便是边地,早在《诗经•风》中,就有《出车》描述杀虎口一带抗击外敌的诗歌:“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旗旌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猃狁作为北方早期少数民族,常常袭扰边疆,中原王朝派出边将奉命征讨。右玉县在战国期间属赵,赵孝成元年(公元前265年),赵国就派重兵驻守雁门一带,戍边大将李牧曾多次从这里出击,抵御匈奴的反攻袭击。秦为“善无县”,计策地位非常主要,大将蒙恬率军驻守防御匈奴。
汉代大将李广、卫青、霍去病也曾从这里挺进大漠,驰骋疆场,终极封狼居胥,百代流芳。汉代苏武持节从杀虎口出使匈奴,自知一起凶险,出路未卜。王昭君出塞途卧羊山顿生悲痛之心,马蹄犹豫不前,留下“立马皆不发,盘石成蹄窟”的传说。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发丁男百余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即今右玉境内的苍头河),一旬而罢。”炀帝作《幸北塞》:“鹿塞鸿旌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稽颡至,屠耆相继来。索辫擎膻肉,韦鞴献酩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唐贞不雅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领兵从杀虎口出塞,消灭突厥20余万众。为了庆祝这一大捷,唐太宗李世民写下了《饮马长城窟》。
明王朝为了抵御北元的袭扰,遂设置九边,明长城穿杀虎口而过,一韶光古堡、烽燧林立,气势壮不雅观,特殊是杀虎口段,砖石砌面,筑有城楼、望台等很是壮不雅观,此时的杀虎口成为外长城的主要关隘。杀虎堡位于杀虎口东南1公里处,由杀虎堡(旧堡)、中关、平集堡(新堡)组成。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周二里,高三丈五尺。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在杀虎堡南百米外又兴建了一座同样规模大小的新堡,名为平集堡。后来由于边贸繁荣和人口繁盛,在两堡中间筑东西两墙,二堡之间被围起来形成一座封闭的关,名为中关,全体城堡平面呈“目”字型,从南到北形成三连环式的堡城,成倚角互援之势,大大提高了杀虎口的防御能力。杀虎堡地处繁华要道,随着商贾云集,一度人口骤增,极盛时住户达3600户,近5万人。各种衙署、寺院、学堂、牌楼遍布堡内外,宫不雅观寺庙共有50多座,其繁华远近有名。
杀虎口和右玉城做为明王朝北部军事要塞,战火不断,特殊是明正统至嘉靖年间,曾多次从杀虎口出兵征战,抵御蒙古瓦剌、鞑靼南侵。隆庆四年,双方才化兵戈为玉帛,蒙汉通商自此开始,杀胡堡、得胜堡、新平堡(天镇)马市重新开放马市,每当通商期间,鞑靼人“逐日蜂聚堡城,任意流连,信宿不去”。
清康熙三十五年,帝西征凯旋,在杀虎口设宴请西路军有功将士,杀虎口成为清廷后勤基地,一韶光,商贾云集,南来北往,成为北方最大的商埠。达到了“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的盛况。康熙帝统一了蒙古诸部,南北一家亲,“杀胡口”的名字带有毁坏民族联络的意思,康熙帝为杀胡堡题名,改“胡”为“虎”,真可谓“恩波洵不遗穷谷,帝力博识未易名”。此时的杀虎口计策地位虽然没有明朝期间主要,但仍具有十分主要的军事意义,亦有兵丁驻守。
到
到了1925年,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进驻“杀虎口”,任命其十三太保之一的韩多峰为杀虎关镇守使。韩为了缓和民族抵牾,促进中原地区与塞外的贸易,遂沿袭自清朝以来的俗称,改名为“杀虎关”。杀虎口见证了金戈铁马、烽火狼烟,沧桑玉帛,世道兴衰……如今,作为抵御外敌的雄关险隘,早已失落去了昔日的功效,掩映在一片绿洲之中,历经岁月洗礼,斑驳破旧,但仍可见其雄伟的气势,瑰丽之风采。
到
通商口岸
历史上杀虎口既是主要的军事要塞,也是主要的“边防口岸”。军事和商业这两个彷佛不干系的事,在杀虎口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由于山西十年九旱,百姓为了觅食求生,形成“走西口”的迁徙群体。他们涌入归化城、包头城、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逐渐从谋生提升到求富的阶段。走西口的山西人把西口的路走宽了,走熟了,走出了晋商的大小商团,走出了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业成本源远流长,山西贩子的生动,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期间。明朝期间,蒙汉在长城一线进行民间贸易,互通有无,隆庆四年正式开关,关贸进一步扩大。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履行,为晋商的发展供应了契机。杀虎口成为内地贩子对蒙俄贸易的商路上主要的商品运输枢纽,政府在此设置税卡,在北上、西去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条固定的晋蒙大通道,人们习气上称之为“西口古道”。学术文献中谓之“晋商驼道”“晋商驼道”起始于先秦,下至民国,历经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晋商驼道分“南三线”和“北三线”,其紧张枢纽为“一关、一店、三口”:即北有山西代州(今代县)雁门关、南有河南赊旗店(今社旗),以及山西右玉杀虎口(俗称西口)、河曲黄河渡口(亦称西口)和河北张家口(俗称东口)。“北三线”即晋商东北驼道、晋商华北驼道和晋商西北驼道。便是人所共知的“走西口”,指的是晋商从雁门关或历经太原、静乐、宁武的汾河谷地北上走出内长城之后分为三路北上:一是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张家口远赴东北驼道,二是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右玉杀虎口远赴华北驼道,三是至广武经河曲黄河渡口远赴西北驼道。经杀虎口向西北而去的西口古道方便快捷,成为首创空想,走南闯北的大通道。
康熙征噶尔丹时(1696—1697年)期间,山西太谷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张杰、史大学三个人随军搞军需供应。时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部驻防杀虎口,他们随军至外蒙的乌里雅苏台(前营)和科布多(后营),之后以三人为主体,结合杀虎口的几个人组成集体小商伙吉盛堂(大盛魁)。当时专门走草原到蒙民中去贸易的山西贩子由于会说蒙古语,称为“通事行”。最大的“通事行”便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曾经盛极一时的“大盛魁”店铺的发祥地就在杀虎口,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店铺,成本近亿两白银。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大盛魁职员极盛时超万人,骆驼2万峰。其经营范围之广、贸易总额之大超乎人们的猜想,获利之多、韶光之久,在我国民族贸易史上是罕见的。
雍正十五年,朝廷调集大军,平定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正当朝廷高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山西贩子担当重任,将征集来的十三万石军粮运往前哨,但不幸被叛军劫走,他变卖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再一次买粮补运。范家以“毁家抒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赖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年夜方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三盛公”和晋商有着很深的渊源,若要理解三盛公,就必须从“走西口”必经之路杀虎口提及。清王朝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休养发展,到了乾隆期间,全国人口打破3亿大关,人口与地皮问题抵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无奈之下“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下南洋”。乔贵产生发火为晋商走西口的代表人物,于乾隆年间沿着山西的中部出发,一起向西,杀虎口到内蒙古,在包头一个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乔贵发(华)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改名为复盛公。因乔家做生意最看重诚信,复盛公买卖兴隆,及至乔致庸成为乔家第二代掌门人时,复盛公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店铺,险些垄断了全体包头市场。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当时乔家除在包头有11处生意外,其它地方还有非常多的店铺。
晋商雄风
明清期间,杀虎口成为晋商的发源地和主通道。1690年开始,随着康熙天子西征,杀虎口已成为运送粮草的大本营,从康熙、雍正、乾隆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山西贩子看准机会,随军贩送粮草,杀虎口作为华北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是中原与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俄国贸易的必经之路,清政府不仅在此驻兵操练防守,也在此设税关,清极盛期间,关税日进“斗金斗银”,政治、经济同时达到了最壮盛的期间。军事和商业两大缘故原由,让杀虎口繁荣至极。商贾云集,车水马龙,豪商巨富,坐拥荣华。在京包铁路尚未开通之时,杀虎口仍是中原和漠南的通衢要道,以浩瀚的人口,兴隆的商业,发达的文化,星罗棋布的古迹而远近知晓。
清代形成大一统格局,加之清朝对蒙古采纳怀柔政策,实行喇嘛教,大兴寺庙,大量招徕山西、陕西、河北工匠和破产农人外出谋生。出西口后的经营地域紧张是三大营地:前营、后营、西北营地。前营即乌里雅苏台一带,后营即科布多一带,西北营路则是北雅尔、伊犁、古城子(奇台)、红庙子等处。据《绥远通志稿》说:“绥为山西辖境,故做生意于此者多晋籍。其时投运货色,经由杀虎口交纳关税后,至归化城行销。”这里的山西贩子,分行商与坐商,行商贸易于大青山后和西营一带,需向绥远将军署领取理蕃院颁发的“龙票”,这种“龙票”不仅便于清政府管理,而且对旅蒙商也是一种分外照顾,持此“龙票”贸易者,“蒙户如有拖欠,札萨克有代为催还之责,且旗长对付此等商户,纯以礼客遇之。”以是旅蒙商很少亏折,获利巨厚。行商驱赶着骆驼队,分赴前营、后营及西北营贸易。这种贸易途中没有旅店可宿,须结驼队行进,自携锅帐。驮运出去的商品,以绸缎、布匹、茶、糖、烟为大宗;运回的物资,以绒毛、皮毛、各种畜生为主。重新疆方面回来的还有白银、金砂、鹿茸、葡萄干、杏瓜之类。运回的货色有一部分在丰镇、归化、包头出售。大约每年将二十余万只羊卖给京羊庄。鹿茸开市之时,交易量日达20万两白银,甘草约50万银元。
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贩子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贩子,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担保了后勤之需,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贩子独占其利的做生意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
从清代1644年—1840间,山西贩子的货币经营成本逐步形成,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蒙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全体亚洲地区,乃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喷鼻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贩子的足迹。当时中国从陆路对俄、蒙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迪化(乌鲁木齐)、莫斯科、库伦、科布多、彼得堡等十多个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店铺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贩子的贸易也很生动,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险些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入口和百货输出。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贩子。”晋商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生动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亚洲大地上留下了残酷的商业文化。
杀虎口见证了太多的金戈铁马,周征猃狁,汉伐匈奴,隋唐伐突厥,宋伐契丹,明讨蒙古,清康熙玄烨帝亲自率兵出征蒙古葛尔丹,均经此地。杀虎口见证了商贸往来的繁荣,有“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之称。历来山西贩子“走西口”走的便是杀虎口,杀虎口成为晋商孕育地之一,走西口造诣了晋商的辉煌。伴随着交通的飞速发展,这个繁荣了五百年的古税关也逐渐停滞了运转。昌盛百年的杀虎堡和平集堡随之走向衰落,仅存的残垣破屋,古道土墙向后来者诉说着昔日的辉煌。所有的统统都消逝了,杀虎堡的古老影象也随着岁月逐渐消逝。金戈碰击声没了,悠悠驼铃远去了。长城睡了、店铺睡了、古堡也睡了。只有那首柔肠凄凉的绝唱《走西口》,还留在人们的耳畔。传唱数百年,越唱越红火。当年无数的山西人通过“走西口”而有了活路,生活有了盼头,晋商精神如是,走西口如是,但总有一种精神不会散去,那便是一个个先辈们的开拓精神永久散发着不朽的故事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