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看我对诗词感兴趣,请教我一些格律诗的根本知识,如诗韵、平仄、对仗等等,我初步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也试着写了几首“打油诗”,经父亲指示,有了一点提高。
1969年初,我和姐姐、哥哥一道,下到浏阳沙市公社当“知青”,我把平时抄在小本子上的《词牌韵律》也带在身上。在屯子,每天和社员一道出工、收工后还要种菜、挑水,打柴,忙完这些后天已经断黑,只想早点安歇,根本没韶光、也没心思去做别的事情了。
1969年,根据当时的国际海内形势,毛泽东发出了“三线培植要抓紧,便是同帝国主义抢韶光,同改动主义抢韶光”等一系列培植三线的指示。为落实三线培植这一重大计策决策,推动计策大后方的经济培植和国防培植,1969年,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建筑醴陵至茶陵的湘东铁路(现称醴茶铁路)。1970年9月成立了湘东铁路培植指挥部,由浏阳、醴陵、攸县、茶陵、酃县、安仁等6县12万民工(当时叫民兵),按部队的体例分成师、团、营、连,投入湘东铁路培植会战。我们姐弟三人,也积极相应号召,和浩瀚农人兄弟一道,奔赴攸县,参加湘东铁路培植。
1970年11月,我们挑着大略的行装,随全公社2000多名筑路大军(体例为一个营),步辇儿180公里,来到攸县皇图岭,我们连在攸县二中附近的一个生产队驻扎下来,我姐和全公社所有上阵的女“民兵”们,被编为2个“娘子军”连,驻在附近另一个生产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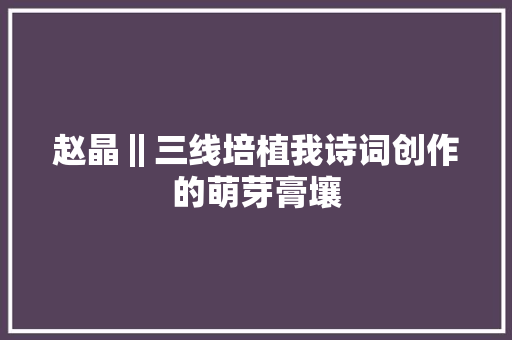
第二天,我们全体民兵就投入了紧张而又繁重的修建路基的土方作业劳动。
我们营的任务是修建一段大约2公里长的路基,既要挖开一段长300多米,宽10米,最高处有10来米的小山,又要将挖下的黄土去填高六七百米长的一段低地。那时的施工,没有任何施工机器,完备靠人海战术和最原始的工具,锄挖肩挑。但是,工地上热气腾腾,民兵们干劲十足。工地上,每隔几十米就插着一壁印着某团某营某连字样的红旗。在回填的路基上,每填高一尺旁边的松土,就有打夯的民兵,每四人为一组,喊着歌声和号子,将一个100多斤重的石夯高举过分,再落回地面,利用其重力,将松土夯紧夯实。最值得钦佩的是那些女民兵,她们都是20来岁的大姑娘,但是,干起活来,不管是挑土还是打夯,都是巾帼不让男子,乃至在生理期间也不安歇。
当时参加建筑铁路的民兵的报酬是:每人每月36元。个中15元作副业收入交回各自的生产队,每天按标准工记工分,参加年终分配,15元交连队食堂作炊事费,余下6元作为津贴,由民兵个人支配。没有节假日和工休日,除非下大雨,否则每天要上工地,干满8小时。只管这样,没有任何人有怨言,相反,每月6元的津贴费,对当时的农人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工余韶光,不要自己做饭种菜,空隙韶光多了。目睹工地上风起云涌的热烈气氛和民兵们冲天的干劲,我不禁萌生了写作的激情。当时营部、团部都办了小报,我便写些通讯、散文和诗词之类的稿件去投稿。那些文章现在早已忘了,但写的诗词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下面这首七律,是1971年元月所作,这也是我写的第一首格律诗:
七律·新春咏怀
大地春回旧岁残,英雄筑路战犹酣。
涔涔热汗濡衣帽,凛凛寒风卷旆旃。
铁臂筑成千里路,银锄劈断万重山。
赤心报国修三线,铁马引来幸福泉。
我们营卖力修建的路段中有几个涵洞,须要大量的石头砌筑,而石头须要从五六公里外的坪阳庙山里运来。那时没有运输工具,只能靠肩膀挑。为了不延误工期,涵洞必须要提前完成。有一段韶光我们每天天不亮,号声一响就要起床,去山里挑石头到工地,来回20余里,每每挑回来时天刚刚放亮。
如此繁重紧张的劳动,却也引发了我的诗兴,在一次挑石头的途中,我触景生情,脑海中填词一首,回到驻地立时写到了本子上:
忆秦娥·坪阳庙凌晨运石
冬残月,
催征号角夜空裂。
夜空裂,
披衣疾起,北风寒冽。
百斤石担双肩迭,
运途十里难稍歇。
难稍歇,
东方清晨,凯旋心悦。
经由两个多月的苦战,我们终于在1971年1月中旬基本完成了路基的修建任务,后续的工程已经不须要这种“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因此,大部分的男民兵和所有的女民兵,在春节之前“班师”还乡,留下三分之一旁边的男民兵进行缩编,连续完成后续的培植任务,我也留了下来。
我所在的连和其余两个连的民兵合编为一个连。3月尾,我们接到命令,到攸县网岭以北9公里的宁家坪建筑一座跨河铁路桥——大塘桥。
我们连驻扎在离大桥工地1里远的一个生产队,紧挨联兴河边,每个班安排住在一户农人家里。当地的民宅都是土砖砌成,底层上面还有一层小阁楼,我们都被安排住在小阁楼上。只有连部的女卫生员和连长、辅导员住在楼下正房,算是分外报酬了。阁楼只能从表面墙上搭的一架木梯子高下,出入甚是不便。阁楼里中间高、两头低,中间高也不过比一个人稍高一点,低处就只有半个人高,头顶上便是一排排的瓦,稍不留神,脑袋就会撞到瓦上。木楼板上铺上一长溜稻草,上面再铺上年夜家自带的草席,这一溜大通铺就成了我们的“床”。
大塘桥超过联兴河,是一座双拱混凝土大桥,跨度大约200米。我们来时,三个主桥墩已经露出水面,是前期民兵军队所建。我们的任务,便是合营铁路桥梁专业施工单位——铁建五公司,完成桥墩以上的主体工程。
桥梁的支模、扎钢筋、操作施工机器、水、电、木等技能工种,全由五公司的工人师傅承担,我们这些民兵,则承担了所有的重体力活。
工程须要大量的混凝土,为此,连里抽调一个排,到十几公里外的坪阳庙山里放炮采石,将大块的花岗岩用汽车运到工地,再用破碎机打碎成大小得当的碎石,沙子则全靠我们从河边的沙滩挑到工地上。所幸联兴河岸边的沙滩很长,很宽,有大量的优质河沙可以直接用于混凝土,这个天然上风,也为工程节省了不少的造价。
我们到来之后,就进入了紧张的浇筑桥拱的施工,首先从河南岸的小拱梁开始。工地上,破碎机、混凝土搅拌机、振捣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七八十名民兵,分成三组,一组卖力从河里挑沙到山脚下的混凝土搅拌机旁;第二组卖力用铁桶将混凝土成品顺山路挑到高高的脚手架上,再倾倒在支好的模板仓里;第三组是在搅拌机旁,将水泥、碎石、沙子按比例配好,倒入混凝土搅拌机后面的料斗里,开搅拌机的工人师傅则节制加水量和进料、出料。全体施工过程环环相扣,合营默契,紧张而有秩序。
我被分在第二组,便是挑混凝土。两桶混凝土足有100来斤,只管在屯子已经接管了两年的“再教诲”,但每天七八个小时挑着上百斤的担子往山上爬,而且这天晒雨淋都不能停歇,确实须要一定的体力和毅力。每当感到筋疲力竭的时候,看到其他弟兄们都争先恐后地冒死干,听到广播里播放的激越的革命歌曲,就不由得又振奋起来。
我写的一首七律,真实记录了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景象:
七律﹒大塘桥工地 ——1971年4月16日
战歌洪亮薄重天,工地豪情现面前。
雄峙桥墩临水面,凌空脚架入云端。
机声震耳长空裂,铁担承肩大地颠。
热汗横流何所惧,长虹誓教跨河川。
随着浇筑的拱梁和桥面逐渐向北岸延伸,挑混凝土的间隔也越来越远。那一年的热天又来得特殊早,五月份气温就很高了。我们所有的民兵,从挑第一担混凝土开始,一贯到收工,身上的笠衫就没有干过。有人怕汗液永劫光浸泡衣服,会缩短衣服的寿命,索性脱光上衣,光着膀子干,毕竟那时买一件笠衫要花客岁夜半个月的津贴费呀!
好在连里给每个人发了一顶草帽,多少能遮挡一点暴晒的阳光。这笔经费还是从节余的炊事费中支出的。
五月下旬,桥拱和桥面的浇筑已经到了最紧张的阶段,由于浇筑混凝土必须连续作业,不能中途停顿,因此白天晚上连续、乃至通宵施工也是家常便饭,至于刮风下雨,更是阻挡不了施工的进度。
一天上午,又是浇筑桥拱。开始时艳阳当空,暑热蒸人,快到中午,忽然乌云密布,刮起大风,顷刻间电闪雷鸣、暴雨如注。但是,所有的工人和民兵战士都没有停下手中的事情,而是连续在狂风暴雨中拼搏。此情此景,令人激奋、动容。脑海中当即填词一首以赞:
菩萨蛮﹒雨至——1971年5月26日
雷声滚滚天河裂,光鞭闪闪倾盆即。
风伯卷红旗,霑衣人不离。
民兵钢铁铸,勇令天公怖。
志在贯长龙,肚量胸襟全世红。
6月份,湘东铁路培植指挥部主编的《湘东铁建报》向我约稿,我便填了《满江红》词一首寄去,并做了一些笔墨解释:
满江红﹒工地即景 ——作于1971年6月
浩荡东风,传捷报,动人功绩。
不雅观河边,红旗蔽地,云梯矗立。
壮士劈山开道路,英雄架拱骑墙壁。
树红心壮志力无穷,惊奇迹。
为革命,工期迫。
铺铁轨,桥梁急。
有雄文在握,何知疲竭。
联兴河中流热汗,大塘桥上凝心血。
早通车铁马跃湘东,胡尘灭。
末句中的“胡尘”,古时指北方游牧民族(又称胡人)兵马扬起的沙尘。比喻胡兵的凶焰,这里借喻为当时屯兵百万于边疆的北方强邻。
收工往后,每每已是夕阳西斜,吃过晚饭,大家就到河里沐浴。河水不深,清澈见底,河滩上满是干净洁白的细沙。每到这时,是大家一天中最欢快的时候。我们在河里拍浮、嬉戏,洗干净满是灰尘汗水的衣服,每每要到天快黑才上岸。
最令人难捱的是晚上睡觉。
白天的烈日,将屋顶上的瓦片晒得滚烫,小阁楼又透风不好,活脱脱就像个大蒸笼。纵然入夜往后,阁楼上依然暑热逼人,人要待在上面,就像蒸桑拿一样平常,不要一分钟,就会大汗淋漓,前半夜是根本无法入睡的。那时,别说空调、电扇,乃至连把蒲扇都买不到,就连照明还是用的石油灯。刚开始我们只能湿毛巾不离身,随时用来擦汗,后来,有人发明了“土折扇”,便是用几片竹蔑片,一头用钉子钉成一叠,其余一头伸开呈扇面,然后把结实的水泥袋纸用胶水粘在竹蔑上,就成了一把“土折扇”。有一天,我和几个弟兄偶尔在附近的小卖部里创造有几把草编的扇子,如获珍宝,急速全部买下。
不仅是酷热令人难以入睡,蚊虫也是人们的大敌。屯子的蚊子又多又大,只要让它们叮上,肯定是一个大包,奇痒难忍。没有蚊帐,纵然有蚊帐,阁楼上也不好安装,况且装了蚊帐,将更加闷热。为此,连里买来许多大蚊烟,便是那种用锯末灰掺了农药粉、大拇指粗细、有点儿像小蛇似的老式蚊烟,一个阁楼里放两根。这样虽然避免了蚊虫的袭扰,但凌晨起来,个个却都被熏得头昏脑胀、鼻干唇燥。
前半夜无法入睡,大家索性搬把凳子坐在室外“侃大山”,天南海北地闲聊。一贯聊到下半夜,觉得出发点凉风了,才纷纭爬上阁楼,点燃粗蚊烟,逐步睡去。
一天,在别人侃大山时,我冥思苦想,步南唐后主李煜的词韵,也填了一首《虞美人》词:
虞美人·夏夜难眠
——步李煜原韵戏作之
夜蒸日晒何时了,
挥汗知多少?
小楼今夜又无风,
辗转难眠热在不堪中。
黎明即起豪情在,
未见精神改。
问君何故不言愁,
且看铁龙将至似年夜水。
那时候,县里的电影放映队每隔几个月就来放一场露天电影,每逢这时,周遭好几里的农人都欢天喜地,早早地拿着椅子或板凳,聚在电影场,银幕的前后都挤满了人不雅观看。看电影成了屯子少有的文化生活之一。我们当然也不会放过这难得的机会,特殊是夏天晚上,更是有电影必看。
记得有一天,不知是谁说十几里外的网岭镇上放映电影,我和几十名弟兄,同等决定走路去看电影。大家沿公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天快黑了,离网岭镇只有一两里的时候,遇上返回的几个弟兄,说根本没有电影看,是假的。大家乘兴而去,绝望而归,白白来回走了二三十里路。
回程路上,我又戏作了一首词,记下了这次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
清平乐·步辇儿网岭不雅观影空返 ——1971年7月
佳音相告,影讯揪心闹。
十里路程行带跑,唯恐往不雅观迟到。
惊闻谣传,掉头绝望回还。
漏夜方归驻地,腹中早已饥餐。
一转眼,八一建军节快到了,弟兄们在晚上“侃大山”时提及,既然我们是军事体例的民兵,建军节也该当是我们的节日,过节了,领导也该当有所“表示表示”。这个见地反响上去后,果真有效。7月31号那天早上出工凑集时,连长宣告:“来日诰日是八一建军节,放假安歇一天,改进炊事。”大家一阵欢呼,连长紧接着又说:“还有更好的见告大家,和五公司协商好了,从八月份开始,我们和正式工人一样,每个星期安歇一天。”
这个不啻于久旱逢甘霖,全连弟兄欢呼雀跃,个个春风得意,比过大年还要高兴,干起活来更加起劲了。
第二天是建军44周年纪念日,放假一天。我利用这难得的安歇日,填词一首,纪念这伟大的节日:
念奴娇·纪念建军44周年 ——1971年8月1日
震天鼙鼓,报南昌叛逆,动人。
誓拯公民于水火,大纛井冈矗立。
星火燎原,工农奋起,赤色苏区辟。
踏长征路,思念无数英烈。
力戡日寇凶狂,国度栋梁,光复丰功业。
强敌逆流挑内战,三载灰飞烟灭。
抗美援朝,江山铁固,全球堪无敌。
新功再建,亿民异口同说。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五公司的技能卖力人张工程师,对我们民兵中的知识青年特殊关照。他常常端着一台老式的双镜头120相机,来工地为我们摄影,至今我保留下来的几张老照片,便是张工为我们所摄。他理解到我有写美术字和黑板报的特长,就常常抽调我帮工地上写标语和宣扬栏、黑板报。个中有10块悬挂在大桥上、用旧模板制成的1.5米长、1米宽的大木板,用白底红漆写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10个黑体大字,一里路之外就能瞥见。
在大桥主体快竣工时,张工要我在大桥正中两边的护栏上“刻字”,我愉快地接管了这个任务。工人们浇筑了两块混凝土预制板,趁水泥没有固化时,我用手指在一块预制板上写下了“大塘大桥”四个凹进去的隶书阴文大字,在另一块预制板上用同样方法写下“一九七一年玄月建”八个字。过了十几天,预制板已经完备固化,安装到了护栏上,我又在那些字的凹槽里涂上红油漆,显得非常刺目耀眼、俊秀。这几个字,也算是我留在大塘桥上唯一的纪念物了。
9月中旬,大桥的主体终于建成落成了,后面还有不少附属工程,如砌护坡、未成形的路基等等都须要完成。这时,景象逐渐地风凉下来,劳动强度也相应减轻不少,连队的文体活动也积极开展起来。
连里组建了篮球队,常常在安歇日和兄弟连队进行友情赛。连里的宣扬栏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包打包唱,每一期上都有我写的诗词和文章。连里还成立了文艺宣扬队,排演一些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
图为连里篮球队员在桥上合影
图为作者在大塘桥下留影
1971年10月,我们连移师15公里外的攸县新市,紧张担负路基的护坡修砌和植被绿化事情。告别为之奋战了七个月、傲然特立在联兴河上的大塘桥,我心潮起伏,填词一首,抒发离去之情:
忆秦娥﹒大塘桥竣工移师新市
——1971年10月18日
飞虹架,凌空越水昂霄跨。
昂霄跨,
青山腾舞,红旗如画。
英雄热汗河边洒,
整装重把征途踏。
征途踏,
凯歌声动,松风声飒。
我们在新市干了三个多月,在这期间,铺轨工程也在紧张施工。到了第二年的2月初,攸县至醴陵段的路轨铺设完成,开始试运行,我们民兵的任务也基本完成了。春节前夕,我们坐上试运行的敞篷货车厢,一起向北,到了醴陵,随后乘上专门安排的大巴车,返回了浏阳沙市,结束了一年四个月的三线岁月。
在三线,与许多农人兄弟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情意。他们吃苦刻苦的精神、纯梗直率的性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殊是与几位读过初中和高中的农人弟兄,更是成为了莫逆之交,至今仍有交往。回到浏阳后,一位朋友写信给我,畅叙衷肠,我复书中赠了他一首诗:
七律·答朋侪 ——1972年2月
铁龙北上似离缰,战士扬镳返故乡。
浏北高歌归胜曲,湘东尽谱凯旋章。
一年奋战情深厚,数日分离倍觉长。
梦醒晨曦期唤友,举头但见断缘墙。
三线培植是我毕生难忘的一段人生经历,它不仅熬炼了我的意志和体魄,也是我诗词创作的沃土。我最初学写的格律诗词,都属于抽芽之作,便是出身在这块沃土之上。只管这些诗词中的许多措辞和词汇,刻有上世纪70年代的深深印记,但却真实地反响了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三线培植民兵们火热的战斗生活。已经时隔将近半个世纪的本日,再回看这些诗词,依然是那么影象犹新,依然是那么令人振奋,依然是那么回味无穷。
一晃40多年过去了,怀着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结,今年五一小长假,我偕爱人专程来到攸县大塘桥,思念那一段火热的岁月。故地重游,嫡黄花,原来住的泥坯民房变成了瓷片装饰外墙的俊秀小楼;原来长着稀疏马尾松的荒山秃岭也都林木葳蕤,满目葱翠;原来并不宽的一条沙石公路,现在拓宽成了平整的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的106国道……只有大塘桥,依然傲立在联兴河上。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侵蚀,远了望去,它只管显得有些古朴沧桑,但还是那么雄伟和坚实。
登上大桥,只见大桥的不少护栏已呈残破状。走到桥中间的护栏处,一眼就看到我写的“大塘大桥”和“一九七一年玄月建”几个字依然还在,虽然稍显斑驳,但仍旧依稀可辨,只是红油漆早已脱落,失落去了刚立上去时的风采和亮丽。我在桥上和桥下留了好几张影,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回到家中,浮想联翩,连夜赋诗一首,以作此行纪念:
七律·重游湘东铁建工地 ——2019年5月
半世春秋弹指间,湘东岁月恍如前。
隆冬凛凛寒风卷,盛夏炎酷热浪翻。
筑路劈山平涧壑,架桥筑拱战云端。
青春无悔当年事,永驻心中在忆田。
当年那风起云涌的三线岁月,铸就了我们那一代铁建民兵的意志和精神,湘东铁路上洒满了我们的汗水,承载着我们的奉献和光荣,同时也留下了我的那些抽芽诗作,永生难忘。
作者简介
赵晶 株洲冶炼集团公司高等工程师,株洲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在《纵横》杂志、《株洲日报》、《株洲》、《中国旅游报》、《康健周报》、《科学》、《中国消费者报》等多家报刊揭橥文章,1971年开始诗词创作,格律诗词和当代诗均有涉足,诗歌《献给祖国母亲的歌》、《周总理的办公桌》曾得到株洲市诗歌朗诵会创作一、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