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鬼谷子》、《曾国藩》,早已成为职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而《道德经》、《王阳明心学》也被生理学奉为圭表标准,即便是一向被认为失落去成长环境的传统诗词,也呈现了大批的爱好者和创作者。
从《中华好诗词》、《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的热播,以及叶嘉莹诗词著作的热销,可见我国仍旧有着一大批诗词文化的爱好者。
由各种民间的官方的诗词协会的不断发展,也足见,从上古期间出身的传统诗歌,经历唐风宋雨一贯到如今都在被继续着发扬着。
得奖作品《惊蛰》得益于网络媒体的发展,当代天南海北的诗词爱好者,能够以社交软件、论坛等为平台,互换着对诗词的意见,相互批驳各自创作的诗词,这无疑促进了当代诗词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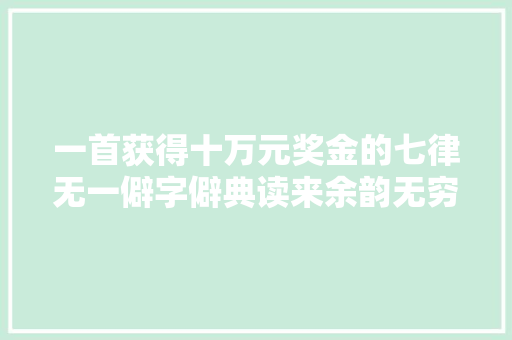
而各种诗词比赛,也发掘了许多令人面前一亮的佳作,比如肖美刚的《惊蛰》:
响雷闻落冷窗多,碍我春眠枕夜过。
梦里蝶胎催裂变,世间蛇足要腾挪。
始从山雨芽尖笋,渐自云根蔓细萝。
总觉江熏风尚好,领先花鸟上青柯。
这首诗是第一届“荣昶杯”诗词大赛的一等奖作品,奖金是10万元。
诗不可译,译之则为译者之诗,诗词之以是美,很大部分缘故原由是声韵以及凝练的诗家语,如果翻译出来,那便失落去了味道。肖美刚这首诗实在并不难解,并无僻字僻典,以是就不逐句翻译了。
很明显,这首七律写的是惊蛰节气。
惊蛰到,春雷乍响,此时阳气上升、温度回暖、雨水增多,万物复苏,大地一片活气盎然。虫儿破茧成蝶,沉睡了一冬的动物也睁开了惺忪的双眼,欢迎新的一年。草木笋藤也在东风下萌芽抽绿,正是农耕的好时节。
末了,墨客说到江南之春,比其他地方的春景更早一步,但只描写了花鸟上青柯的景象,没有详细去描写,余韵无穷。读罢这首诗,便彷佛能感到春天破茧、抽芽那种细微的声音被放大,有种繁盛热闹繁荣的气息,更有很强的画面感。
在读到春天景象的活气、新,这首诗的背后,又彷佛在写社会气候的活气和新,多重含义,令诗作更耐读。
而且这首七律对仗工致,声韵非常和谐,即便是用了古韵,可用本日的普通话读来依旧朗朗上口。这也是“荣昶杯”对参赛作品的一个哀求:既要符合古韵,又要符合今声。
这种理念,既保留了传统诗歌的声韵精髓,又顺应了当今时期的措辞习气,只是创作起来,比古人更难。
诗词创作不应厚古薄今当代的人,每每厚古薄今,总认为古人的诗才是好诗,现在写的诗词,都不值一提。实在这种认知是缺点的,无论是知识的广度,还是深度,今人都具备更有利的条件,没有看详细今人的诗作,就发出这种辞吐,无疑是一种偏见。
许多人还持有一个不雅观点,认为诗词在唐宋就已经被写尽了。如果身处元明清说这种话,或许还有几分道理。由于唐宋元明清只管改朝换代,但生活的环境变革并不大。
而艺术来源于生活,以是很多题材都被唐宋被写了,后世很难写出新意。故而才出身元曲、明清小说,诗词方面,元明清只能在技巧上不断发展。
但如今不同了,这是一个思想昌明、科技发达的社会,神舟奔月、高铁追风,无论是事情还是生活环境,以及思考问题的办法,都和封建期间有着大相径庭。对付事物的认知,今人也是更胜古人,很多事情,是古人无法想到的。
举个大略的例子:
时差,是古代大部分人难以认知到的,更别提以此立意写诗词了。但对付今人来说,却是妇孺皆知的一个知识点,当代墨客彭莫有一句诗:“想得费城时中午,可怜月也不同看。”
这句诗是怀人,望月思怀,在唐宋已经被写烂了,伤感的、凄清的、开阔的、豁达的。对付明清来说,实在写不出新意,但彭莫以时差立意,他在晚上望着玉轮,思念朋友,而身在费城的朋友正处于中午,可怜两个人,连月都不能同看,做不到“千里共婵娟”。
以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古人很难想象出的,他们更无法写尽世间的诗歌,正如钱钟书所说:“诗歌的天下是无边无涯的。”只要时期在发展,诗歌的天下就会不断被扩大。
由于诗本便是歌咏时势,我们的生活,便是诗歌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很多人以为当代没有好诗词,而钟情于古代,是由于,大部分不是喜好诗词的歌咏时事情志的内核,是喜好诗词那种古风古韵的外在,这种想法完备本末倒置。
要想写出符合当代气候的诗词,就该当多关注生活,多把稳社会百态,然后多看当代精良墨客写的诗词作品。而不是沉浸在兰舟、瘦马、古道、蓑衣等虚假的生活中。
而说到当代精良墨客,“荣昶杯”的评委,同时也是新国风诗社的社长赵缺,作品就非常好,他的个人诗集《无咎诗三百》,是他从数千首作品中选录出来的佳构,这也是我的枕边书。
赵缺师长西席虽然没有高学历,但从小喜好阅读古典书本,而且每每能够举一反三,得出自己的思考。同时,他前半生一贯奔波在社会底层,摆过摊,做过推销员,他以自身角度,不雅观照社会的发展变迁,更为深刻动听,想必大家都能从他的诗中,读到自己生活的影子,读到时期的气息。
诗集附录了他总结出的诗词创作心得《彼岸诗话》,相信真正喜好诗词的朋友,能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