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
——————————
张景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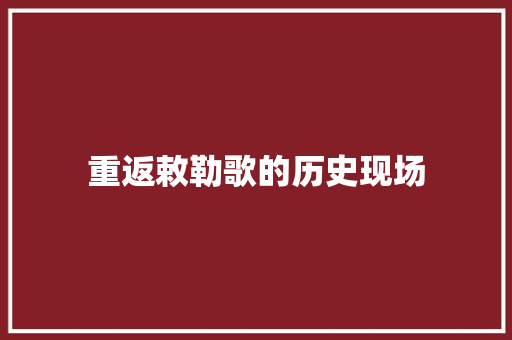
《敕勒歌》很著名。纵然连绵起伏的那拉提与阿勒泰风光无限,但“天苍苍、野茫茫”的开阔如砥,仍是中国人潜意识中对草原的期待;开阔如砥的呼伦贝尔间隔今日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敕勒川1000多公里,在干旱年份的牧草高度仅能与足球场草坪相称,却并不妨碍游人一遍遍重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叹。
诗篇描述的工具去古已远,笔墨却依然稳定传颂。然而在熟稔之外,我们是否已完备理解这首短诗的精彩高妙之处?
共同指向一种苍凉的心境
近1000年以来,《敕勒歌》被视为塞外风景描写的上乘之作,评论家同等赞赏其笔触的简练与朴实。宋代的王灼与近代的王国维尤其推许《敕勒歌》,前者谓西汉后仅此诗与韩愈《琴操十首》能得古意;后者将此诗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道并称为景物描写中“不隔”的典范。
从《碧鸡漫志》到《艺苑卮言》,环绕敕勒歌的经典评论每每会为《敕勒歌》找到一个同时期的比拟物,那便是以宫体诗为代表的南朝文学传统。宫体诗的题材是绮丽的、形式是繁缛的、技巧是繁芜的,其情趣格调不免坠入颓废腐烂,当然须要另一种自然简洁、清新宏阔的例子予以反衬乃至救赎,《敕勒歌》正当其选。遐想到南北朝终极由北方主导完成统一的历史命运,则《敕勒歌》自带的北方属性,无疑可被视为某种统一盛运来临前民族朝气与活力的来源。
虽然文学史的书写给予我们一种基于比较的鉴赏策略与意义授予办法,但笔墨对付心灵的直接冲击力,仍是剖断一个作品代价的最直不雅观依据。坦率地说,当代读者在首次面对《敕勒歌》的文本时,并不太随意马虎感想熏染到某种冲击力的存在。
“网络原住民”在孩提时期就能轻易通过广角镜头与无人机视角欣赏草原之美,他们诵读《敕勒歌》时,由视觉履历建构的“前见”早已形成,最大的阅读体验无非是“原来如此”的契合感。
不过,古人的阅读体验彷佛与当代读者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敕勒歌》有着并不平淡的感情色彩。元好问激赏其“年夜方”有“英雄气”,王夫之感叹“不知凄凉之何以生”,陈廷焯夸奖“苍茫凄凉、千古绝调”。梁启超虽然承认这首诗在字面意思上只是“独自一个人骑匹马在万里平沙中所瞥见的宇宙,他并没说出有什么感想”,却坚持个中隐然浮现着“粗豪沉郁的人格”。
古人的体验虽有所不同,但感想熏染并非轻松愉快,其共同指向乃是一种苍凉的心境。
《敕勒歌》与玉壁败北后的高欢
最早提及《敕勒歌》的文籍,是成书于唐初的《北史》与《北齐书》,二书都位列后世所谓“正史”之中。公元546年深秋,东魏政权的实际掌握者高欢,率大军进攻西魏政权在汾水下贱的主要军事据点玉壁城(今山西稷山县境内)。玉壁城守军不过数千,但阵势险要、准备充分,加之守城的西魏名将韦孝宽治军有方、战术利用得当,高欢强攻数月不克,士气低落。加之入冬后景象寒冷、疾疫盛行,东魏士卒去世亡7万人,高欢被迫撤军。
途中,军中盛传高欢已被仇敌射杀,民气惶恐。高欢为防止溃败,不顾身已染疾,强打精神调集心腹宴饮,席间命大将斛律金歌唱《敕勒歌》。斛律金不识字,却很有口头文学的创作才能。伴随着斛律金的歌声,高欢击节跟唱,不禁潸然泪下,军心遂安。不久,52岁的高欢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忧愤而终,这位浊世枭雄终极未能实现统一北方的夙愿。
《北史》与《北齐书》纂成的时期,间隔玉壁之战仅有百年,干系记载基本同等,个中仅提到《敕勒歌》之名而未涌现全文。又400年后,《敕勒歌》全文被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收录,其时已是宋代。从此开始,《敕勒歌》究竟是斛律金即兴原创,抑或只是经其翻唱的北地民歌,评论者一贯争议不休。
将《敕勒歌》与干系历史事宜密切结合,显然是近代以前一以贯之的诠释路径。可见古人关于《敕勒歌》“年夜方凄凉”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来自文本,不如提及源于玉壁败北后高欢英雄末路、壮志未酬的移情。正如清人袁枚所云,“唱罢阴山《敕勒歌》,英雄涕泪老来多”。到了近代,文学研究者才将《敕勒歌》与作为伴随文本的《北史》《北齐书》剥离,终于使其作为一首记叙塞外风光的“北朝民歌”写入教材。
本日,如果读者不知足于欣赏风景的白描,重返《敕勒歌》的历史现场仍是必由之路;但大略重复古人感慨,同样未慊襟怀。从文本出发,有两个贴近的问题须要办理:高欢在惨败之际,命斛律金吟唱一首描写塞北风光的歌曲,究竟出于何种考虑?为何它可以重新凝聚败北之师的民气?
迢遥的故乡之景,引发的不是“乡愁”
对付高欢、斛律金及其将士而言,《敕勒歌》固然是写景,但所写并非面前之景,而是迢遥的故乡之景。敕勒川,大致位于今内蒙古中部的河套-土默特平原。拓跋鲜卑很早即以敕勒川为根据地,在建立北魏并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在包括敕勒川在内的北境设置6个军镇防备柔然。
六镇居民,多为世代从军的职业军人或对朝廷有服役之责的游牧部落。高欢属于前者、斛律金属于后者,高欢集团的骨干人物与紧张兵员都来自这一区域。中古时期,六镇区域多为草原牧场,间有零散的粗放农业,景不雅观一如《敕勒歌》所述,这是高欢集团将士们的少年影象。
而作为高欢平生末了沙场的玉壁城,景不雅观则与之迥不相侔。玉壁城坐落于黄土高原,位于汾河河谷与丘陵的过渡地带,阵势波折险要,多数地皮很早就被开辟成农田,植物群落中人工栽培作物霸占紧张地位。寒冬中,收成过的野外一片萧瑟肃杀,袒露的耕地上阡陌纵横,处处显示塞外人群所不熟习的空间秩序。
高欢集团于此遭遇惨败,周围环境不仅陌生,更显严厉。此时,斛律金的《敕勒歌》垂垂伸展出夏季草原的宏阔安详,唤醒六镇子弟灵魂深处的故乡影象,如同一种镇静剂,给予经历苦战、麻木恍惚的将士们以短暂的安宁。
然而,《敕勒歌》中的俏丽草原,却是高欢、斛律金回不去的故乡。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六镇军民地位与生活水平迅速低落,终极酿成摧毁北魏王朝的大叛逆,是为“六镇之乱”。高欢、斛律金以及这一集团的骨干,都崛起于“六镇之乱”。草原是他们的出发地,在从边缘人物、被压迫者到征服者的转变中,这群六镇子弟从未停下脚步。颠沛流离、浴血奋战,任何一次失落败都可能万劫不复,这样丰富而紧张的人生,大抵是没有闲情逸致怀念乡土的。
虽然高欢本人生活俭朴,但高氏统治集团的上层以奢靡纵欲而著称。这群人终极止步于玉壁城下,猝然创造自己已从意气少年变为迟暮老者,而且意气摧折、身陷险地。伴随着《敕勒歌》的歌词旋律,陷于绝望中的征服者,终于能停下脚步转头一望,自己出发的草原已是如此遥不可及,其间相隔的不仅是重重关山,更是一幕幕辗转杀伐的峥嵘岁月。这回望所引发的,绝对不是后世熟习的“乡愁”,而是历尽平生后的无限惆怅,使得败军之将老泪纵横,同时也使他们猛然惊醒:手中的权柄、光彩乃至江山,究竟从何而来,该当若何去掩护?
玉壁城陨落了高欢,却未成为这群六镇子弟的宅兆。他们丢失惨重,但核心力量终极全身而退,并在历史舞台上连续生动30年。
在晋室南渡后的200多年中,北方民歌总是与战役相联系,歌颂孤胆英雄的《陈安歌》、赞赏传奇女子的《木兰辞》,都是如此。与之比较,《敕勒歌》的笔墨最为沉着从容、最没有兵戈之气,其战役背景却最为详细惨烈。
塞外草原的俏丽风景与中原沙场上的苍凉心境,在《敕勒歌》中通过歌咏者交织回顾的怅望姿态,实现了繁芜弯曲的交融,这或许正是《敕勒歌》成为经典的一重深层缘故原由。或容许以认为,历史情绪的景不雅观根本与历史景不雅观的情绪表达,应该是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之一。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