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背景的力量。本来,衡量一个人的代价,只应纯粹地皮算这个人到底如何,是不应把背景也打算在内的。然而,倘若这个人果真是有所谓背景的话,那么在打算时,却会一定要加上背景的——背景越深邃、伟大,和也就越大。人值几个钱,便是几个钱,应是一个常数。但我们在这里正好看到的是一个变数——一个量大无穷的变数。
当我去镇静地剖析自己时,我创造,我原也是一个“有背景”的人。
我的背景是北大。
这是一个大背景,一个险些大得无边的背景。现在,我站在了这个彷佛无声但却绝对生动有力的大背景下。本来,我是微小的,微小如一粒恒河之沙,但却因有这个背景的衬托,从而使我变得彷佛也有了点光彩。背景居然成了我的一笔无形资产,使我感到了富有。其环境犹如融入浩浩大海的涓涓细流,它成了大海的一部分,仿佛也以为有了海的雄浑与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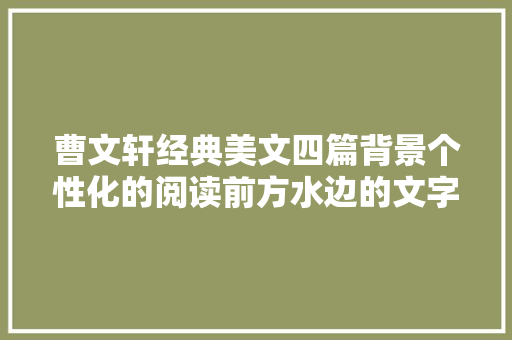
我常去揣摩我与北大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我将如何?此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个背景参与了我的身份的确定。我为我能有这点自知之明而感到一种良心上的安宁。我同时也想到了我的同仁们。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里,确实干得非常出色,个中一些人,切实其实可以说已东风浩荡、锐不可挡。大概我不该像发问我自己一样去发问他们:如果没有北大这个背景,他们又将如何?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去发问自己的——北大门里或是从北大门里走出的人,都还是长于省察自己的。我相信这一点。
北大于我们来说,它的恩典膏泽既表现为它曾经给了我们知识,给了我们人品,给了我们前行的方向,又表现为它始终作为一道背景,永久地矗立在我们身后的苍茫之中。由于有了它,我们不再感到自己没有“来头”,不再感到那种身后没有樊篱的虚弱与惶恐。
就在我于心中玩味“背景”这一单词时,总有一些详细的事情与场面繁忙地穿插于其间——
那年四月,我应邀去东京大学讲学。在日本的十八个月中,我时时刻刻都能感想熏染到这个背景的存在。那天晚上,在东大教养学部举行的欢迎外国人西席的酒会上,我代表外国人西席讲话时,在一片掌声中,我感想熏染到了。在我为我的小孩办理临时入学手续时,我感想熏染到了。在我于北海道的边陲小城受到一位有时相识的日本朋友的激情亲切接待时,我又感想熏染到了。……十八个月结束后,东大教养学部的师生们破天荒地为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送晚会。在那个晚会上,“北大”这个字眼涌现了数次。我心里明白,这个晚会的隆重与热烈,固然与我十八月的负责事情有关,但最根本的缘故原由还是在于我背后有这个背景。
无论是在学术会议上,或是应邀到外校讲学、演讲,险些是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场合,我都能感想熏染到这个背景。它给了我自傲与勇气。它默默地为我增加着言语的重量,并且神奇般地使我精力焕发。
它乃至免去了我的尴尬与困境。
大约是在五年前,那天上午,我将一本书写完了,心情甚好,就骑了一辆车,一起南行,到了紫竹院一带。已是中午,我感到饿了,就进了一家饭铺。那天胃口真是好极了,独自坐下后,竟要了好几个菜,还要了酒,摆出了一副要大吃大喝的样子。阳春三月,景象已经非常暖和,加之我吃喝得高兴淋漓,额头上竟沁出不少汗来,身与心皆感到莫大的痛快酣畅。吃罢,我不急着走,竟坐在那儿,望着窗外路边已笼了绿烟的柳树,做一顿好饭菜之后的遐思。“今天真是不错!
”我在心里说了一声,终于起身去买单。当我把手伸入口袋去掏钱包时,我顿时跌入了尴尬:出门时忘了带钱包了。我的双手急忙地在身上征采着,企图找出钱来,不想本日也太难为我了,浑身高下,里里外外,大小口袋不下十个,却竟然摸不出一分钱来。身上立即出来大汗。我走到收款台,正巧老板也在那里,我吞吐其辞、颠三倒四地说了我没有带钱的情形。老板与小姐听罢,用迷惑的目光望着我。那时,我不才意识中立即想到了一点:本日也只有北大能救我了。未等他们问我是哪儿的,我便脱口而出:“我是北大的。”老板与小姐既是从我的眼睛里看出了我的老实,更是他们听到了“北大”这个字眼,随即换了另样的神色。老板说:“师长西席,没有关系的,你只管走便是了。”我想押下一件什么东西,立即遭到了老板的阻挡:“师长西席,别这样。”他在将我送出门外时,说了一句我们这个时期已经很难再听到的彷佛属于上一个世纪的话:“师长西席,你是有身份的人。”
一起上,我就在想:谁给了我“身份”?北大。
这个背景也可以说成是人墙。它是由蔡元培、马寅初、陈独秀、胡适之、鲁迅、徐志摩、顾颉刚、熊十力、汤用彤、冯友兰、朱光潜、冯至、曹靖华等无数学博功深的人组成。这是一道永久值得仰望与审美的大墙。
我想,这个背景之以是浑沉有力,一是由于它历史悠久,二是由于它气度恢宏。它是由漫长的历史积淀而成的。历史一点一点地巩固着它,发展着它,韶光神秘地给它增长着风采。而蔡元培师长西席当年对它所作的“大学者,席卷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定义,使它后来一贯保持着“取精用宏,不名一家”的非凡学术气度,担保了这个背景的活力、强度与无限延伸的可能性。
话说到此时,我要说到另一种心态了:对背景的回避。
这个背景一方面给了我们各类好处,但同时也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生理压力。我们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生存着,无时无刻不感到有一根无形的鞭子悬在头上。它的高大,在无形之中为我们设下了险些使我们难以接管的攀登高度。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良久以前,我就有一种觉得:当我一脚踏进这个校园时,我就仿佛被扔到了无底的漩流之中,我必须聚精会神,奋力拼搏,不然就会葬身涡底,要不就会被浪头打到浅滩。
我们都在心中默念着:回报、回报……。一代一代曾得到过北大恩典膏泽的北大人,都曾默念着它而展开了他们的人生与学术生涯。
这个背景的力量之大,居然能够使你不敢仅仅是利用它、享受它,还能提醒与鞭策你不能辜负于它。这就形成了一个难度:一代又一代人设下一道又一道台阶,使后来人的攀登愈来愈感到吃力。有些时候,我们就有可能生出遮盖“北大”身份的动机——“北大”这个字眼并不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乐意提及的。背景既给予了我们,又在哀求着我们。背景给了我们方便,给了我们名誉,但又被别人拿了去,成了衡量我们的难免不免有点苛刻的尺度。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说:没有我们就没有他们,是我们创造了先驱。先人们的光彩与辉煌,是后人们创造的。若没有后人们的创造、阐释、有力的弘扬与巨大的扩展,先人们的光彩大概就会黯淡,他们就有可能永久默默无闻地沉睡在历史的荒漠之中。任何得其盛誉的先人,都应由衷地感谢勤奋不倦的后人。没有现在的我们,这背景也就不复存在;背景衬托了我们,但背景却又正是通过我们才得以反响的。
然而,这个角度究竟不能使我们得到彻底的安心与解脱。我们还得在宛然可见的先人们的目光下向前、向前、无休止地向前。
背景是一座山,大山。
我们任何个人都无权骄傲,有权骄傲的永久只能是北大。
奋斗不息的我们,终极也有可能在薄暮时变享受背景为融入背景而终止自己。这大概是我们都期盼着的一份幸福而悲壮的景不雅观。
1998年3月3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个性化的阅读世间有许多读书种子,但他们的读书彷佛与他们的精神无补,反而读成呆子,读成迂腐可笑之人。曹聚仁师长西席说他曾听说过浙江金华有个姓郭的,书读到能将《资治通鉴》背诵一番的程度,但写一个借伞的便条,却写得让人不堪卒读(那便条写了五千余字)。读书多,莫过于清朝的朴学家,然而,像章太炎那样令人钦佩的朴学大师又有几个?我认得一位教授师长西席,只要提起他来,人们第一句话便是:此人读书很多。然而,他的文章我才不要看。那文章只是别人辞吐的联缀与拼接,读来实在以为没故意思。读书不是装书。读书用脑筋,装书用箱子。脑筋给了读书人,是让读书人读书时能举一反三,能很强健地去扩大知识的。箱子便只能如数装书。有些人读一辈子书,读到终了,不过是只书箱子而已。
从前有不少人琢磨过如何读书。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有段笔墨:“袁文清公桷,为湘江世族,受业王深甯之门,尝云:‘予少年时读书有五失落:泛不雅观而无所择,其失落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缩不敢望,其失落儒而无立;纂录故实,一未终而屡更端,其失落劳而无功;闻人之长,将疾趋而从之,辄出其后,其失落欲速而好高;喜学为文,未能蓄其本,其失落又甚焉者也。’”袁氏之言,我虽不敢全部苟同,但大都说在了读书失落当的症结之处。而个中“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缩不敢望”,我以为是读书的大忌。
更有甚者,还有读书把人读糟了读坏了的。周作人当年讲:“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抽去这句话当时的详细所指,抽象一点说,这句话倒也说得通:中国的事坏在一些读书人手里的还少吗?
我是一个常常编书的人,是一个要常常向别人开写书单也要常常向别人索取书单的人。读了几十年的书,做了几十年的书的筛选,我对我阅读视野之开阔,对书之好赖的判断、选择,都已经比较自傲。那年,我给一家出版社编一套北大清华的状元丛书,看了那些状元的一份份阅读书目之后,我就更看清了读书与个性之间的关系。我不得不佩服他们在这个年纪上就能开出这样的书单。这是一份份高质量的富有见地的书单。能开出这样的书单,绝非易事。不将书读到一定的份上,没有一定的鉴赏力,是断然开不出这样的书单来的。一个好的中医,其水平的高低,末了就全显示在他所开的一纸药方上。一些有名的药方,会令业行家家惊诧,但随即它的绝妙就会使人叹为不雅观止。而一个好的读书人,其水平终极是显示在他的一纸书单上。他们在这样一个年纪上就能淘出这样的书来,真是很不大略。这来自于他们阅读范围的广大和阅读的细心与深入,也来自于他们对书的一种体悟能力、直觉能力和对书的一份不可言说的默契。
书海无涯,他们是淘书人。而在淘书过程中,他们显示出了十足的个性,或者说,他们在阅读方面一贯在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个性。我创造了一个十分主要的话题:个性在阅读中的意义。
个性是阅读的关键,是阅读是否能够得到最大利益的根本。以前,我们只谈阅读,不谈如何阅读——纵然谈如何阅读,也很少会有人把稳到个性在阅读过程中的那份举足轻重的意义。
很多人都在读书,但未必谁都能将书读好。而书读不好的缘故原由之一是这个人的书读得全然没有个性。许多年前,我曾在北大的教室上说:读书也有一个谢绝媚俗的问题。除了一些大家都该当读的基本书之外,一个人读书应有自己的选择。做人忌讳雷同——一个人若无个性,一定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家伙,做文忌讳雷同——文章写得似曾相识,这篇文章也就失落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读书也忌讳雷同——读书一雷同,也就什么都雷同了。因此,聪明人读书,会独辟路子、另谋生路。一个人说:我不读别人读的书,只读别人不读的书。此说大概是年夜言,大概是极度,但这份决议确定也有可取之处,这便是那一份在读书方面顽强地展示个性的意识。到别人不常进入的领域去淘别人不淘的书,就会得到别人得不到的知识,就会发出另样的声音。这个道理大略得犹如走别人未曾走的路,就会创造别人创造不了的风景一样平常。
选书选得很有个性,而读法与理解也极有个性。同样的一篇文章,在他们眼里,却有另一番天地,另一番气候,另一番精神。不在乎别人对那篇文章的唠叨,乃至不在乎专家威信对那篇文章的断评,而是按自己的心思去读,按自己的直觉去读,乃至按自己的奇思怪想去读,读得津津有味,读得出神入化。
书海浩淼,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人面对那么多的书,他要有充分的自主意识、驾驭意识。知识欺人,比世上任何恶人欺人还甚,一个没有自主意识的人,知识早晚会将他沦为它的奴隶。而无驾驭意识,知识只是一堆一无用途的石头,它既不能助你提高,也不能使你增加财富。知识只有在那些有自主意识、驾驭意识的读书人那里,才可亲可爱,才具有美感,才具有使人升华的力量。只有那样的读书人,也才会有畅游知识海洋的莫大快感。
我在想,一个好的读书人,读到末了会有那样一个境界:知识犹如漫山遍野的石头,他来了,只轻轻一挥鞭子,那些石头便忽然地受到了点化,变成了充满活力的洁白的羊群,在天空下欢畅地奔驰起来。
前方他们去哪儿?归家还是远行?然而不管是归家还是远行,都基于同一事实:他们正在路上。归家,解释他们在此之前,曾有离家之举。而远行,则是离家而去。
人有克制不住的离家的希望。
当人类还未有家的意识与家的形式之前,先人们是在险些无休止的迁徙中生活的。本日,我们在电视上,总是瞥见美洲荒原或者非洲荒原上的动物大迁徙的伟大场面:它们一直地奔跑着,翻过一道道山,穿过一片片戈壁滩,游过一条条河流,其间,时时遭到猛兽的打击与追捕,或摔去世于山崖、淹去世于激流。然而,任何阻拦与艰险,也不能阻挡这声势浩大、撼动人心的迁徙。前方在召唤着它们,它们只有奋蹄挺进。实在,人类的先人也在这迁徙中度过了漫长的光阴。
后来,人类有了家。然而,先前的习气与希望依然没有寂灭。人还得离家,乃至是远行。
表面有一个广大无边的天下。这个天下充满艰辛,充满危险,然而又丰富多彩,富有刺激性。表面的天下能够开阔视野,能够壮大和发展自己。它总在诱惑着人走出家门。人会在闯荡天下之中得到生命的快感或知足按捺不住的虚荣心。因此,人的内心总在叫嚣:走啊走!
离家大概是出自无奈。家容不得他了,或是他容不得家了。他的心或身抑或是心和身一起受着家的压迫。他必须走,远走高飞。因此,人类自有历史,便留下了无数逃离家园,结伴上路,一起风尘,一起劳累,一起干瘪的故事。
人的眼中、心里,总有一个前方。前方的情景并不明确,朦胧如雾中之月,闪烁如水中之屑。这种不愿定性,反而助长了人们对前方的抱负。前方使他们愉快,使他们行动,使他们陷入如痴如醉的状态。他们仿佛从苍茫的前方,听到了呼唤他们前往的钟声和激动民气的鼓乐。他们不知疲倦地走着。
因此,这天下上就有了路。为了快速地走向前方和能走向更远的地方,就有了船,有了马车,有了我们面前这辆破旧而简陋的汽车。
路连接着家与前方。人们借着路,向前流浪。自古以来,人类就喜好流浪。当然也可以说,人类不得不流浪。流浪不仅是出于天性,也出于命运。是命运把人抛到了路上——形而上一点说。由于,即便是许多人终生未出家门,或未远出家门,但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仍旧有无家可归的觉得,他们也在漫无尽头的路上。四野茫茫,八面空空,面前与心中,只剩下一条通往前方的路。
人们早已创造,人生本色上是一场苦旅。坐在这辆车里的人们,将在这样一辆拥挤不堪的车里,开始他们的旅途。我们可以想象:车吼叫着,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颠簸,把一车人摇得东歪西倒,使人一起受着皮肉之苦。那位男子手托下巴,望着车窗外,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个将要开始困难旅程的人所有的惶惑与茫然。钱钟书师长西席的《围城》中也涌现过这种拥挤的汽车。丰子恺师长西席有篇散文,也是专写这种老掉牙的汽车的。他的那辆汽车在荒郊野外的半路上抛锚了,并且总是不能修睦。他把旅途的不安、无奈与焦躁不宁、枯燥乏味细细地写了出来:真是一番苦旅。当然,在这天底下,在同一韶光里,有许多人大概是坐在豪华的游艇上、舒适的飞机或火车上进行他们的旅行的。他们的心情就一定要比在这种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中的人们要好些吗?如果我们把这种具象化的旅行,抽象化为人生的旅途,我们不分彼此,都是苦旅者。
人的悲剧性本色,还不完备在于总想到达目的地却总不能到达目的地,而在于走向前方、到处流浪时,又时时刻刻地想念着正在远去和久已不见的家、家园和家乡。就如同一首歌唱到的那样:回家的心思,总在心头。中国古代诗歌,有许多篇幅是交给思乡之情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古诗十九首》)“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卢纶)“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未老莫回籍,回籍须断肠。”(韦庄)……悲剧的不可避免在于:人无法还家;更在于:即便是还了家,依然还在无家的觉得之中。那位崔颢,本可以凑足盘缠回家一趟,用不着那样伤感。然而,他深深地知道,他在心中惦记的那个家,只是由家的温馨与安宁养育起来的一种抽象的觉得罢了。那个可遮风避雨的实在的家,并不能从心灵深处抹去他无家可归的觉得。他只能望着江上烟波,在心中体味一派苍凉。
这坐在车上的人们,前方到底是家还是无边的旷野呢?
水边的笔墨屋小时候在野外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忙劳碌碌的,很像一个人家真的盖屋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小工。一边盖,一边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个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等家什。谁谁谁睡在哪张床上,谁谁谁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一直地说着。有时好商量,有时还会发生争执,最严重的是,可能有一个霸道的孩子由于自己的欲望没有得到知足,恼了,溘然地一脚踩烂了立时就要竣工了的屋子。每逢这样的情形,其他孩子大概不理那个孩子了,还骂他几句很难听的,大概还会有一场激烈的打斗,直打得鼻青脸肿哇哇地哭。无论哪一方,都以为事情很重大,仿佛那真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屋子。无论是希望屋子好好地保留在树下的,还是肆意要摧毁屋子的,完备把这件事算作了大事。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屋子盖起来了,大家在嘴里发出噼里啪啦一阵响,表示这是在放炮竹。然后,就坐在或跪在小屋前,悄悄地看着它。终于要拜别了,孩子们会走几步就转头看一眼,很依依不舍的样子。回到家,还会时时地惦记着它,有时就有一个孩子在过了一阵子韶光后,又跑回来看看,仿佛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到表面的天下去流浪了一些时候,现在又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屋子、他的家的面前。
我更喜好独自一人盖屋子。
那时,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泥瓦工、木匠和听使唤的小工。我对我发布命令:“搬砖去!
”于是,我答应了一声:“哎!
”就搬砖去——哪里有什么砖,只是虚拟的一个空空的动作。很逼真,还咧着嘴,仿佛是一大摞砖头,去世沉去世沉的。很劳碌。一边劳碌一边不住地在嘴里说着:“这里是门!
”“窗子要开得大大的!
”“这个房间是爸爸妈妈的,这个呢——小的,不,大的,是我的!
我要睡一个大大的房间!
窗子表面是一条大河!
”……那时的野外上,大概就我一个人。那时,大概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大概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稻子。我很投入,很专注,除了这屋子,就什么也觉得不到了。那时,大概太阳正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大概都快落进西方大水尽头的芦苇丛中了——它很大很大,比挂在天空中心的太阳大好几遍。终于,那屋子落成了。那时,大概有一只野鸭的军队从天空飞过,大概,天空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便是一派纯粹的蓝。我盘腿坐在我的屋子跟前,悄悄地看着它。那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它,这种欣赏与米爽朗基罗完成教堂顶上的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实在并无两样。可惜的是,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受雇于别人而作画的人,每完成一件作品,总会悄悄地在他的作品的一个不太会引起别人把稳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早知道这一点,我也会在我的屋子的墙上写上我的名字的。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此后,持续许多天,我都会不住地惦记着的我的屋子,我的作品。我会常常去看它。说来也奇怪,那屋子是建在一条田埂上的,那田埂上会有去田间劳作的人时时地走过,但那屋子,却总是好好的还在那里,看来,所有见到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直到一天夜里或是一个下午,一场滂湃年夜雨将它冲刷得了无痕迹。
再后来就有了一种玩具——积木。
那时,除了积木,彷佛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玩具了。一度期间,我对积木非常着迷——更准确地说,依然是对建屋子着迷。我用这些大大小小、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建了一座又一座屋子。与在野外上用泥巴、树枝和野草盖屋子不同的是,我可以一直地盖,一直地推倒再盖——盖一座不一样的屋子。我很惊异,便是那么多的木块,却居然能盖出那么多不一样的屋子来。除了按图纸上的样式盖,我还会别出心裁地利用这些木块的灵巧性,盖出一座又一座图纸上并没有的屋子来。总有罢手的时候,那时,必定有一座我心中空想的屋子矗立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座屋子,是谁也不能动的,只可以欣赏。它会持续好几天矗立在那里,就像现在看到的一座经典性的建筑。直到一只母鸡或是一只猫跳上桌子毁掉了它。
屋子,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会有的意象,由于那是人类先人遗存下的意象。这便是为什么第一堂美术课每每总是老师先在黑板上画上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再用几条长是非短的、横着的竖着的直线画一座屋子的缘故原由。
屋子便是家。
屋子是人类最古老的影象。
屋子的涌现,是跟人类对家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家便是庇护,便是温暖,便是灵魂的安置之地,便是生命延续的根本情由。实在,天下上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和家有关的。幸福、苦难、谢绝、祈求、拼搏、隐退、捐躯、逃逸、战役与和平,所有这统统,都与家有关。成千上万的人呼啸而过,杀声震天,血沃疆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家是神圣不可陵犯的。这就像高高的槐树顶上的一个鸟窝不可陵犯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情景:一只喜鹊窝被人捅掉在了地上,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喊,一只只都显出不顾统统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溘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荡。
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当我终年夜之后,儿时的建屋希望却并没有消退——不仅没有消退,随着年事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而变本加厉。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笔墨。
笔墨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楚,我都须要笔墨。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笔墨永久是我无法离开的。特殊是当我在这个天下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须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虽有时切实其实便是铩羽而归,但毕竟我有可归的地方——笔墨屋。而此时,我会创造,那个由钢筋水泥筑成的家,实在只能办理我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办理我全部的问题。
多少年过去了,写了不少笔墨,出了不少书,实在都是在建屋。这屋既是给我自己建的,也是——如果别人不介意、不嫌弃的话,也尽可以当成你自己的屋子。
我想,其他作家之以是亲近笔墨,和我对笔墨的理解大概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在水边终年夜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