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方向于动态人生,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历史从来便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声称特殊喜好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期。
毛泽东书写了中国的近代史,他生平翻遍了中国的史籍,他也最有资格评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1964年他写下了一首流传不广的词《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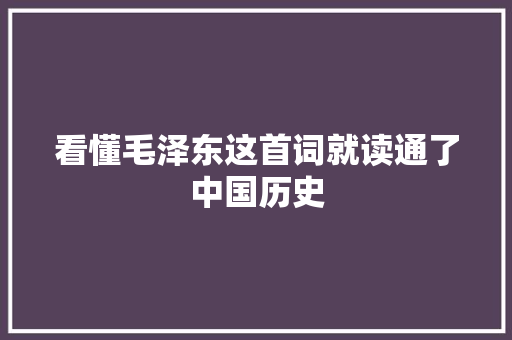
不过几千寒热。
人间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骚人物?
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说实话这首词对历史有一种哲学意义上的闭幕,要想真正明白这首词,你须要从《三国演义》开始,《三侠五义》《说唐》也不能空过,从启蒙到研究,然后到经史子集都要阅读,皓首穷经之后,你就有可能看懂了,看完后什么觉得呢?便是不雅观止矣,不雅观止矣。
什么意思?便是你看不懂,就解释你的历史白学了,须要连续学;看懂了,你会创造你的历史也是白学了,历史便是这首词里写的这么多。
这是老年毛泽东的总结,早知道有这样的结论摆在那里,为什么还去翻那故纸堆呢?这便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哲学意义上的闭幕,历史在历史的书写者面前是大略的。
有智者认为,读书不下秦汉,显然这一点在毛泽东这里也能得到印证。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生动的期间便是在春秋战国期间,当时人才辈出,后人以百家争鸣来形容当时的盛况。
毛泽东曾经神往过社会“大同”境界。世界大同在一些人眼里是假象,是青春期的幻象,但对付其余一些人来讲,它却可能是空想,虽然很难,但值得崇奉和追求。而追求和履行这一空想就使得毛泽东向着人类的顶峰攀登,那至高的峰顶上刻着“平等”两个字。
可以说毛泽东一贯在探求大的本原,本原到底有没有,能找到吗?本原会不会便是一种否定的过程,可能就像老话传说那样,早就在你耳边响起过,但你可能不理会,总以为不会是那样大略,但某一天你会溘然间说找到了,当你将这一真理见告其他人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惊异地看着你,说难道这么大略的道理你刚刚知道?由于你找到的真理便是大实话,真理的分量不是那句话,而是那探求过程中的沉甸甸的否定。
毛泽东在随后的不断失落败中,不断考试测验新的道路。在成为领袖往后,毛泽东也常强调要长于捉住办法,捉住紧张抵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而在当时,贰心目中的“本原”或“大今年夜原”,很有些像老子的“道”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总之是宇宙天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则,终极他实践的成果便是创造哲人们表述的只是笔墨幻象。他当时把“本原”普通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认为它是支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
他表示,目前和将来一段韶光里,自己“只将全副工夫,向大今年夜原处磋商,磋商既得,自然足以阐明统统”。他随后的成功表明本原不是一个名词,或一个观点,一句话,而是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
(原题《毛泽东的精神力量》,摘选自《为什么是毛泽东》一书,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任志刚
编辑:许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