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克修简介】墨客。1971年生于湖南隆回,1995年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系。获过《星星》《诗歌月刊》“2003·中国年度诗歌奖”“1986年--2006年中国当代十大新锐墨客” 、《十月》杂志社“2013十月诗歌奖”、撒娇诗院“民间年夜师奖”。著有诗集《三重奏》。2003年创办并主编《来日诰日》诗刊。2013年发起“地方主义”诗歌运动,并开始《万国城》系列诗篇。现居长沙。
对你们的宝贝古诗说几句
谭克修丨文
大众对新诗有多大的误解都不奇怪,但季羡林、陈图画、叶扬这种级别的学者,和韩寒这样的80后文化符号人物,也对新诗的误会如此之深,完备损失判断力,有点奇怪。说他们不频年夜众更有眼力和见识,难以相信,但他们表现出对当代新诗的唾弃时,还如此理直气壮,就更奇怪了。在新诗已有百年历史,成绩不小于小说的环境下,身份的合法性问题,居然还是新诗的最大问题。诗坛内部的人在奢谈新诗百年造诣,诗歌外部的人,却对新诗完备不承认。看来,对多数人,包括所谓的学者阶层来说,关于新诗,连基本的扫盲事情都还没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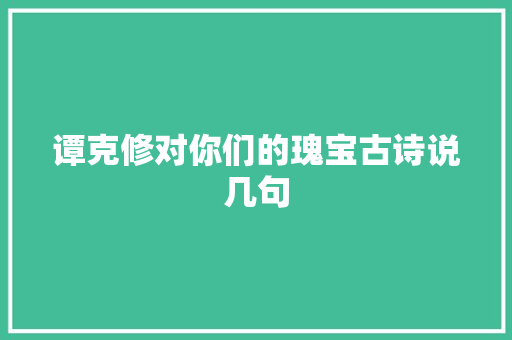
要对新诗进行扫盲,是很辛劳的事情。对你们的心肝宝贝——古诗谈几句意见,要省事得多。古诗的法宝,是格律。在古诗里,大家用同样的格律写诗,相称于当前的克隆技能。在严苛的格律技能之下,诗歌在形式上的新的可能性完备被抹杀了,诗的内容成了核心标志物,唯一的差异部件。在那迢遥的冷兵器时期,诗的内容也是有限的,天下和人性没这么繁芜,墨客日常接管的信息量少而且大略,写诗题材无非便是怀古咏物,山水田园,战役行旅,送别闺怨之类。以是,同样题材的诗会涌现各种陈词谰言,大量墨客只好为赋新诗强说愁。
李白杜甫要杀出重围,不被陈词谰言淹没,发出自己的声音,确实可用伟大来形容。后来者难以超越李杜,不是后来者里再没有诗歌天才,一个比一个蠢,而是那种木乃伊一样的形式,吸干了一代又一代墨客的鲜血。当寥寥可数的几座大山,被陶潜李白杜甫李商隐们各自占山为王,后来者不想当几大天王的粉丝,只能默默地绕道而行。像贾岛那样,须要“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而想一鸣惊人的苦吟墨客,不计其数,但再难以得到贾岛这样的诗歌名声。在古诗那种强大格律形式的桎梏下,墨客自己的声音,按理说是最主要的声音,不过充当极细微的背景音乐而已。他们真实的嗓音、腔调,根本穿不透高音喇叭里的统一格律声。现在看来,在唐宋往后,不能在形式上得到解放的汉语诗歌,走向彻底衰亡已是一定命运。只是白瞎了元明清一代又一代墨客的才华,都耗在古诗词格律里做填字游戏。
后来者,已经无人能复活古诗词那具形式的木乃伊。献祭给它再多的童男童女也没用。1917年,胡适揭橥《新文学刍议》和他的8首口语诗,正式发布了作为这个国度最值得骄傲的文学形式——古体诗,带着它曾经的辉煌,和已经瘫痪数百年的病躯,黯然离世。也发布了一个属于新诗的时期的到来。有人可能会往后来的古体墨客毛泽东来回嘴这一事实。毛的诗词,可当一个特例。毛诗声音之洪亮,部分来自于其异于凡人的声带和肺活量,部分来自于传播,才使毛诗在气势上凌驾于技能之上,先声夺人,能在那种用烂了的古诗词形式里,保存他自己的腔调。但那只能说是古体诗一次极其意外的回光返照而已,无法让古体诗去世而复活。对毛泽东诗词,我们要评论辩论其艺术水准是失落语的,它也无涉诗歌的当代性问题。
我们的诗歌杂志,开始重新拥抱古诗词,该当是迫于生存压力吧。一些宦海、商界的实权派人物,依然在用古诗词来附庸风雅。对他们来说,与已经沉沦腐化为大略填字游戏的古诗比较,新诗技能壁垒确实太高,水太深。何况我们的教诲里,古诗的合法地位,高于新诗无数个量级。我倒要劝劝写古诗的人,若真想附庸风雅写诗,至少要对手头的东西有个基本认识。想当墨客,还是写新诗吧。若一定要坚持写古诗,最好用羊毫写。穿上长褂,留着辫子。有钱的还可以请一个丫环来研墨。
谭克修,2016,9,5,即兴
(本文不雅观点不代表平台态度,欢迎留言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