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晚年退居江宁,在居住的地方,书房、窗户、屏风上,都写上“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生作卧龙”,这句诗出自唐朝墨客薛能的《游嘉陵后溪》,可见这句诗深契王安石晚年心境。
明朝三大才子的杨慎却认为这句诗是在“讥薄武侯”。《载酒园诗话》也认为“从来文人,多好妄语。最可恶者,如薛能之薄诸葛”,对薛能大加斥责。
同一句诗,为何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理解呢?
《游嘉州后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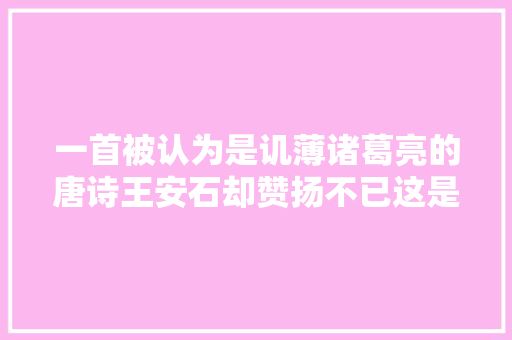
(唐)薛能
山屐经由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舂。
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生作卧龙。
赏析:
晚唐期间,军镇盘据,武夫跋扈,盛行下尅上,唐王朝对此束手无策。薛能受朝廷委任,先后出任剑南西川节度副使摄嘉州刺史、感化军节度使徐州刺史、工部尚书、许州忠武军节度使。然而,薛能带着徐州兵到许州接任忠武军节度使的时候,许州军害怕被薛能武力夺权,大将周岌乘众疑怒,于是作乱,驱逐了薛能,占城自主。
唐末乱象,由此可见。薛能深切体验到唐王朝积重难返,心中愤懑,自己也想匡正时局却无力回天,激愤不已。
薛能说:
穿着登山的木屐,路上留下脚印一串串;
远了望见小溪的对面,有人家在夕阳下舂米。
当年,诸葛亮做成了什么事?
诸葛亮就该当好好的做个隐士。
初月朔看,如果把这句诗,当做是“铺陈其事”,直抒不雅观点的话,薛能就真是不知好歹,非议诸葛亮的文治武功,后世文人斥之为“妄语”,彷佛有理。
然而,薛能这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生作卧龙”,不是“赋”,而是“比兴”,是用诸葛亮的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励精图治,克意进取,却终极壮志未酬的经历,来抒发墨客自己有苦处功,却无力回天的挫败感。
清朝吴乔在《答万季野问》给出精确的解读,他说:“薛能云: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生作卧龙。见唐室之不可扶而悔入仕途,兴也。升庵误以为赋,谓其讥薄武侯。”
薛能作为朝廷重臣,掌军国大权,游山玩水之时,依旧还在思虑国家大事,格局非平凡迂腐读书人所能理喻。
中国古代重道德文采,而轻事功。司马光因砸缸的故事,道德和聪慧的光环加身,写了一本《资治通鉴》,自以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落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然而事实上并不能挽救北宋的悲惨命运,反而站在变法强国的对立面,成为时期的绊脚石,本身便是可笑之极。
而王安石看到北宋光鲜背后积贫积弱的场合排场,主见富国强兵,推动变法,却触犯了守旧派的利益,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处处挚肘。至宋神宗去世之后,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新法,王安石生平心血付之东流。
王安石晚年退居江宁,回顾这些往事,难免有诸葛亮式的遗憾、酸心和不甘心。愤懑之余,或许也会想:如果知道结局必定如此,我又何必折腾?
“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生作卧龙”,王安石的生平也犹如诸葛亮一样,呕心沥血,勤政为国,末了却是人去政息,前功尽弃,以至于名声受累,被批为奸臣,如此宋朝又有什么值得去扶持呢?
“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生作卧龙”,或许就该当这么理解:注定去做一件不会成功的事,那还不如一开始就选择躺平!
现实中,这种事情常有,付出努力却不能有好的收成,尤其是内卷日益严重的社会体系里,躺平或许才是最睿智的选择。
来源:推文扫文少年野
声明:本文已注明转载出处,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联系邮箱:news@ersanl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