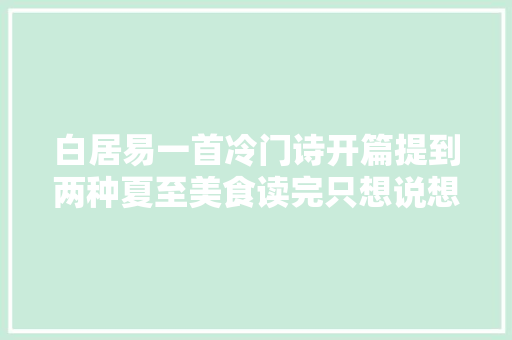夏至面
白居易一首冷门诗可以给我们供应一点思路。在《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来宾》一诗中,白居易暴露出了“吃货”实质,他落笔便写: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他怀念起自己在苏州的光阴,曾经所熟习的夏至筵席。
在其很有名的《忆江南三首》里,白居易写怀念江南最能够勾起回顾的是杭州,其次是吴宫(苏州),而苏州影象里,他并未提及美食,只写难忘的美酒与美人——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补上了苏州的夏至美食,如此,便全了苏州影象“三美”了。他这两句写美食的诗句,读了令人唇齿生喷鼻香,只想说两个字:想吃。这两句诗是:粽喷鼻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
竹筒饭
这是两道什么菜?
后者是脆嫩鲜喷鼻香的烤子鹅。虽然苏州的烤子鹅没有考试测验过,但烤鹅如今还是比较普遍的,而夏至吃鹅也有说法。中医认为鹅肉有益气补虚,和胃止渴的功效,有的地方也有“喝鹅汤,吃鹅肉,一年四季不咳嗽”的说法。
前者,则是用嫩竹子装米密封烤熟而成的“筒粽”。
我们如今的粽子,多用新鲜芦苇叶包成,在端午节食用。成书于南北朝期间的《齐民要术》,其卷九引《风土记》注记录了古代粽子的做法及食用韶光:“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夏至啖之。”“菰”也便是我们常见的茭白,用它的叶子裹上黍米,称“角黍”,端午、夏至均食用。
涌如今白居易苏州回顾里的是筒粽,泛着嫩竹的暗香。妙的是,笔者在距苏州千里之外的四川,偏僻小山村落里也久久流传着一道美食:以嫩竹筒装上新米,豌豆,鲜肉,密封,放在火上烤熟,也便是我们所谓的“竹筒饭”。
竹子的暗香,米的暗香,肉喷鼻香,在火烤之后领悟,揭开竹盖……来不及等到家拿筷子,小伙伴们迫不及待地用随意削成的竹片吃起来。直至如今,仍常常怀念当年竹林间那竹筒饭的滋味。
竹筒饭
谁曾想,多年往后,在某个夏至日,在白居易的一首诗里,居然可以读到,超过那么久且远的时空,同样的美食,同样的怀念。这种觉得,真的奇妙。
我们现在所熟习的东西,回溯到千百年前,可以从我们各朝各代的先人们那里找到源流。以是,只管我们如今举头所看见的不再是古时的那同一轮明月,我们的认知,有从古至今代代流传的下来的,我们所食所住所用,有的曾涌如今古人的周围,它们带着古代的印记,依然生动至今——我们有一样的传承。
附白居易夏至全诗——
《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来宾》
(唐)白居易
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
粽喷鼻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
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
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
交印君相次,褰帷我在前。
此乡俱老矣,东望共依然。
洛下麦秋月,江南梅雨天。
齐云楼上事,已上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