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的历史地位
荷马史诗措辞简练、情节生动形象光鲜、构造严密,如百科全书般包涵着天文、地理、历史、社会、哲学、艺术和神话等知识。鉴于希腊直到公元前 8 世纪才有笔墨记载,史诗便席卷了迈锡尼数个世纪(即口述时期)的史实和口头传说。
古希腊的面积不大,但却是一个诗乐大国。诗乐文化形式丰富多彩:既有集体的颂歌、婚曲等合唱,也有作为私下消遣的吟唱。个中,最引人瞩目确当属悲怆的挽歌。以《荷马史诗》中两位英雄的葬礼为例。“歌手们下坐在赫克托耳的身边,领唱凑楚的挽歌”,“女人们哀嚎,答呼”,接下来的三次“哭诉”分别由安德洛玛克、赫卡贝和海伦主诵。比较而言,阿喀琉斯的葬礼更为盛大;母亲提斯带领众仙女赶来悲悼哭泣;九位斯女神全部出席,亮开甜美的歌喉,轮唱挽歌,持续 17天,昼夜不断。
古希腊的英雄,在世时,追求沙场上的气吞山河;去世后,则看重诗歌对声名的传诵浸染。由此不雅观之,古希腊人认为人生虽然短暂但诗歌却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生命,能够外扬人的千秋功德。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诗是历史和哲学的“母亲”,可以为凡人的壮举或情操树立丰碑,而这一丰碑乃至比金字塔更经得起韶光的侵蚀。忠贞的佩涅洛佩不愧为人妻模范,为此,神祗便将她的高尚品行编入欢快的诗歌,使她的隽誉长存世代传唱。有褒奖自然也会有贬薄,阿伽门农的妻子克鲁泰墨丝特拉,犯有通奸和杀夫之罪,这一丑恶勾当将被后人诅咒,遗臭万年。
古希腊人相信,天界有专司诗歌的神祗,如阿波罗、慕奈莫苏奈(意为“影象”缪斯姐妹们的母亲)和缪斯等;而人间最早的墨客,如菲俄斯慕赛俄斯等,都是神的后代。能说会道是斯赠予凡人的“神圣礼物”。因此墨客和歌手在当时社会颇受敬仰。并且墨客也自傲:一个仰慕沙场勇士的社会,也该当是在“诗场”上纵横掉阖的精英。譬如,荷马通过奥德修斯之口说道:“所有的凡人中我对你称赏。一定是宙斯的女儿缘斯,要不便是阿波罗教会了你诗唱(《德赛》第八章)。”此外荷马还不止一次地赞赏奥德修斯用词典雅,本领高超,并把他比作歌手——当他“亮开洪大的嗓门,语从丹田冲出,像冬天的雪花纷飞”。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诸如此类的表述多少已带有一些程式或套话的色彩,是歌手们“事情措辞”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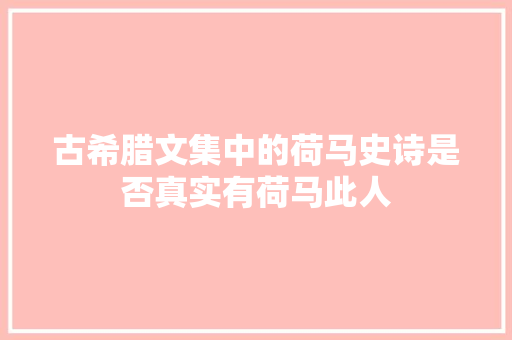
对付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的游吟墨客来说,唱诵诗歌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情。字母笔墨如果说有了,也只是刚刚产生。在史诗文本中,只有一处暗昧地提到“书写”(《伊里亚特》),而后再也不提因此,荷马有可能会请别人把自己的唱诵整理成文,但其本人却不可能撰写史诗的笔墨版本。包括荷马在内的墨客们基本上还是靠耳闻心记和反复练习来节制编诵诗歌的技巧。面对规模伟大的史诗,墨客必须节制大量的词汇,包括多种措辞用语和许多日常生活中不用或少用的词人名(包括神名)地名俯拾皆是,各种遁词、套语五花八门。要记住并准确、顺畅地唱诵这统统,不节制一点窍门,不依托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不最大限度地发挥歌手的主不雅观能动性,恐怕是弗成的。一个没有足够的天分,没有惊人影象力和卓越吟诵及演出才华的人,是不能成为吟唱墨客的。
历史上是否真的曾经有过荷马这一人物?对付这个问题,希腊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出于“弘扬民族文化”的缘故原由,他们始终“坚信”荷马出生在小亚细亚延安的希腊人移民区,是伊俄尼亚的盲墨客(伊俄尼亚人是古希腊人的一个主要分支,原来栖居希腊本土,后来受多里斯人逼迫,才迁移至小亚细亚沿海地区)。此外,希腊人还在蛛丝马迹中考证,推测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旁边,而史诗编创的韶光则可能在公元前750至675年间。不过,研究职员的证据却少得可怜,除了“自相抵牾”的史诗本身,只剩下公元前7世纪留下的一手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古诗:“(荷马是)住在契奥斯岛(爱琴海中的一个岛)的一个盲人。”
希腊人“过度阐释”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的先人也曾为了“天下归一”而“以神道设教”。可是,话又说回来,追慕先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历史事实却不能随意杜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们必须直面孔前的尴尬现实:关于荷马的创作和生活,今人所知很少,乃至是否真有荷马其人(抑或是一个墨客团体),也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这些疑问,古人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提出,当代人就更不应该视而不见了。
当然,关于荷马传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确定的:如果荷马确有其人,那他便是古希腊时期在公众场所唱诵诗歌的“游吟墨客”。在古希腊本土及其小亚细亚沿岸,有许多行吟墨客来往于各城邦之间,为人们演唱关于古代英雄业绩的诗歌。个中,伊俄尼亚的游吟墨客最为生动。他们以伊俄尼亚方言为根本,创造了一种以韵律诗为特色的口头文学形式。须要解释的是,荷马之前的希腊人有着发达的口头文化,但却不会利用笔墨。当时还没有书面笔墨,或书面笔墨已经失落传,故事传说只能凭借口头传播。之以是采纳歌谣形式,是为了使吟唱墨客随意马虎记诵。较有才能的吟唱者也可以当场即兴发挥,并且每次演出的细节都不完备一样。每个吟唱者把诗歌以自己的办法进行修正,一首诗经由一代又一代的修饰与加工,就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在公元前 8 世纪中叶,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人(后消逝当时居住在叙利亚)将字母传入希腊。希腊人在借鉴创新之后,逐渐有了拼音笔墨和书写记载。此时经数百年口耳相传的史诗情节基本定型,内容也日趋丰满。因此,当《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终极记录在文本上时,已经颇具规模,基本和当代人所看到的版本相同了。基于上述论断,我们不妨在此对史诗的起源和写作过程做一个较为稳妥的推断:就在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字母,知道如何书写时,一个天赋极高的吟唱墨客代表(或团体) 荷马涌现了,他广征博采,巧制精编,采古人之长,避众家之短,搜集了当时流传的大量口头诗歌,并结合历史、神话和传说,终极整理创编出两部不朽的长篇巨制。
《伊利亚特》分为24篇约1.5万行诗句,描写特洛伊战役第十年的故事。以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和名将阿喀琉斯的争吵为中央,集中阐述战役结束前几十天发生的事宜。叙事结束于赫克托尔的葬礼。《奥德赛》约1.2万行诗样分为24篇,讲述希腊将领奥德修斯的坎坷返国进程,也便是海上奇遇十年流落。叙事也集中在末了一年零几十天。在阐述这些故事时,荷马史诗采取了许多口诵史诗的技巧和特点,是一种范例的口头文学。纵不雅观荷马史诗,大部分都是采取伊俄尼亚方言,同时亦原谅大量的埃俄利斯方言的语法特色。有的乃至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慕凯奈时期。《伊利亚特》描写的紧张是发生在几日内的事,并且对战阵战功极为强,《奥德赛》所述业绩则有一年之久,内容多为抱负和神仙妖怪。
难怪19世纪英国小说家巴特勒指出:《奥德赛》的浸染该当是女人而不像是男人!不过针对这一驳诘,也有人提出了辩白之词:史诗写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后世墨客不断编削润色而成,虽然现存的手抄本没有早于公元前3世纪的,但是两部史诗呈现出相仿的风格,这足以表明某一个期间确有一个统摄的力量,匆匆成了这两部史诗。但这统摄力量源于何处?是个人还是某个集团?由于没有确切的笔墨记载,这些疑问还将长久困扰着人们。
参考文献:
荷马的天下. 陈戎女, 著.中华书局.2009
荷马社会研究. 晏绍祥著.上海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