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贯以为诗歌中的民歌才堪称真正的诗,由于它来自民间,是诗的源头,是百姓心声的倾吐和情绪最朴拙的表达。
那些至今流传的民歌,经由漫永劫光的淘洗,愈加地风采卓然。我知道,它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财富,因此怀着敬畏的心情读这些诗词,让人以为是那样地亲切而美好。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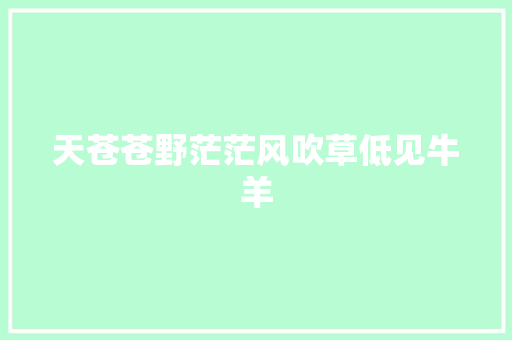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是我最最喜好的一首民歌。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我就为之吸引,为之迷恋,彷佛它描写的那个草原,我在前世就与它万般熟稔。
我险些以为它便是我的故乡,虽然从未与它谋面,但每每读《敕勒歌》这首诗,一种莫名的乡愁就会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乃至,我会因此不自觉地想起席慕蓉的几句诗: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玉轮的晚上想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我不知道在阴山下的那个敕勒川,有玉轮的晚上有没有人吹笛,我只知道,笔墨的力量是那样强大。《敕勒歌》短短二十七个字,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无比辽阔、广袤的草原图景。
在这个草原上,没有人欢马嘶,也没有如一朵朵白蘑菇盛开的帐篷,它表现出来的只有无边的空旷,还有一种雄壮,同时,在空旷和雄壮中弥漫着一种无边的静默。
偏偏,我就喜好这种空旷和静默,我在头脑里无数次地想象,那嵬峨的阴山是如何地连绵起伏,而那阴山下的敕勒川又是如何地无垠和肥沃。它养育着草原上的所有生灵,它从远古走来,没有人记得它形成于何时,也没有人知道它还要存在多少年。
草原上的天空是低垂的,牧人在草原上生活得久了,以为全体天地便是一个帐篷,而那浩渺的天空便是这个帐篷的穹顶。
那些牧人,或许他们生平都没有走出这个巨大的帐篷,但是他们并不感到遗憾,由于那俏丽清洁的草原,便是他们最好的家园。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终极安息于斯,他们大概是不会倾慕别的地方的。
是的,他们为什么要倾慕呢?他们举头所见是天之苍苍,纵目远眺是野之茫茫,一起追逐着那草中的牛羊,他们可以任意畅想,可以肆意放歌,可以做任何此时他们最想做的事情。
《敕勒歌》中不但有川还有山,《敕勒歌》中的阴山,在本日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包括狼山、乌拉山、色尔腾山、大青山等,是一个计策地位曾经非常主要的地方。
自从古老的匈奴崛起后,他们就一贯在争夺阴山山脉的掌握权,由于在匈奴的眼里,阴山便是他们的生命线。
阴山宛若一道巨大的天然樊篱,在阴山山脉的南面,黄河的漫流,导致湖泊浩瀚,水草丰美,阴山山脉以北则是广袤的草原,非常适宜放牧。
匈奴作为逐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常常随时令变革而迁徙。冬季寒冷他们会南下探求水草,夏夜酷热他们又会北上避暑,而阴山山脉的南北区域,正是匈奴空想中的宜居之地。
世代生活在阴山的中原公民,自然不会将阴山一带拱手让给匈奴,于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但是温情脉脉的文明,还有弱肉强食和残酷地屠戮。
王昌龄的《出塞》一诗,便有力地佐证了在阴山曾经发生过无数的战役,而阴山在战役中的防御浸染重之又重: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只管在阴山下,在敕勒川,不计其数的人为自己的王朝在这里流过血,作出过捐躯,但这些都已经由去了。令人欣慰的是,本日南北的多个民族在阴山下相互联络,亲如一家,和谐共存,同谋发展。
虽然那阴山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俏丽景致,现在也早已无处可寻,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我们在现实中失落去的那些关于古代的浪漫的影象,还可以到那些古老的民歌,到那些隽永的诗词里去探求,去一遍各处重温,一遍各处怀想。
而这,大概便是文学存在的意义。
作者:张风莉,笔名雨枫,甘肃省白银市作协会员,《唐诗宋词古诗词》专栏作家。已出新书《生命的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