菖蒲,“乃蒲之昌盛者”。民间,因菖蒲有对节气变革的先知,将其作为春耕的标志。《吕氏春秋》记载:冬至后五十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师长西席者,于是始耕。
两年前去苏州,在所居住的民宿附近,我曾幸运地与菖蒲临水而遇。
阳光下,清风里,一汪碧水莹绿,它们静立个中。一丛丛细叶挺立细长,像一排排带有文气的士兵,接管着路人的校阅阅兵。一阵风起于水波之上,那些直挺挺的叶子随风而动,如一支支宝剑纷纭出鞘,泛起一道道凛然的光芒。这也是有些地方把菖蒲叫做“水剑”的缘故原由。
菖蒲悠长的家史,可追溯到《诗经》: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蒲和荷一粉一绿相映成趣,衣喷鼻香鬓影的女子临水而立,蒲喷鼻香杳杳,荷叶田田,烟渚上,望不见那弄篙荡舟的少年郎——没有一种草药,可以治愈小女子铺天盖地的相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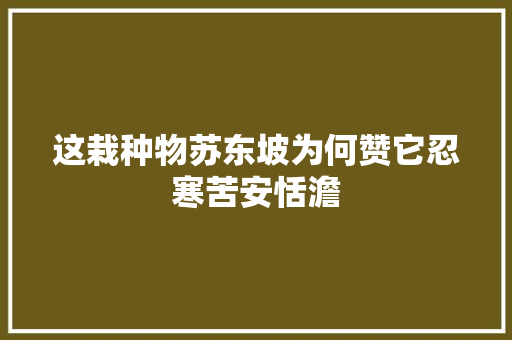
千年前,《孔雀东南飞》里的凄凉女子,以菖蒲的韧性暗示:君心如磐石,妾心如蒲草。磐石无转移,蒲草韧如丝。寥寥几字,落入耳,却重如施咒。悲剧早已过去,她的蒲苇则连续坚韧,在历史的河流里永久成长。
幼年,曾在乡下一教书先生长西席家见过菖蒲。
他是从城市下放到屯子的知青,为人正派,脾气温和。乡下人家多植好养的蔷薇、月季,唯独他家屋里屋外、盆里瓮中遍植菖蒲,逐日与书山书海为伴,居然有种相得益彰的美。每次途经他家门前,会忍不住放慢脚步,向屋内张望。隔着门缝,会看见教书先生长西席布衣素服端坐一旁,在菖蒲的盎然绿意中,或温书,或煮茶。
我痴痴立在门外,只以为那里面有不一样的人间烟火。当下暗想:终年夜了,也要像先生长西席一样在家里种满菖蒲。
自古以来,菖蒲是文人墨客喜好之物。与兰、菊、水仙并称为“花草四雅”。他们把菖蒲持重地移植到身边,在书桌旁放置,昼夜相伴。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夸奖它:不假日色,不资寸土,不计春秋,愈久则愈密,愈瘠则愈细,可以适情,可以养性,书斋旁边一有此君,便觉清趣洒脱。
苏轼很欣赏其“苍然于几案间”,且能“忍寒苦,安淡泊,与清泉白石为伍,不待泥土而生者”。这位声名赫赫的大文学家为了养好菖蒲,竟然去捡碎石,“取数百枚以养石菖蒲”。
听说,只要净水不涸,菖蒲可数十年不枯。另据《赞石菖蒲》记述,由于陆路羁旅,不便照看,苏轼曾将游慈湖山时采得的菖蒲配上好看的石子,寄养在朋侪九江羽士家中,日后路经此地时,定要特地探看菖蒲是否安好。想想九江羽士得东坡居士探望还要沾菖蒲的光,也真是可以收入“人不如蒲”系列了。由此可见宋代文人不雅观养石菖蒲的风气之盛。
一晃经年,从屯子到城市,从平房到电梯房,生活环境越来越好,菖蒲终是没种。
没种的缘故原由,实在是怕自己的俗气玷污了它,它有兰的幽雅、竹的洒脱、梅的素洁、菊的清高,纷乱人间怎好惊扰?只有那个遍植菖蒲的梦,时时温存于心。
后来,有时看到“扬州八怪”之首金农的《菖蒲图》,短短密密的菖蒲植于陶钵,不设敷色,却自有一种清气。这样的清气非常人能有。再读长款题跋忍不住眼湿:“石女嫁得蒲家郎,朝朝饮水还休粮。曾享尧年千万寿,生平绿发无秋霜。”寥寥数字,却是人与植物的奇妙情绪。
金农生平落魄,视菖蒲为人,石女和蒲郎都是心腹。金农有诗言:莫讶菖蒲花罕见,不逢心腹不着花。他对菖蒲的期待,也如古琴一样,是得遇心腹,他们在方寸之间,与之对话,得到欢畅、知足和感悟,便是方寸之间的大天下。菖蒲不美,却是一种恰当的安慰,为他带来内心的安静平和。
实在,他自己也正是一株老绿的菖蒲,顽强、孤独地成长在逼仄的旧光阴阴里。
菖蒲是清寂的,清寂的东西都是倔强的。那是一种有傲骨的倔强。纵然无闻,也不流俗,就那样兀自觉展,不谄媚,也不讨巧。
(壹点号 读点)
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不代表齐鲁壹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