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那年,我做了一场美梦。
我梦见外祖母家的小院里,梅花开了一全体冬季。而梅姑就站在树下,收了一坛子的雪水,说来年要给我烹茶。
她手腕上戴着我赠的玉跳脱,而我腰间挂着一枚喷鼻香囊,上面的梅花是她亲手绣下。
后来啊,那场梦还是没有做完,我披上战袍去了硝烟弥漫的厮杀。而母亲也自作主见,拆散了我的姻缘,送走了我的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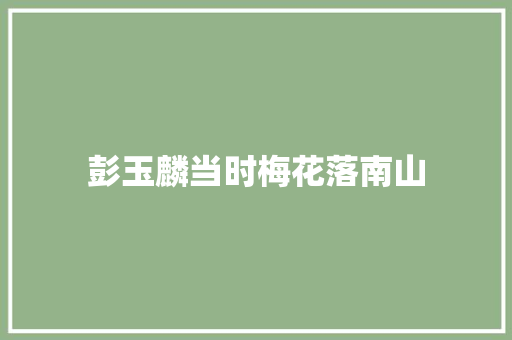
一
梅姑原来唤做王竹宾,是外祖母收养的孤女,也便是我的姑母。可她偏偏生的和我一样平常大的年纪,我不愿唤她姑母,只叫她梅姑。
“你乐意如何唤便如何唤吧!
”梅姑拗不过我,只好接管了这个名字。
而我之以是唤她梅姑,是由于她爱极了梅花。外祖母院落里有数十株梅花,每一株都是因她的照料而存活下。年年冬日里,她都立在树下,等今冬第一场雪的到来,然后封存使女,来年为我烹茶。
“梅姑,撑着些伞!
”那时我总立在她身后,撑起一把桐油伞,遮住纷纭扬扬的絮子落在她的眉眼之间。
“雪琴!
”她轻唤我一声,我赶忙应去。
“我在呢!
”
“你遮住我的视线,我怎么看梅花?”梅姑转头,连恼怒的神色都是美的。
“那便看我好了?”
她不再说话了,可是我分明看到她脸上的颜色,变成了春日桃花。
二
或许是我心里装了太多的东西,有她,还有天下。
我究竟披上了盔甲,去了兵刃之间求生的金戈铁马。而母亲无法接管我们之间的情愫,为她选择了别的人家。
待我得胜归来,她已然成了别人妻。我看着她绾起长发,粉黛却是为别人而画。
“他对你好吗?”我追她出来,还是立在院落的那棵梅花树下。
她点点头不语,我便也没了接下来要说的话。
我屈服父母之命,娶了邹家的小姐。她眉眼虽不似梅姑温婉,却也算的明艳无暇。
“夫君,为何只爱画梅花?”妻子不懂为何,只以为是我爱它的气节罢了。
我饮下她为我烹好的茶,茶喷鼻香浓郁,只是不是当年的梅花。
国家衰败,我愁于兴亡,只得一次次披上盔甲,去为民族做末了的挣扎。要知道浊世里,百无一用的便是诗人。口诛笔伐拉不回政府的懦弱,只有兵马,才能暂时为民族争取一个喘息的机会。
可我还是亲眼看着它走到了苍苍晚年。我可以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可是我放弃了统统,还是无法改变这个结局。
到了不惑的年纪里,我功成名就,有高官厚禄,有百姓爱戴,可我却在那场死活之战前,接到了梅姑离开的。妻子来信,说她难产而去世。可我留在她身边的侍卫却言她的难产,与妻子有关。
那场战役,我打的困难。几处负伤,差点就没有命回来。或许是由于她走了,这个人世里,我再没什么好留恋。
“若我活着归来,便为你画万株梅花吊唁!
”晕厥前,我立下誓言。
可等我睁开眼睛,我创造自己还在人间。
床边是愁眉不展的妻子,我从她的眉眼里,看见了以前忽略的狠厉。
后来我再不同她相见,毅然辞官,回了梅花故里,画了四十载的梅花。
“自从一别衡阳后,无限相思寄雪喷鼻香。羌笛年年吹塞上,滞人旧梦到潇湘。”每一株梅花旁,都有我对你的留恋,可寥寥数言,哪里写得尽我半生的思念?
三
记得湖南相逢时,我们仍旧坐在开着梅花的庭院下,你信手烹着茶,说着无关风月的闲话。
那时我很想问问你如今若何,可是看着你眉眼的干瘪,又以为问什么都是多余。
若我那年没有放你归去,是不是,你也不会留我一人在这孤独的人间?可偏偏我放了手,让我再也没能同你相逢。
幼年相亲意气投,芳踪喜共渭阳留。
剧怜窗下厮磨惯,难忘灯前笑语柔。
生许相依原有愿,去世期入梦竟无由。
笠帽岭上冬青树,一道土墙万古愁。
我画了万株梅花,种下了满园绿萼轻语,用四十载的光阴去遗憾,当时梅花落南山。
四
后人评说我时,知晓我当年征战疆场,无人能敌;知晓我弃笔从戎,晚年辞官归隐,画梅画出了自己的一派风骨。可无人知晓你路子过我的倾城光阴,影响了我生平的轨迹与发展;无人知晓我生平想念的,只有梅花树下那个为我烹茶绣花的姑娘。
平生最薄封侯愿,
愿与梅花过生平。
唯有美男心似铁,
始终不负岁寒盟。
庭有梅花树,梅姑去世之年植下,今仍年年纪末盛放,只是少了梅花下的美男与佳话。
五
彭玉麟,字雪琴,号退省庵主人。晚清名将,湘军领袖,人称“雪帅”,复兴四大名臣之一,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大清三杰”。
彭玉麟幼年时,居安徽老家,遇见了外祖母收养的孤女王竹宾。可因世俗羁绊与父母的阻挡,终极错过,看着她另嫁他人。后梅姑难产而去世,他仇恨生平,赌咒为她画万株梅花吊唁。终用四十载的光阴,成了梅妻鹤子的另一个痴情佳话。
“生平心腹是梅花,魂梦相依萼绿华。别有闲情逸韵在,水窗烟月影横斜。”
光绪十六年,这位叱咤生平的老者病逝,家中无余财,仅十万梅花共葬。
作者:霜见十九,00后自由写手,喜好统统古风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