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赵师长西席,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和蔼的老人家。他常年在东冶镇的店铺里做账,家里并没有太多田地家当。由于我父亲年幼时便从家里独立出来住在东冶镇,我对付与祖父同住的影象并不多。我只听说过,祖父对我疼爱有加,每次的肉菜都会喂给我,可能这样让我年纪轻轻就不能接管肉食,闻到肉味就会感到恶心。我记得我常常跟随父亲去槐荫村落探望祖父祖母。那时的我大约六、七岁,刚为祖父庆祝过他七十二岁的生日,百口人一起吃了顿饺子。然而不久后,祖父便因中风病逝,他的尸首被安置在西堡住宅的正厅。直到1932年祖母去世后,祖父和祖母的灵柩才一同出殡,安葬在五级村落的新墓地。
我家祖父的孩子比较多,统共有四个儿子和一女儿。第一个是殿武哥哥,但他不幸很早就过世了。我父亲是第二个孩子,排行第三的是秉武弟弟,最小的是崇武弟弟。我还有一个叫心儿姑姑的姐姐,她常常与祖父母住在一起。因此,我们这一代堂兄弟姐妹们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彼此关系犹如家人一样。而我的父亲由于伯父伯母之前分家搬离了原居地,就相称于这里的长兄了。据他讲,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在他小时候很艰巨,他只在学校读了两年书。但他非常努力自学,看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很好。他回顾说,他放学后常常去地里捡高梁茬,用来当柴火。每天早上他早早起床生火,给祖母熬好稀饭再上学去。这便是他幼年期间的生活状态。大家都非常依赖他,由于他是家里的宗子,有着强烈的任务感和义务感。这些是爷爷的孩子的大致情形和我父亲的经历,现在我们与他们的关系都非常紧密且主要。
在我出生之前,我的伯父在北京赚了大钱,还捐了官职,并带着祖父去北京旅游了一次。然而,伯母不愿意将赚的钱交给大家庭,因此她想分家。伯母身材矮小,短胖,说话严厉,不好相处,以是妯娌们给她起了个外号。末了,祖父祖母只得赞许他们家先分出去。伯父在东五里的大集镇东冶镇买了一个大院子,而我有幸在这个宅院里出身。我的外祖母家在东镇冶东南的一个小村落落里。母亲有身晚期住在那边,但不到九个月我就要出生了。当时由于韶光紧迫,母亲无法返回槐荫的婆家生产,以是舅舅匆忙将她送到了伯父家西边的屋子里,我在那里降生。由于我在东冶出生,父母曾短暂地称我为“东生”,但后来还是按照家族排行习气,给我起了“立柱”这个小名。随着大家庭人口增多,我们原来的槐荫老宅住不下了。1915年,我伯父借给父亲一些钱(相称于现在的一千元),父亲用这些钱买了一处与伯父家相邻的院子。这个院子原来是李进士家的,是一个有三个院子的住宅。后院伯父已经买下了,而前面的两院,包括仪门和过厅,以及内外院的厢房共十九间,都被我父亲买下。于是,我们家从槐荫村落搬到了五台县最大的集镇东冶镇。
这里我先给大家先容一下槐荫村落的环境。稍后,我们将详细磋商东冶镇的特点。槐荫村落和东冶镇之间隔着一条十分清澈的小河,河流两侧是肥沃的农田,这里十分富余繁荣。小营河的水终极在槐荫村落的南边汇入滹沱河。槐荫村落位于五台县的西南边缘,向西走大约十来里路就进入了嶂县(现在叫原平县)的地界。因此,我们这一带与崞县有很多亲戚往来。在村落庄西边五里的地方,有一座叫做济胜桥的桥,它是五台通往太原的公路上必经的一座桥梁。简而言之,槐荫村落是个俏丽的村落庄,与富饶的东冶镇仅一河之隔,而且交通便利,与周边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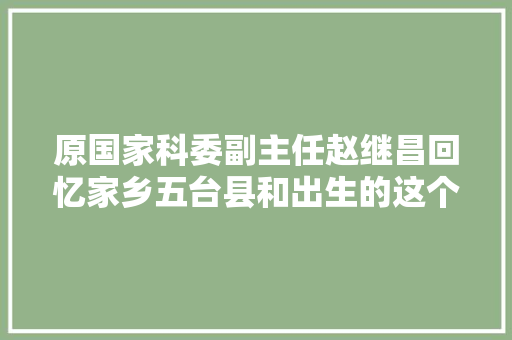
由于槐荫村落被磨子山(油篓山)挡北,田地渠道纵横,而东南西侧有河水环抱,以是这里风光奇丽,气温也相对较高。这里的居民家户户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春天来得比别处都要早。每当翻开旧时的五台县志,总能创造个中记录了“五台十景”,个中有一景就与槐荫村落息息相关。到了三月春暖花开的时候,其他地方还在冬天的尾巴里挣扎,但槐荫村落的三里长街上已经是春意浓浓了。垂柳已经抽出了嫩绿的新芽,桃花和杏花竞相开放,一派活气勃勃的景象。进入村落里,就像走进了画卷中。在村落的中部有个叫大寺的寺院,村落里的事情都在这里处理。大寺前有一块空地作为广场,南边还有一座戏台。大寺后面的小山坡上便是小学校,最高的土崖上还有座关公庙。在大寺附近的路边,有一口甜水井,以前行商途经这里都会来这打水解渴。由于水源充足,大寺周围还种着几亩稻田。可以说,槐荫村落是五台县最俏丽的村落落之一,有人说它就像晋北的小江南。只管过去这个村落里王侯将相不多,但文人学者不少。像民国初年的书法家赵斐造诣是这村落的人。由于这里读书人很多,以是当教员的大概多,我小学的老师中就有六位是槐荫村落的。此外,民国期间山西的旧军人赵承绶也是槐荫村落的人。他曾经在西北军国民三军服役,后来投奔了阎锡山。在太原解放前,他选择了投诚公民解放军。而在共产党方面,槐荫村落也有几位五台的早期共产党员,如赵源、赵之容、朱秉权等。
在槐荫村落的最末端,有个小地方叫小关堡,那里有一扇巨大的门,仿佛是一座城池的大门。我老家所在的西堡就坐落在村落庄的西边,也有个堡门。这堡子建在高高的土坡上,坡非常陡峭,大车都上不去。在西堡坡的下方,西侧是一家烧饼店,东侧则是一家骡马堆栈,店门上还贴着对联。这些都见告我们,西堡前边是一条主要的交通大道。至于村落庄中部和东部的其他堡子,我记不清它们的名字了,或者我已经忘却了。在村落庄最东头,有个娘娘庙,前面是个开阔的广场,广场南边有个戏台。后来这娘娘庙变成了赵氏家族的家祠,他们的先人叫国英,神位就供在庙里。这个村落庄虽然有两家赵氏家族,但我们这一家和他们相处得很好,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宗族歧视或者轇轕。这是由于这里的人们思想开放,不搞宗派斗争。其余,旧社会里人们因此地主和农人、穷汉和富人的身份来区分的,不同家族之间,基本没有大的抵牾。之前说到的槐荫村落由于环境幽美,以是人才辈出。听说这里的年轻人长得都挺姣好。附近的人常说这样一句话:“槐荫出美人”。东冶镇的家庭主妇们特殊善于做白面馒头,做出来的馒头又白又松软,特殊好吃。而在东冶北边五里外的北大兴村落,那里栽种的黄黍粘米非常喷鼻香甜,油炸的糕点也特殊美味。至于槐荫村落的姑娘们,我以为不一定个个都美,但至少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思想比较开放。
由于我小时候就搬到了东冶居住,以是对付两岁前在槐荫的生活影象已经模糊不清。现在能够记得的,是在襁褓中睡在老家的屋子里,这可能是我搬家到东冶后,再次回到槐荫时的情景。从我四五岁开始有影象以来,每年都会多次去奶奶家。爷爷家在西堡东巷的最北端,家里有两部分,南院的东侧有一个半亩大小的空地,空地东边的屋子是磨房。这个院子还有个走马的大门。后院比前院稍大一些。在后院的正房后面,有一个小花园,实在并不种花,只有几棵树和一些菜地。这个花园的后墙和两边的墙都建在山崖边,崖下是一条大沟,再往北便是高高的地皮和磨子山。因此,我们的家在村落庄的边缘,非常安静。当我们和祖父一起住时,我家和四叔家住后院,而祖父祖母和三叔家住在南院。我们搬走后,就只有四叔一家还住在后院,有时东房会留一个邻居。
每到新年的正月月朔早上,当地人称大年初一的那天,我们会提前起床去拜见槐荫奶奶和爷爷家的家族成员。天微亮的时候,我们村落里的男人就会前往奶奶家,向祖父母磕头拜年。吃完奶奶家准备的饺子后,我们会和本族的爷爷、叔伯、兄弟们一起,前往西边的先人墓地祭拜。下午我们会再逐一拜访本族在东西两巷的长辈们。只有到了晚上,我们才会回到东冶的家。而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和十月月朔,我们会一起前往槐荫的地方,和族人一起敬拜先人的墓地。如果家族里有主要的事情发生,比如叔父姑母家的婚丧大事,或者是当槐荫庙会期间有庆贺活动或戏曲演出时,我也会回到奶奶家,与堂兄弟、堂姐、表兄等一起参与活动。这些时候的相聚总是让我感到十分快乐和充足。
在奶奶家附近有个井,这个井离平地有些远,由于山堡很高,以是井特殊深。为了从井里绞水,得用很长的井绳绕着辘护绕三圈才能看到水。这井水很甜美,煮绿豆稀粥特殊好喝,大娘喜好叫它“小蜜水”。听说东冶镇的井水很苦,我们更惦记西堡上的这口甜井了。
我对家乡槐荫有着深厚的感情,由于这里是我童年的乐园,我和堂兄弟、表兄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欢快光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亲兄弟一样亲密无间。比较之下,我们家搬到东冶镇后,作为一个外来家庭,我们与邻居的交往并不多。只管五级村落有外祖母的家,但我们也很少去拜访,以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并失慎密。
在先容槐荫村落的时候,我也顺便提一下流经它和东冶镇之间的小营河。这条小河总是让我想起我的童年光阴。小营河的水质特殊清澈,河里有许多小鱼和蝌蚪在游动。河床铺满了各种颜色、圆润的石头。虽然水流不算大,但整年都不会干涸。我小时候,在春、夏、秋三个时令,都要通过一块块踏石过河。当大水来临时,如果大水冲走了踏石,人们就会挑选大而平的石头,重新摆好间隔成行,方便人们过河。在冬天河水结冰之前,人们会搭起一座木桥,这样马车就能通过了。由于这条河从北沟流下,北沟很长,两边有高山,以是暴雨来临时,河水会迅速上涨。如果水势冲到农田那边,良田就会遭受毁坏。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后农人们又重新开始耕种修复。在大水冲走踏石后还没有韶光重铺的时候,要过河就必须赤脚穿过小石子,在河里淌水过河。我依然记得一次我父亲卷起裤腿先背着母亲涉水而过,又背我过去的情形。我还记得有一次马车在过陡峭而波折的河道时翻了车,套车的骡子都倒在了河里,幸好我和我母亲被人从翻倒的车里救出,再被送过河去。这些事情都深深地刻在我童年的影象中。
下面开始从一位亲长提及,他是我的伯父赵殿武,小名快意,别称紫庭,家里人常常称之为德寿堂的掌权者。伯父在年少时曾在商店学徒打工,中年后凭借聪慧和努力在东冶镇崭露锋芒,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广泛赞誉。有句话说得好:“谈起富余,得数他姓赵”。虽然伯父并非地方权力最高的大户人家,但他在北京赚得的钱财,让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更为显著。只管他的紧张成本不在本地,地皮也不多,因此他与当地民众的抵牾并不突出。再说说另一位主要人物,那便是赵戴襄。他是山西名流赵戴文的弟弟,也是五台县的一位大名流,就住在我们家对面。而徐广进则是南街的著名财主。在本地地位和财力上,伯父虽然不及赵戴襄,但他的影响力在京城得以发挥,使其在外界更加受到人们的尊敬。以是不管是从哪里看,他都相称的“风光”。
据传,我的叔叔年幼时在本地学习技艺成为学徒,待年纪稍长后,在亲友的引领下,前往北京探求生活出路。他回顾起当初上北京的旅程,说那时还未建筑京汉铁路,只能走旱路。他走过长城岭、阜平、保定,历经半个月的艰辛跋涉才到达北京。那时他仅携带一双布鞋和五百文制钱作为盘缠。在旅途中,他住过一些小店,每夜花费二三文钱;用饭的用度也不过几文钱。因此,当他抵达北京时,身上还剩下二三百文钱。之后,他在北京朝阳门外与族里一位长辈一起开办了一个名叫万盛窑厂的烧砖瓦的窑厂。正值西太后大举建筑颐和园等工程,他们的窑厂凭借此机遇,发展得十分茂盛。数年前我参不雅观故宫的午门时,还能看到城墙上有许多刻有万盛窑厂字样的大城砖。除了万盛窑厂,叔叔还与他人合营了太厚导生恒中药店、在铁铺村落附近的五台山有一个商店以及在东冶镇与他人合营的锦和成纸坊。此外,他还拥有几十亩的水田和旱地。
伯父虽然财富增加,家当丰富,但未重视学问和学位。在清朝西太后掌权的期间,由于社会地位的局限性,他选择了通过捐纳的办法提升官职。这种做法,实在因此银两换取官职的腐败征象。他给自己购买了如“参将”、“守备”、“知州”等官职;为我祖父购得“太史”的名誉官职;还为我祖母和伯母赢得了“一品夫人”的尊贵称号。因此,他们家的条案上常常供奉着装着诏书的诰封匣子。这些匣子由梨木精心雕刻而成,上面镂空成蟠龙和珠子,并带有水波图案。诏书则以满汉两种笔墨书写,上方还盖有皇家的御玺大印。家中长辈们见告我,祖父、祖母、伯父和伯母都有清朝的官服。在我祖父的葬礼上,他身着朝服,头戴镶嵌水晶的赤色缨帽,颈戴朝珠,足蹬朝靴,尸体上还覆盖着陀罗经纸被。家人们提到,伯父在捐官后,朝廷还降下诏书到他家。接旨时,仪式非常持重,这也是家族中一段难忘的盛典。听说伯父曾被赐封为山东曹州府的知府,但因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他未能履新。这些事宜都反响了当时清朝政治制度的一些问题,也见证了家族曾经的辉煌与变迁。
伯父的院子紧挨着我们家的东边,两家的屋子牢牢相连,仅有一堵墙相隔。须要办理大事(如丧事)时,我们就会打通这堵墙,方便来往。他家的院子原来是三进三院的构造,曾经属于李进士家,但由于后院李家后代不愿意出售,以是我们只买了前两进院。大门上雕刻着三个字,代表着父辈的官职。我不清楚这位官员的职位有多高,但知道其地位不如那般显赫,可能相称于现在的中高等官员。从外院到内院,必须经由一个有着四块门板的仪门,门板上刻着四个大字。正厅的房檐下挂着一个蓝色的横匾,上面用金色滚龙和金字写着四个字。正厅里有一个二尺见方的大镜子装在玻璃框里,镜子里嵌着西太后亲笔写的“福寿”二字。伯父家常常从北京购买各种家具和用品,如高等木制轿车、黄铜制暖炉、八音匣等。家中还常常摆放散发喷鼻香味的木瓜和佛手等水果。我曾见过一个三寸多长的玄色物品,伯父见告我那是喷鼻香蕉,我剥皮吃了,那是我第一次尝到。在旧社会,富余人家常吸鸦片,伯父也不例外。他的生活并不顺利,正如他为自己写的墓志铭所说。这块碑文由我父亲用朱砂笔写在碑石上然后雕刻完成。原来立在伯父墓旁,现在可能已遭毁坏。伯父及其一子二女在我小学期间相继去世。在我放假或失落学在家时,曾照顾伯父几个月。过年时,他给了我五元钱。我三叔的两个儿子在我上学期间和抗战初期曾帮助我经济上。伯父的不幸遭遇既有有时性也有一定性。在旧社会,由穷变富很难,但富而堕落是普遍征象。伯父家也未能幸免。伯母因生活优渥而身体肥胖,一天中午因中风去世。伯父唯一的儿子赵寿昌曾在北京法政大学读书,但因不明缘故原由未去日本留学。因家庭富余,他后来染上疾病并吸鸦片,终极病重不治。伯父家曾买过一个邻县的女孩做丫环叫春喷鼻香,终年夜后嫁人。伯父曾再娶并有一女。我曾在抗战前见过伯父担当副镇长的匾额挂在院子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保持革命后代的纯洁和不变质。以上便是关于伯父家的简述,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父亲和我叔叔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为人非常正派,看重交谊,从不失落信于人。他从不涉足不良的娱乐场所,也不吸食有害的毒品,这都是由于他为人正派的风致。父亲很重视节俭,喜好用和平的办法与他人相处。他对子女的哀求非常严格,以是用“父严母慈”来形容我的父母是很恰当的。父亲对我非常关爱,他晚年过着节俭的生活,把心思都放在了我的未来上。他乃至拿出了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供我上学。在我成年后,1949年我回到老家看望了他们。母亲说,没想到晚年还能得到我的照顾,他们之前乃至以为可能等不到我。父亲知道我在邻县担当过抗日县长的职务,他出于关心我的身体考虑,见告我四处奔波不如做个贩子,生活会轻松许多。然而,他无法理解那些有共产主义空想的革命战士对个人幸福和公民幸福之间关系的意见。他不能理解我们为了更高的空想而奋斗的人生不雅观。
父亲出生于1871年农历五月,属马。母亲则生于1875年农历四月,属猪。当我出生时,父亲已经41岁,母亲37岁,因此我是家中的老幺。据我父亲曾说,他小时候在东冶镇的商店当过学徒,到了二十岁旁边,去了北京在我伯父的万盛窑厂当了记账师长西席。他在那里事情了二十年,但职位和收入都没有明显提升,难以支撑家庭生活。因此,他在40岁时离开了北京回到家乡。由我伯父帮助,我父亲在东冶镇区公署旁开了一家杂货店。我五、六岁时,那家店就倒闭了,父亲之后在家闲置了一、二年。不久后,乡绅赵戴襄推举他担当五台县政府办的银号经理,这银号名叫汇通钱局。这个银号紧张办理存放汇兑、发行县钞票、经营地产,乃至还代收田赋。由于父亲有丰富的商业履历和北京二十年的事情履历,以是他被县里选中。由于他的管理能力和办事能力都很强,以是常常被约请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担当责任经理。父亲还被聘为平耀局的经理,由于他的热心做事,省政府给他颁发了一个银质嘉禾奖章,并赠予了一个写有“四字”的匾额。当上一世的班禅喇嘛来到五台山时,五台县成立了支差局,我父亲被派去处理支差局的事情。由于他在县里的官钱局事情,以是他有机会与县长和其他官员打仗。从前曾任县长的鲁宗藩和陶封锡与他关系很好。当乡间的亲友邻居因违规受到罚款时,他们常请我父亲帮忙说情减免。但父亲从不哀求别人给他报酬。如果别人坚持要送他一些物品,他会用其他礼品回赠。他相信广交朋友对自己有好处。然而,当我家境困难,我学费难以张罗时,他的一些朋友却没有一个人乐意帮助我们。这让他晚年对人情光滑油滑感到淡薄,也有了深深的感触。总的来说,我父亲的生平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原则。
在大约1918或1919年的时候,我的父亲被派往县城担当县钱局经理。在此之前,我大约在1920年入小学之前已经去过他的事情地点。我记得那年秋日县城举办了全县高年级学生的运动会,我有幸不雅观赏了他们的精彩演出。当我开始上学后,每当寒暑假期间,我都会去县城的汇通钱局探望父亲。我常常和他一起睡在同一张炕上,这样他可以看到我,这个家里最小的孩子,从而缓解他离开家的寂寞。同时,他也会监督我练习羊毫字和阅读书本。这样的日子,让我俩都感到快乐和知足。在我的影象中,那些与父亲共度的光阴都是那么的温馨和难忘。每当我回忆起那些日子,我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亲情和温暖。
我父亲刚加入汇通钱局时,约定薪资为每月十元。但过了一两年,他创造百十元的年收入难以支撑百口生活。当时五台县的县长鲁宗藩调任他县,我父亲曾考虑跟随他到新岗位,担当县政府的文书员。县政府的司帐员和文书员常由县长亲信担当,但他们薪水并不高,常日只有十几元。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后,五台县政府为了留住他,决定除了每月十元的人为外,还将钱局的年利润按十股分配。我父亲以他的劳力分得一股,其他副经理等人则分得三厘、五厘不等的报酬。大部分利润会作为县政府收入。这种以劳力作为股份的制度在旧社会的私营商店很常见,财东供应资金,经理和副经理则以劳力作为股份参与分红。随着钱局业务的扩大,到1923年旁边,我父亲的年收入提高到六、七百元,他也开始有些积蓄。于是他花了不少钱来装修院中的正厅,这是一个五间的瓦房,进深较长。虽然原来是李进士家的过厅,但由于我们家只租用了部分房间,以是他们把后门封上,将大厅作为家具和食品的仓库。邻居赵戴襄曾建议我父亲装改动厅以便他家办丧事借用。同时,他也想在祖母去世前为我及二姐办好婚事。因此,他们决定对正厅进行装修,并同时修理了东西厢房。我们一家从西厢房搬到正厅居住,而东厢房则作为厨房利用。在我十三岁时,父母为我安排了婚姻。第二年又为我二姐找了一个人家。后来,父亲又购买了五亩田地。因地质条件不好,他只花了很少的钱租了出去,打算将来作为坟地利用。我哥哥在京、津的晋胜银行事情后也寄回了一些钱。父亲用这些钱买了八亩好地,但后来又卖掉了,由于地租收入太低了。当时放款的年利率常日比地租高很多。几年后,父亲的股份收益减少到了六厘。到了1930年前后,父亲用一部分积蓄购买了榆次县晋华纺织厂的股票约千元。虽然每年股息不多,但详细是否有分红就不清楚了。我读高中时,父亲便辞去了事情在家养老。晚年时他与其他朋侪互助经营小商业和作坊,虽然收入不多但足以坚持生活。
在抗战期间,我在河北省平山县的邻县担当抗日政府的县长。那时候,由于我的职务,汉奸曾多次向我家敲诈,我父亲无奈之下给了他们三百元。那八年抗战,我在游击战中度过,常常梦见自己偷偷潜回被仇敌盘踞的家乡,探望我的父母。1949年的秋日,我有机会回家探望父母。那时我见到父亲,但不久后的冬天,他就离世了,享年七十九岁。我在他去世前已经见过他一次面。然后在我1958年再次回家探亲后,我的母亲在1959年离世,享年八十四岁。他们两位都经历了清朝、民国、国民党统治和日寇盘踞的期间,也在解放后的日子里生活过,真可谓阅尽人间沧桑。
我的父亲有着两个特殊的兴趣。一是热爱读书和写字。只管从他偶尔的言谈中能觉得到他以为做生意并不如从政那样高大上,但他仍旧把阅读和知识视作人生中最主要的部分。每当他有空,就会拿起书本,特殊是那些古典小说和文言文。他的字迹非常工致,且秀气,同事们对他的羊毫字赞不绝口,但他总是谦逊地称自己的字只是普通的商业体字,与书法家的作品还有差距。我还记得,当我读初中的时候,家中须要重做屏风,父亲竟主动拉来纸张让我来写屏风上的对联。这是他对我的爱护,也表示出他笃信读书人的主要性。他的另一个爱好是保持清洁和秩序。无论是他的住所还是院子,都哀求六根清净,每件物品的摆放都井井有条。他非常节俭,这种习气从小就影响了我。比如每天清晨,他都会客岁夜门外扫行人性,然后清理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会打扫大门和院子。父亲还常常在冬天在风斗上写古文或古诗的段落,并在末端写上他的别号“34”。我理解这个别号是他希望自己保持明净的意思,并非超脱尘世。此外,父亲还把我们的家称为“乐天国”,这代表了他知足常乐、乐不雅观向上的旧思想。我们给家里写信时,有时会写“赵乐天国收”,而不是直接写父亲的名字,这是旧时礼教中对长者的一种尊敬和避讳。这便是我父亲的两种爱好,大略而深远地影响着我。
现在我来给大家先容一下我的妈妈。在我们这儿,我们习气称呼父亲为爹,而妈妈则称为嬷嬷,实在便是对母亲的亲切称呼。我妈妈叫杜三清,她还有个昵称叫改变。我外祖母的家位于东冶镇阁下的五级村落。我曾经见过外祖母,她那时候脚上长了个大瘤子,以是不能起床,不过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关于和她对话或是我在她家过夜的影象,我彷佛已经不记得了。我妈妈有四个兄弟姐妹,我们家与他们都有来往,但与伯父和叔叔家更为亲近。二姥爷家是个大家族,他的儿子杜春晃是个读书人,我们都叫他二舅。他家有个很精细的书房院。而舅舅家则比较穷苦,可能是由于舅舅沉迷于大烟,导致家道中落。我记得在1938年我在岢岚县城事情时,曾见过舅舅在一家商店里闲居。我父母关系一贯很好,从未红过脸。由于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以是吃妈妈的奶水韶光最长。我还记得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妈妈还常常抱着我喂奶。妈妈是个心地善良、细心的人,一点小事都会让她睡不着觉。每当家里碰着困难或战役时,她总是心惊肉跳的。这便是我的妈妈,一个充满爱心和慈悲的人。
我这生平对家庭有些许不满,紧张在于我父亲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就为我和我哥哥找来了一位年事上相差三到四岁的妻子。对付哥哥,这种情形更是导致了深深的抵牾。1924年他还乡度假时,提出了离婚。他将离婚的申请交给了镇公所,但碰着了困难,由于当时镇公所并未处理过离婚案件。在过去的旧社会里,人们常常私下办理这类问题。于是,作为副镇长的我伯父就帮忙把这个问题暂时办理了。封建的包办婚姻制度像一扇扇难以打开的铁门,对付我们来说冲要破真的非常难。虽然当时的社会许可娶妾,但离婚却十分困难。我哥哥和嫂子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但他对她不闻不问。有一天晚上,嫂子试图自尽,被哥哥创造了。哥哥因此以为有了痛处,而嫂子则哭着说要离开我们家。不过,她回到自己外家五级村落后,她的家人第二天又将她送回了我们家。嫂子向母亲认错并磕头,母亲虽然批评了她,但同时也担心事情并未完备办理。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哥哥虽然暂时迁就了嫂子,并生下了三个孩子,但第三个孩子不幸短命了。然而,他们的思想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办理。因此,在抗日战役开始前夕,哥哥在太原再次结婚。由于他之前的妻子还留在家中,从1深感酸楚、分离、挣扎的他于1936年开始,直至1959年去世的这二十多年里再也无法回家探望父母。这件事给他个人和父母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痛楚。
我个人的经历和很多人有些相似。我亲眼见证了我哥哥的痛楚遭遇,但旧时期的封建道德却像一把锁,把我禁锢在了这个无路可逃的困境里。那年冬初的时候,家里四个孩子都在院子里与母亲一同事情,用斧子将兰炭砸成小块,为寒冷的冬季准备燃料。我们一边事情,一边评论辩论着对包办婚姻的不满。两位姐姐流露出对婆家的不满,但她们对丈夫本身并没有太多怨言。哥哥长久以来对婚姻抱有不满,我们都知道。作为最小的孩子,我也开始表达我对婚姻制度的反感,我说大人们只是为了让有人照顾他们而给儿子娶媳妇,而不是让他们自己选择伴侣,这样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呢?父亲也理解我们的不满,但在那个旧社会,他无能为力。他只是说,如果我们有能力,可以像某些有权势的人一样娶几个小老婆。后来,我上大学时开始思考自己的婚姻问题。如果在家乡无法得到办理,我乃至考虑去苏区探求办理办法。在抗日战役期间,我在抗日根据地提出了申请,并通过县政府的讯断,办理了这个问题。条件是我将家产的继续权转交给对方。这样,当我父母去世后,我便没有了家可归,也没有了亲人可探望。我幼年时成长的家乡和房舍,如今只能在梦中怀念了。
下面我来重新先容我两位叔叔、姑母和家人的情形。三伯父以他开阔的肚量胸襟和开放的品质有名,他在岢岚城内开设了一个多样化的商店,那里不仅有各种杂货,还售卖当地特色商品。此外,他还购买了三顷位于岢岚的林地。当时每亩地的价格只有几块钱。这些林地原来是山坡上的天然林区,经由砍伐和烧荒后,被用来栽种莜麦。但每亩地皮的产量并不高,只有几十斤的收成。因此,这种地皮的租金并不高。五台山也曾是茂密的森林,但后来也采取了类似的开拓办法,栽种莜麦和土豆。对付中国本日森林覆盖面积减少的问题,历史上毁林开荒的做法有很大关系。在旧社会,由于五台东冶镇一带缺少耕地,许多男人选择离开家乡去外地谋生,有的去了内蒙,有的去了阜平,还有的留在了岢岚山上。三伯父便是一贯在岢岚生活并经营他的买卖,但不幸的是,他在1926年病逝于岢岚。此外,我还想提及我的姑母以及其他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生活和经历,虽然详细情形我没有详细理解,但我知道他们都在为生活努力奋斗。
四叔父与祖母一贯住在一起,他是一位做生意的人,在岢岚有他的商铺。他还曾两次卖力税收的管理事情。1938年我曾去岢岚,那时四叔住在离城较远的村落庄的窑洞中。我们曾经见过一次面,他那时很沉迷于鸦片,喜好吃美味的食品。在战役期间,他不幸去世了。我的姑母一贯照顾着祖母,她由于从前失落去了丈夫,以是一贯吃斋念佛。她有三个儿子,与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个中大表兄已经早逝,三表兄在解放后也离世了。而二表兄白迁英在解放后搬到了新疆和西安,与他的女儿白宝文一起生活了很永劫光。他曾多次来北京居住,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去世了。
我家有八位堂兄弟,老大赵宝昌在太原的尊生恒中药店事情,他性情虔诚诚笃,很受大家喜好和尊敬。他曾经从太原带回一只美国桔子给我们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桔子。大约在1924年冬天,他在五台山收购药材时因病去世了。老二是赵福昌,现在八十多岁,住在兰州。年轻时他在北京万盛窑厂做学徒,后来在山西包过工程,并在太原开了一家服装店叫华洋服装行。他曾经来我读书的地方,为我做了制服,后来还成为了阎锡山军鞋厂的一个科长。三哥是赵寿昌,他是我们伯父的独生子,之前已经先容过了。四哥是赵安昌,也便是我的亲哥哥。他只读了四年书就去做学徒了,之后也在不同地方担当过银行和司帐的职位。因他提出哀求增加副食补贴被银行革职。他在解放后去煤矿事情,对我尽了一份任务。我哥哥虽然从小离开家做学徒,但他也赚了钱给家里。我则由于读书多,花家里的钱也多。以是我对他的遗孀和孩子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接管革命思想后,常常和我哥哥分享我的意见,他也附和我的不雅观点。他也提醒我要小心,由于如果有人知道了我的思想,可能会误以为我是共产党人。我感到自己是家里最幸福的孩子之一。
五哥名叫贵昌,他的字是子和。他是三叔的第三个孩子。他完成了沱阳高小的学业后,在山西省银行找到了事情,后来在山西铁道银行成立时,还担当了该行的司帐股长。抗战开始后,他在多个地方经营商店,终极到了台湾。不幸的是,由于商业失落败,他选择了投海自尽。我读书时,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五哥都给予了我经济支持,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我在家中的排行是第六。七弟叫美昌,他是四叔的儿子。我和他在河边川中学时是同学,但他比我低一年级。在抗战期间,七弟不幸去世了。八弟广昌是三叔的第四个孩子,后来被过继给了我伯父。他小时候患了高烧病,留下了后遗症,导致精神不正常。不久后,在解放不久后他也去世了。这便是关于我几位兄弟的大略先容,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和命运。
我的大姐,也是我们家族中的长女。二姐是伯伯的大女儿,三姐是四叔的第一个女儿,四姐则是伯伯的次女。而我的亲生二姐则是我常称的六姐,但我们都更习气地叫她二姐。这样算下来,我有两位二姐。除此之外,我还有五位姐姐,个中七姐是四叔的另一个女儿。以上提到的七位姐姐中,只有三姐仍旧在屯子生活着,别的的都已经不在世了。
【赵继昌,山西五台人。清华大学求学。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平山县县长,晋察冀五专署、晋察冀边区政府秘书主任,华北联合大学教诲学院副院长,晋察冀边区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华北贸易总公司大连办事处主任,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秦皇岛分局局长。建国后,历任中国入口公司、中国技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外贸组组长,对外贸易部办公厅副主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对外贸易部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经济日报社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