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李白那般洒脱浪漫,杜甫的诗总是那样沉郁抑扬,“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他的诗具有极强的传染力,读来总有种苍凉感,令人忍不住伤感。
但是就像洒脱的李白也有落寞之时,“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烦闷如杜甫也有欢畅之作。
公元763年,52岁的杜甫听闻了一个好,又哭又笑地写下了一首诗,被誉为“平生第一快诗”,千百年来传唱不衰,还入选了语文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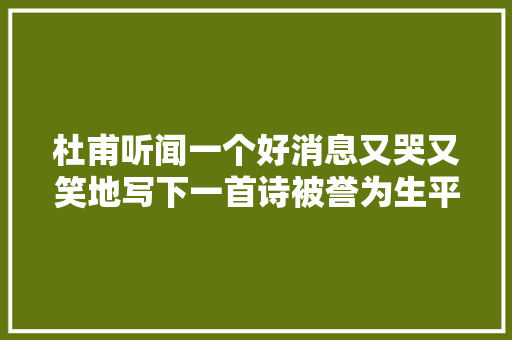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回籍。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迁移转变点,那是全体王朝的灾害,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无不遭受牵连。
战乱爆发时,杜甫回老家探亲,算是躲过一劫。
可是忧国忧民的杜甫眼见生灵涂炭,自是无法苟且偷安。
他听说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为皇后,便想前去投奔,可是半路却被乱军抓回长安,直到半年后才逃离敌营。
后来他前去投奔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
短暂的仕途生涯让他对朝廷失落望到了极点,不久,他就辞官而去。
他一起流落,几经周折,流亡到了成都。
在好友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建立了浣花草堂,这才安定下来。
在草堂的那段日子该当算是他平生最清闲安逸的光阴,“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附近水中鸥”。
可纵然生活安逸,他依然关心着天下苍生,以是当听闻唐军收复洛阳、郑州等地时,才会喜极而泣地写下这首惊艳了千年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诗歌首联写的便是他乍闻后的心情。
实在唐朝收复失落地本是在762年的冬季,可是古代没有互联网,而杜甫收到这个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
一个“忽”字表明了来得惊惶失措。
墨客多年流亡在外,便是由于“蓟北”被敌军盘踞,以是听闻这个后,他才会涕泗横流。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大概永久无法想象战役给公民带来的侵害是有多严重。
有家难回,有亲难见,乃至就像杜甫在《春望》中所言“家书抵万金”。
因而杜甫的“涕泪满衣裳”也是情有可原了,他终于可以回到家乡,他等这一天真的是等了太久了。
颔联写的是他转悲为喜的心情。
不是他感情善变,而是这本便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对付唐王朝来说,收复失落地,平定叛乱,意味着皇室皇权、朝廷地位的规复;而对付庶民百姓来说,战乱的结束,代表着新生活的开始。
无论哪点对付忧国忧民的杜甫来说都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以是他才会卷起诗书,手舞足蹈。
颈联连续刻画他的喜悦之情。
就像李白当年得到唐玄宗召见时,“高歌取醉欲自慰”,杜甫此时也是放声高歌,开怀畅饮,这在杜甫忧郁的生平中也是难得一见了。
这里的“青春”当然不是指我们现在的少年青春,而是解释媚的春光。
杜甫已经操持着在这鸟语花香的时令里,和妻儿一起返乡了。
末了的尾联便是他想象返乡的情景。
杜甫也真是敢想,从成都到洛阳,千里迢迢,我们如今飞机动车自是可以几小时就到达。
可古代山高路远,当年魏万追踪李白,从王屋到扬州3000里,足足追了半年才遇上。
而杜甫这里仅用几个字,“从”“穿”“下”“向”,将这千里迢迢的路程轻松地串联起来,一个个连忙飞驰地画面一闪而过,将墨客那种返乡的急迫和喜悦之情写到了极致。
全文感情热烈旷达,畅快淋漓地表现了墨客忽闻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就像明代王嗣奭所言:此诗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跃。
如此豪放的情绪,难怪都说这是杜甫的“平生第一快诗”。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