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上的笔墨组合成篇时,有横排与竖排两种形式。决定笔墨排列横与竖的基本成分,在于笔墨的书写方法。
汉字中夹杂的英文
中国古代是在竹简上写字
古人之以是竖着写,是由于在造纸术发明以前,古人是在竹木简牍上写字的。竹木简牍都是窄长的竹木片,用绳串起来可卷成册。“册”字便是简牍的象形字,而打开卷册自然是右手执端,左手展开方便。以是,书写也便是自上而下,从右往左了。古时竹简的书写,是一片片单片写好后再装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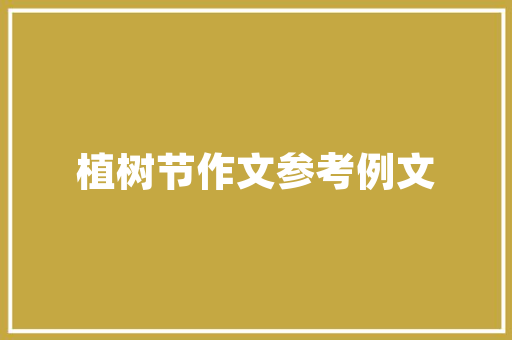
注:以上效果图仅供参考
从汉字的特点和人的生理习气来看,一个字的笔顺自然是从上至下来、从左到右方便。如果从右往左横写,写左半部时,羊毫势必挡住右半字形,不便于安排构造,影响结字的都雅。而每个汉字的末笔都是在中下或右下,写完上一字的末笔紧接着写下一字的起笔,竖式书写比横式书写更便于笔势的连贯。
古人以右为尊,汉字书写的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也反响了古人的尊卑思想。古代,上为君,为父母;下为臣,为子女。右为大,左为小,“无出其右”便是没有超过的意思。
而泰西的拉丁化字母是从左向右书写,因而由拉丁字母排成的洋文书都是横排。“洋文码子”不能以码成义,要两个以上的字母拼成词组,而竖行洋文则无法拼词。由于洋码不能竖排,在竖排版的中文书中涌现拉丁字母时,也要让其横向卧倒,否则洋文就无法与汉字“兼容”。汉字可以独立成义,因此可以横竖任意排列。横排时也能适应从左向右或自右而左的两种不同方向的顺序。
图为张旭草书《古诗四帖》
汉字的书写是自上而下、由左至右的顺序。大部分汉字的扫尾,在字的正下方和右下方。因此,汉字书写,尤其是书法的书写最适宜竖行进行。这样才最为流畅连贯,易成“行气”。尤以行草书为甚。
决定汉字竖行书写的另一个缘故原由,在于最初的书写条件。竖写的简册在阅读时要横向展开,简册的两端执于读者的旁边手中;如在简条上横书,简册一定横读。阅读时简册高下展开,读者的双手要一上一下执握简册,这样悖于生理,十分不便。其余,古时无桌,不作大幅,多以尺牍。书写时,左手执牍,右手作书,相得益彰;如将牍本横执横书,在羊毫书写的压力下,左手难于保持牍本的平衡与稳定,一定书写困难,其状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汉字的构造与最初的书写条件是汉字竖行书写的成因,竖行书写又决定了出版物与印刷品的竖式排版形式。
《韭花帖》
历史一直发展,科技不断进步。先后发明了纸张,有了桌椅等方便的书写条件。然而,习气的力量是巨大的。古今文人并未因此将笔墨改为横书,笔墨的利用、出版印刷也依然竖排。这种情形一贯坚持到上世纪的五十年代。
陈嘉庚书法
1950年6月,陈嘉庚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交了“中文从左向右横写”的提案,这个提案受到了相称的重视。之后,郭沫若、胡愈之等文化名人也撰文支持。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首次改为横排版。并在当年,中心级的17种报纸中有13种改为横排。1956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公民日报》也改为横排。自此全国报刊纷纭效仿,图书出版也顺流而动。
左为《光明日报》1954年版,右为1955年版
推广汉字横书横排,自然要有其理论根据。当时提出的情由有三:
1.人的眼晴是横的,视线范围横比竖宽。当时有人搞了一个实验,证明横读的速率是竖读的1.345倍;
2.各种数理化公式、外文语句、外国人名和地名排写方便;
3.可以提高纸张的利用率。实在这个情由并不成立,由于决定纸张利用率和阅读舒适度的紧张缘故原由是每行字的是非,而不是排版的方向。
进入当代社会后,方便实用的硬笔成了紧张的书写工具。羊毫书写的实用性大大降落。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决定汉字横书的紧张成分。在同样利用汉字的日本,笔墨的书写与出版,以竖式为主,横式为辅。小学生的教材都是竖式排印的。日今年夜众依然保持着竖式用字的习气。
西周晚期涌现过从左往右的青铜器铭文,如上图《汤叔盘》
中国汉字从有甲骨文至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险些都是竖式利用(偶有从左往右也是由于器物的限定),横式不敷60年;日本人至今竖式用字,因此不能解释汉字的利用横式优于竖式。近年来,有呼声哀求汉字用简识繁和废简复繁。我想,这恐怕不是大略的汉字利用方便与否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的哀求。
《日本经济新闻》2017.12.5版
为理解决阅读舒适度并提高纸张利用率,每行竖排的字数均在12字旁边。由此看来,竖排与横排的效果相同,横排并不比竖排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