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是讲究平仄押韵的,可在日常阅读时,常常会创造有些诗句,读起来并不押韵。比如:杜牧《山行》“远山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中“斜”字。
时下不少“国学”遍及者都对粤语非常推崇,认为这才是中华正音,是保存了最多古音的汉语方言,乃至还有人提出必须用粤语来读古诗才精确。
不少正在学诗的同学和家长在看到很多这种不雅观点的视频和文章后,都开始纠正自己的古诗诵读,那么这种做法究竟对不对呢?
本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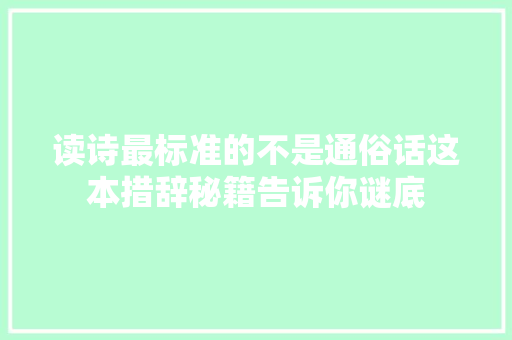
古诗粤语话标准吗?
对付读古诗是否该当用粤语,作者在本书第二部分《方言与古汉语》中的《粤语真的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吗》一文中进行了辨析。
作者的入手点是历史。粤语所在的岭南地区自古便是“天南蛮荒之地”,土著措辞与中原语音基本没有关联。中原措辞(也便是后来的“汉语”)大规模的进入始于秦代南征的赵佗。
此后,中原措辞在岭南的利用也仅限于番禺(今广州)等中央城市,而周围大量的地区都为俚人和僚人所霸占,他们说的仍旧是当地的土话侗台语——也便是“越”语。“此时的岭南和当时的朝鲜、越南北部颇为类似,城市中的中原移民讲汉语,而人口霸占绝对上风的土著居民则在受到汉语影响的同时仍旧利用本土措辞交际。”因此,“这种由秦朝移民带入两广的汉语,也确实并非当今粤语的先人。”
我们知道,秦代的中原语应属上古汉语语音系统。从作者的这一论断可知,现在的粤语该当很少上古汉语语音的影响。以是,那种必须用粤语读《诗经》才是正宗的说法就已经不攻自破了——由于,《诗经》用的正是所谓的上古汉语语音系统。
从笔墨入手
理解更多“其它”知识
一个普通字音,竟然能够串联起了中国的古代史。书中每篇关于措辞的文章,都包含着很多有趣的内容。比如为什么相声里的白要念成“bo”、为什么天津和北京间隔那么近,可措辞却和南方更附近,类似例子还有很多。而我们也可以从措辞学的角度,推导出自己生活圈子里的一些故事。说文不仅是解字,也是解读历史。
单以《“抗日神剧”里,日军说话为什么总是那么怪》看,里面就涉及了日语、上海话、“克里奥尔语”三种措辞,为了搞明白内容在说什么,可能须要大略理解日语的语法构造、上海话的发音和“克里奥尔语”背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