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屯子生活经历或者在屯子终年夜,是体会不到这种环境的;有屯子生活经历或者在屯子终年夜,也不一定会有这种体验。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经济捉襟见肘的年代,统统有用的物品,都是稀缺资源,比如粪。
口语诗《捡猪粪》(作者钟海洋)就记述了这样一个生活的小片段。
全诗十一行四十来字,“儿时/天刚蒙蒙亮/兄弟俩/就去捡猪粪”,韶光很清晰:儿时,这是大背景;天刚蒙蒙亮,这是详细所指。我猜想作者该当是1980年代或之前所生(后来看到,作者出生于1965年),那时,猪粪也是生产资料,捡回来,便是沃田肥土的好东西,不捡,便是摧残浪费蹂躏,可惜。
我没有过捡粪的经历,虽然比作者出生的韶光没有晚多少,但一则家里养了猪,猪粪便是自家的肥料;二则父亲在县城的中学上班,学校的几个厕所中的粪尿,都可以去挑;三则刚地皮承包那会,几户人家还合资分到一头牛(我读高三时还放过年),轮到谁家放牛,牛栏里的牛粪就归谁家所有。如果非要说捡过粪,那也是很少有的几次,比如在房前屋后种树的时候,附近恰好有猪狗羊屎,会顺手划拉到树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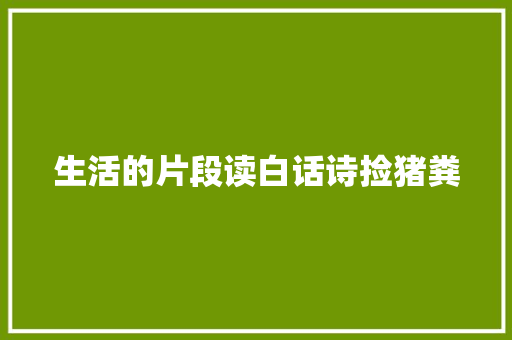
为什么“天刚蒙蒙亮”就要去捡呢?由于捡粪的人太多了,你起来晚了,可能就被别人捡走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便是这个道理。我们乡下有句俚语:想捡钱也要起得早。专门针对那些
“本村落捡不到/就到邻村落捡”,为什么本村落捡不到?由于还有人比兄弟俩起得早,或者本村落是个小村落,人口不多,地盘不大,那就只有到邻村落想办法了。
“碰着驱逐者/兄弟俩/在猪圈外/背靠背/战斗”。这切实其实是影视作品中的经典一幕。肥水不流外人田,同样,我村落庄里的东西,别村落的人也没想问鼎,以是在捡猪粪的时候,难免会被人驱逐,叫他们离开。驱逐的办法有多种,比如,口头呵斥,放肆狗吠、追或咬,直接操家伙驱赶。这时候,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两个就只能同仇敌忾,互为依赖,相互干照了。
小时候,我弟弟就喜好粘着我,我到哪,他跟到哪,彷佛是甩不掉的尾巴。我们曾一起去山里找打柴的父母,差点找不到回家的路,是一个认识我父母的公社干部看到后,把我们送回家的;我曾经掉到井里差点淹去世,是弟弟年夜声叫喊喊来一个更大的孩子把我救起;我也曾经大胆地扑打追向我弟弟的大鹅......
为什么会叫孩子去捡猪粪而不是大人去?穷汉的孩子早当家,父母做更重的农活,捡粪一类轻活,那便是孩子的事情了。学龄前,我和弟弟就开始放牛,多少可以减轻一些父母的包袱,也是属于这一类环境。
当然,我小的时候,猪都是在猪圈里养着的,很少能在表面见到猪(除非是赶远路去配种的种猪),而四处流窜的狗却很常见,以是村落庄里有些老人虽然也捡粪,但基本是捡狗屎,而且狗屎还远比猪粪要肥。或许,所谓的“狗屎运”,也便是这样来的吧。
巧的是,我曾经也写过捡粪题材的短诗:
天刚放亮
火根老汉就提着撮箕
在村落庄周边
捡起了狗屎
顺带捡一捡
豆豉状的羊屎
如果能碰着一堆牛粪
他眼中一定会冒出
自留地里青菜一样
鲜嫩的绿光
(2021.02.06《捡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