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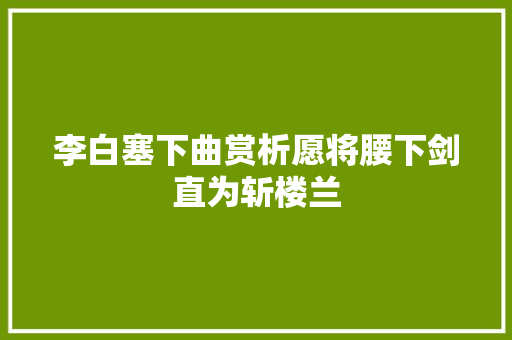
译文
五月的天山仍是大雪纷飞,只有凛冽的寒风,根本看不见盛放的鲜花。
听到有人用笛子演奏《折柳曲》,想着家乡已是春色满园,而在这里,还未曾见到春色。
白天在金鼓声中与仇敌进行殊死的战斗,晚上枕着马鞍睡觉。
但愿能够发挥自己的本领,早日平定边陲,为国立功。
赏析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起首四句是说,五月的天山仍是满山飘雪,只有凛冽的寒气,根本没有花草。只有在笛声《折杨柳》曲中才能想到春光,而现实中从来就没有见过春天。
起从“天山雪”开始,点明“塞下”,极写边地苦寒。“五月”在内地属盛暑,而天山尚有雪。但这里的雪不是飞雪,而是积雪。虽然没有满空飘舞的的雪花(“无花”),却只觉寒气逼人。仲夏五月“无花”尚且如此,别的三季(尤其冬季)的寒冷就可想而知了。以是这两句是举轻而见重,举隅而反三,语淡意浑。同时,“无花”二字双关不见花开之意,这层意思紧启第三句“笛中闻折柳”。“折柳”即《折杨柳》曲的省称。这句表面看是写各处闻笛,实际话外有音,意谓面前无柳可折,“折柳”之事只能于“笛中闻”。花明柳暗是春色的表征,“无花”兼无柳,也便是“春色未曾看”了。这四句一脉贯通,一气直下,措语天然,不拘格律如古诗之开篇,古人未具此格。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这两句是说,战士们白天在金鼓声中与仇敌进行殊死的战斗,晚上却是抱着马鞍睡觉。
五、六句紧承前意,既写军旅生活的紧张。古代行军鸣金击鼓,以整洁步伐,节制进退。写出“金鼓”,则陪衬出紧张气氛,军纪严明可知。只言“晓战”,则整日之行军、战斗俱在不言之中。晚上只能抱着马鞍打盹儿,更见军中生活之紧张。本来,宵眠枕玉鞍大概更符合军中的生活习气,不言“枕”而言“抱”,一字之易,紧张状态尤为突出,彷佛一当报警,“抱鞍”者更能翻身上马,奋勇出击。此两句则就一“晓”一“宵”写来,并不铺叙整日生活,概括性也强。全篇只此两句为难刁难仗,严肃的形式与严明的内容合营,增强了表达效果。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末两句是说,但愿腰间悬挂的宝剑能够早日平定边陲,为国立功。以上六句全写边陲生活的艰巨,若有怨思,末两句却急作转语,音情突变。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西域国名)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叮嘱消磨出使西域,计斩楼兰王,为国立功。此诗末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愿”字与“直为”,语气斩钉截铁,慨当以慷,足以振起全篇。这是此诗点睛结穴之处。
本诗的结尾雄壮有力,与前面六句的陪衬之功是分不开的。没有那样一个艰巨的背景,则不敷以显示如此卓绝的精神。此诗以是极苍凉而极雄壮,意境浑成,是由于有了前六句的铺垫。如果一开口就豪言壮语,转觉无力。这写法与“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二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诗不但篇法独造,对仗也不拘常格,自是五律别调佳作转载于古诗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