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在政治上,他领导了庆历改造,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在文学上,其散文、诗、词创作皆有独特造诣,开拓了崭新的审美境界。更让后世文人推崇的,仍是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殷殷君民之念。
青年期间的范仲淹与齐州还有一段渊源,他曾在当时齐州境内的长白山醴泉寺(寺原归济南章丘,后划归滨州邹平)苦读数年,著名的划粥断齑和窖藏金银的故事传说均是发生在这一期间。这段读书经历为范仲淹日后为官、为文生涯奠定了丰硕的文化积累。
范公祠门口今900多岁树龄的古槐 本版照片均由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徐敏 摄
醴泉寺内的范文正公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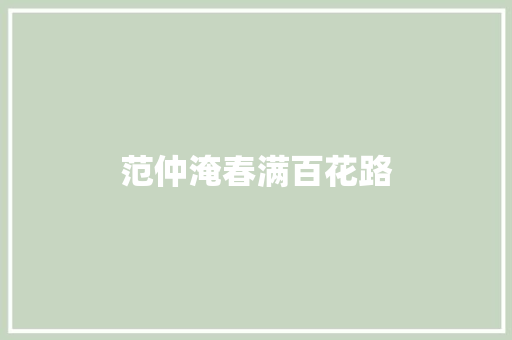
曾在齐州古寺苦读数年
清朝初年,墨客王士祯到长白山醴泉寺寻访,作诗《阻雨望醴泉寺用徐昌谷韵》,个中有句云:“渺渺青山路,苍苍修竹林。法云悬瀑影,幽鸟乱泉音。”如此看来,王士祯看到的醴泉寺位于青山茂林之中,泉声、鸟鸣之声交错其间,清雅秀美。
再往前追溯,王士祯到访醴泉寺之前近四百年,元朝淄川(今山东淄博)文人杨弘道也曾到此寻访“贤相读书处”,作《醴泉寺诗》。他看到的景致是:“老柏参天色,流泉直殿回。树从何代有,水自上方来。”寺中的古树不知道历经由多少年的沧桑,泉水从山岩中汩汩而出流至地面。
醴泉寺相传为一名叫庄严法师的僧人所建,原名龙台寺,始建于南北朝期间,后因年久失落修而废弃。唐中宗时,寺僧道寂重修寺院,唐中宗给寺院东山岩中的一处泉水赐名为醴泉,醴泉名列“济南七十二名泉”。这座寺院坐南朝北,群山环抱,后来因范仲淹曾经在此读书而名声大噪,上千年来不断有文人墨客前来寻古访幽。
比起历史上一度喷鼻香火壮盛的期间,本日的醴泉寺更加宁静生僻。从济南市章丘区东行进入滨州市邹平市境内,穿过一条人群相继而来的商业街市,面前豁然涌现庄严典雅的醴泉寺正门。寺院背靠绵延巍峨的群山,上有灰白色的云从山巅之上穿过,北望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这些都让醴泉寺平添几分来自历史深处的古意。寺中有一口古钟,听说敲击之声可以响彻数里。除了大雄宝殿之外,寺中最主要的建筑便是范公祠,时常会有游客来此拜访,听一段范仲淹的往事。若是讯问看守寺院的老人去哪里寻访醴泉,老人会奉告,早已掩埋在后山的荒烟蔓草之中不知所在了。
即便如今的醴泉寺是21世纪重修的建筑群,即便醴泉早已无迹可寻,范仲淹曾经在此用功苦读的经历却始终是历史的真实。
端拱二年(989),范仲淹出生在徐州的官舍。这时,他的父亲范墉在徐州任武宁军节度掌布告,范仲淹是家中最小的儿子。范家原籍河北,后迁往江南定居苏州,有祖茔在苏州天平山。范仲淹出生仅两年后父亲病逝于徐州,后来归葬苏州。此时其母谢氏还非常年轻,又再醮一名叫朱文瀚的低级官员,他也改名为朱说。朱文瀚在不少地方担当过职位比较低的地方官,范仲淹也和母亲随着他辗转各地,个中有一段韶光就在长白山醴泉寺。
宋真宗景德(1004-1007)初年,朱文瀚任淄州(今山东淄博)长史,范仲淹也随同来到这里,就读于长白山醴泉寺。据《济南通史·宋金元卷》载,这一期间齐州是这一带的学术活动中央,以齐州为联枢,东百余里到章丘、邹平一带,南约百里到泰山,西至郓州(今山东东平),北则延至滨州一带,学风十分浓厚。朱家家境并不富余,十几岁的范仲淹在这里用功苦读,别无旁骛。史料记载,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罢参知政事,出为邠州(今陕西彬州市)太守时跟朋侪讲起过这段往事。他与一名刘姓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两升粟米粥,粥冷之后切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为了让粥的味道不至于太过寡淡,他们把蔬菜切碎后加半杯醋和少许盐,烧熟后当菜食用。这样的苦读生活过了三年,后世称之为“划粥断齑”。
还有一个故事反响了范仲淹当时存心苦读的场景。听说某天一只黄鼠狼偷走粥块藏入洞穴中,范仲淹饥饿之时遍寻,在洞穴中找到了粥块,并且还创造有一大罐金银藏在穴内。此后,他连续一如既往过着食用粥块刻苦读书的寒士生活,视洞穴内金银如无物,也未对人讲起。后来范仲淹为官,醴泉寺僧人上京请他帮助维修寺院时,他才把醴泉寺窖藏金银的事情见告寺内僧人。这个故事未必真实可信,但是年少期间的范仲淹甘于贫穷、专心苦读确是事实。
曾经做过枢密副使的淄州人姜遵对青年范仲淹十分赏识。姜遵为谏议大夫时曾回家乡,范仲淹和一些青年学生去拜见他。告别之时,姜遵单独留下范仲淹并把他先容给夫人,说他年纪虽轻却是个奇士,将来不仅会成为显宦,还将立盛名。姜遵是一名有才能的官员,这个故事解释他看出青年范仲淹才华轶群、志向远大的气质。
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载了范仲淹这样一则逸事。晚年范仲淹知青州时,西望仅百余里之遥的淄州故居作诗《留别长白山父老》:
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余。百花春满路,二麦雨随车。
鼓吹迎前道,烟霞指旧庐。村落夫莫相羡,教子读诗书。
在这首诗中,范仲淹深情回忆起当年在卑微寒苦中读书的场景,对旧居和故人充满了温情的回顾。那是百花盛开的春天,雨水随着车马行进,滋润津润着麦田。他看到乡亲们激情亲切地前来欢迎他,也看到了烟霞中的旧居。不过,这首诗的目的还是劝勉乡亲父老要“教子读诗书”,疏导青少年要树立读书做官的志向。范仲淹本人也曾经出任教职,以阐明儒术为己任,终生不忘讲学以培养奖掖士子。盛行于泰山地区的泰山学派的创始人孙复和石介均曾经受业于范仲淹门下。
范仲淹中进士为官后呈请规复旧姓,更朱说之名为范仲淹。后来,长白山的这名寒儒经由数十年的官场风波之后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千古之音。
次子范纯仁出任齐州知州
范仲淹次子范纯仁与齐州也有一段渊源。就在范仲淹长白山苦读近八十年后,范纯仁于元丰四年(1081)年调至齐州担当知州,这段任期约两年。
范纯仁(1027-1101),北宋名臣,朴实清廉,人称“布衣宰相”。他脾气夷易宽简,为官夷易宽厚,对百姓中罪过较轻者主见采取怀柔感化的政策。范纯仁担当齐州知州时,当地民风一度甚为凶悍,百姓动辄沦为盗贼,官府严加缉拿惩办,以至于监狱人满为患。范纯仁理解情形后才知道,个中很多人不应当监禁,但是官吏担心放他们出去会再次危害百姓,索性将其囚禁,待其生病去世于狱中,也算是“为民除害”。《宋史·范纯仁传》载,范纯仁听闻后十分愤怒:“法不至去世,以情杀之,岂理也邪?”于是命人将狱中之人带到堂下加以训导,见告他们如果改过悛改的话可以重新回到社会上生活。有人担心,对这些人严厉打击恐怕都不能阻挡其违法,公然开释可能更无济于事。范纯仁说:“宽出于性,若强以猛,则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后来的事实验证了范纯仁的做法,不到一年,齐州的犯法者比常年减半。
在齐州的治州之术解释,范纯仁重视对百姓的教养,认为礼仪教养赛过严刑惩处。
即便也有不少诗作传世,不过范纯仁更主要的身份是政治家,因此他在齐州期间的文学活动不多,访问历城人张掞的读书堂算是一次。张掞是与范仲淹同期间的名臣,晚年曾经隐居在王舍人读书,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行经齐州时,曾给张掞故居题字“读书堂”。在齐州任职期间,范纯仁曾拜访此处,作诗《张掞侍郎读书堂》:三纪仁皇侍从臣,当时文学动簪绅。高明已入儒林传,旧室长存历水滨。岘首空留王粲宅,喷鼻香山犹识白公真。他年遗迹应无废,不坠诗书世有人。
从诗作中可以看出,张掞深受天子倚重,在文坛上也颇有名声。张掞在齐州的故宅仍在,追古思今,范纯仁感慨王粲在岘首山的故居和因白居易而有名的喷鼻香山寺,认为只要继承诗书传家的传统,张掞故宅可以世代保留下去。
齐州任职期间,范纯仁还曾与同寅前去龙洞游览,参拜顺应侯祠,并在独秀峰石壁上刻字记录了此行。至今虽历经千年,石壁上的刻字仍旧依稀可辨。题刻内容是:元丰辛酉(1081)四月二旬日,朝散大夫、直集贤院、知齐州范纯仁,朝请大夫、通判州事吕邱孝修同谒顺应侯祠;朝奉郎张起,权齐淄二州都巡检康诩,承事郎、知历城县赵齐贤,不雅观察支使孙述,前颍州团练推官李坚,历城县尉李景隆从至。
顺应侯是宋神宗给龙洞的龙神的封号,由于龙神总是应百姓所求,及时降雨。范纯仁此行来到龙洞拜会顺应侯祠,很可能是农历四月碰着干旱,以是带着部属和同寅来此求雨。
就这件小事来看,担当地方官时,范纯仁对地方百姓也是一片羞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