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也是古老的鸣虫,俗称知了。汪曾祺在《夏天的昆虫》中说:“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嘟溜——一嘟溜——一嘟溜’,一种叫‘叽溜’,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他说,“蝉喜好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画‘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
当然,蝉于扬州人来说,它不仅属于画家,更属于孩子,没有捉知了的童年就算不得一个有意见意义的童年,没有捉知了图景的夏天,就彷佛不是一个完全的夏天。捕蝉之乐,古来有之,《庄子·达生》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曲背老人捕蝉技艺值得一说,更值得想象的还有捕获之蝉会给他的孙儿带来什么样的快乐。韦明铧在一篇描写扬州人的闲适生活的文章中说道,“至迟在唐代,蝉已被笼养。”《扬州画舫录》也记录了这样的场景:“堤上多蝉,早秋噪起,不闻人语。长竿粘落,贮以竹筐,沿堤货之,以供儿童嬉戏,谓之‘青林乐’。”这记述的是大虹桥边长堤柳阴中的事情。亲手捕蝉,是很多作家回味童年生活时最饶有滋味的事情。汪曾祺说:“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竿——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瞥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粘。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
在历史中,蝉也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形象涌如今一些文学作品中。对付蝉的象征意味的吟咏,以唐代最盛,《全唐诗》共录咏蝉诗六十余首,而且风采互异,蝉的艺术形象前后有很大不同。有以蝉颂扬高洁的,有以蝉表达哀求鸣响、希冀奋飞的,也有对蝉寄托乡思、感怀别离的,更有借蝉讽刺趋炎附势的。不过,在咏蝉诗中,虞世南的《蝉》诗最为人推崇:“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年夜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由于,清高、自重、风雅是更多的人借蝉诉说的空想情怀。扬州古代墓葬中以玉蝉作陪葬,便是蝉的高洁文化象征的例子。
无论是生活意见意义还是文化象征,蝉对付扬州人来说,它最大的代价该当是清幽境界的诗意再现。在扬州诗词中,我们总能在蝉鸣阵阵中直抵幽境。“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杜牧眼中的禅智寺是幽深的,蝉的躁动衬托出来的寂静,虽说不乏他为出路和人间的黯然神伤,但谁能不在这样的画面里感想熏染到禅智寺一草一木的清与静呢?清代文学家厉鹗,在寓居扬州时游历不少名园别馆胜地,他被平山堂的蝉声“召唤”而《登平山堂》:“落日堪销暑,疏蝉唤客游。析酲尝蜀井,过眼叹迷楼。天净山容出,堂空树影浮。昔贤遗胜地,抚槛小迟留。”仿佛蝉声逼退了夏阳,仿佛蝉声澄净了天容。昔贤遗胜地——平山堂便在这澄净中风骚突显。厉鹗笔下的寂静地还有筱园,“水亭布砚席,初蝉流碧树。菰芦积无边,不辨来时路。”他雨中过筱园时,被流碧一树的蝉声打动。筱园,是1716年清墨客程梦星在扬州所筑的园子。“筱园”即“小园”,在扬州著名风景区廿四桥旁,这里原来是当地人种芍药的地方,程梦星买下后重新构筑,使它焕然一新。筱园建好往后,成为天下文人汇合之地。不仅厉鹗来过,听过这里的蝉声,钱塘人陈章侨寓扬州时也来过,同样也对筱园的蝉声与清幽留下永久的存照:“溪流凡几湾,荷叶欲无路。撑艇到篱门,一蝉吟碧树。”扬州园林多宁静,在乾隆五十一年举人蕲州知州徐鑅庆的诗中,九峰园也是听蝉妙处:“寓园最萧爽,池馆晚开筵。云起九峰暗,花迷夹岸连。长廊飞水鸟,高树响风蝉……”只可惜,蝉声依稀,荷花池畔的九峰园已不见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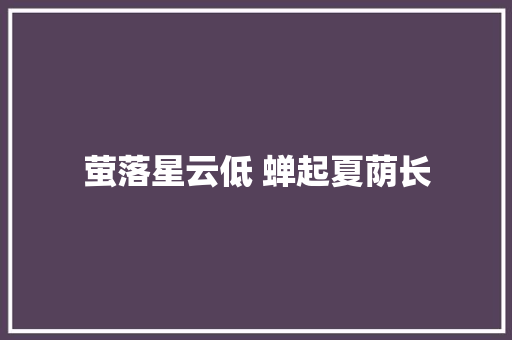
萤映照隋都兴亡事
盛夏最有兴味的图景中肯定有一幅流萤图。厉鹗与朋侪程友声红桥夏夜泛舟时,见到这样的夜景:“月黑水深荷叶路,凉萤无数绕船飞。”乾隆年间国子监博士金兆燕在扬期间,也记录下了红桥边萤火朦胧的情景:“水花凉夜销喷鼻香梦,绕汀画船齐泊……认隔浦渔灯,柳丝笼约。却是流萤,曲廊深处点轻箔……”萤火点点,点缀着红桥的诗意,也引燃了扬州夏夜的浪漫。提及流萤带来的浪漫,人们最先记起的一定是“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句子。然而,要说到扑流萤的生动细节,还要看康熙年间江南华亭人钱芳标在扬州留下的《水龙吟》词句:“薄暮庭园无人,何来几点疏星坠。未烧兰焰,乍移桃簟,催将秋思。巧入低穿,银床渐冷,铜铺初闭。向画栏杆畔,齐纨试扑,忽又逐,墙阴起。飘落溪头山嘴。也多情,草黏花缀……”扬州人玩赏萤火虫可谓别具一格。《扬州画舫录》说:“北效多萤,土人制料丝灯,以线系之,于线孔中纳萤。其式方、圆、六角、八角,及画舫、宝塔之属,谓之‘萤火虫灯’。近多以蜡丸爇之,每晚揭竿首鬻卖,游人买作土宜。”用萤火虫做灯,扬州既有实例,看来今人对“囊萤映雪”作秀的揣测与真实与否的质疑,是没故意义的了。萤火虫还曾在扬州引发过一场空前绝后的浪漫。隋炀帝杨广曾搜聚萤火虫数斛,夜出游山时放之,光遍岩谷。为了看星云满地的奇景,他在扬州还专门建了一座放萤苑。
隋炀帝这一奇思妙想,其结果让扬州的萤火虫打上了一种盛衰、兴亡的标签。千百年来,扬州的萤火虫就一贯背负着历史的重荷,而有了别样的况味。杜牧的《扬州》诗中写道:“秋风放萤苑,春草斗鸡台。”李商隐的《隋宫》诗:“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更是成了千古名句。斗鸡台又称“吴公台”,是隋炀帝被杀后的葬身之处,而垂杨则是指当年隋炀帝开大运河栽柳树的事情。几百年后,清朝墨客程梦星经由雷塘的时候也借杨柳和萤火来总结隋亡的缘故原由:“东风杨柳吹线线,秋宵萤火来翩翩。”以扬州放萤苑来作感怀、凭吊和警示的诗词历代不断。
本日,历史的重负已在萤火虫身上淡化,但环保的诉求却呼唤萤火虫再次登场。
蟋蟀繁华之都存遗音
花鸟鱼虫,是中国文人之四大雅玩。而虫文化最主要确当数玩蟋蟀了。蟋蟀古称匆匆织,又叫蛩、蚟孙,俗称蛐蛐儿。因其善鸣且善斗,因而,玩养蟋蟀便成了上至皇家、文人士大夫,下至草根百姓都热爱的一项极具东方色彩的文化休闲活动。
在盛唐宫廷和民间都有玩赏的习俗,当时紧张是把它当鸣虫看待,《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提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大墨客杜甫、白居易等留下许多诗篇。到宋代斗蛩之戏开始盛行,苏轼、黄庭坚、佛印大师等文人雅士都是个中妙手,还留下许多识别蟋蟀利害的履历之谈。乾隆时的冯霅云更说蟋蟀有五德:“鸣不失落时,是其信也;遇敌必斗,是其勇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伤重致去世,是其忠也;败则不鸣,知耻辱也。”
有着深厚人文传统和经济根本的扬州,自然也是鸣虫文化繁盛之地。扬州斗蟋蟀俗称之为“斗虫”、“玩虫”,起于唐代,盛于明清两代,为全国“四大斗虫盛区”之一。《扬州画舫录》记载了一个名叫鸣秋的扬州人,精于鉴别蟋蟀,并能著书立说:“北郊蟋蟀,大于他处。土人有鸣秋者,善豢养,识草性,著《相虫谱》,题曰‘鸣氏纯雄’。秋以此技受知于歙人汪氏,遂致富。”可见扬州玩蟋蟀之风盛行。扬州人更善于斗蟋蟀,有人以此技为生。董伟业《扬州竹枝词》云:“蟋蟀势穷何处使?鹌鹑场上看输赢。”孔庆镕《扬州竹枝词》云:“蟋蟀声中夜点兵,上场嫡赌输赢。”扬州人称善斗的蟋蟀为“将军”。费轩《梦喷鼻香词》说:“扬州好,生小不知贫。盆买戗金笼蟋蟀,门摊锦袋斗鹌鹑。破产觅将军。”惺庵居士《望江南百调》说:“扬州好,蟋蟀斗纷繁。如虎几人夸异种,牵羊九日策奇勋。养活铁将军!
”
扬州出产的蟋蟀也很有名,其紧张产地一是邗江七里甸西的皇茶庵,出“油黄”;二是皇茶庵西边的悦来集以南,出“青虫”,又分为“白头”和“淡青”两种;还有江都嘶马镇以南,出“紫虫”,以“纯紫”为上品;市区内则产于东关街“化侪所”和“都地皮庙”后院的瓦砾堆中,其“与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斗”。旧时的扬州,赌斗蟋蟀多在地皮庙进行。一样平常先请好“领草”(裁判),将蟋蟀称好重量,按重量分级,用纸条标明重量加编号,并封好盆口,同时各交出一点钱,谓之“交彩”。接着,在街头巷尾贴出海报,上书“某某地秋虫可兴”,旁注韶光、地点、养秋虫者姓名等。赌斗时,由“领草”公证,双方各自确认投标数,浩瀚参不雅观者也可各认定一方,投标赌钱,以台上的胜负为输赢。斗虫结束,胜者鼓翅长鸣,谓之“上风”;败者屁滚尿流,谓之“下风”。
斗蟋蟀活动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扬州民间仍有虫师体味着玩赏争斗之虫意见意义。
蜻蜓、螽斯人间清欢留图画
“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鞲鹰逐兔,挈狗捉獾。”这是一幅旧时巨室子弟平凡声色图景。当然,听虫鸣不雅观虫趣绝不是巨室子弟的专利,听虫鸣也是扬州平凡人家夏日去暑养心的一件雅事。费轩的《梦喷鼻香词》可以佐证:“扬州好,夏日近薄暮。稌秫秸笼听纺绩,柏连喷鼻香爇辟蚊蝇。消得三两文。”稌秫秸笼里装的是纺织娘,它同另一种螽斯——蝈蝈,都是扬州人家窗前、案头的雅玩。蝈蝈叫声最久,可听一个长夏,秋冬喂养得宜也能闻其唧唧,螽斯可听,也可赏。扬州画家及工艺师们更是常将它们玲珑风雅的身姿留在图画里,留在工艺佳构中。
夏日的清玩雅物里,常入画家尺素的除了蝈蝈纺织娘,还有一种昆虫便是蜻蜓。扬州清末画家王素、陈康侯、吴让之等都曾以之为题材画过不少清新灵动的夏日清曲图。
扬州多荷塘,有荷塘则必有蜻蜓。扬州的蜻蜓有四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玄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革质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纲’。这家伙厉害得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嚓嚓地响。或捉之置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薄暮后目光就有点不济。他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玄色,我们叫这鬼蜻蜓,由于这有点鬼气,也叫‘寡妇’。”汪曾祺师长西席见到的蜻蜓扬州人一定都不陌生,扬州多水,河、塘交织的水网中也多荷花与菰蒲,盛夏荷影绿剑中怎少得了蜻蜓的身姿呢。“伶爪细腰肩舞纱,英姿交织混沌天。疏影清潭轻点水,更立剑尖若等闲。”这是元代画家王振鹏笔墨或者图画中的蜻蜓,更是交织在扬州人屋后窗前的光阴流影。李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