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话最早载录于《奉化县志》的媒介中。这部志书由舒津、陈著、任士林三位奉化籍乡贤同纂,前两位是南宋进士,第三位也学识过人,被称为“宋元间明州(宁波)五家”之一。十六七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苏东坡这句慨叹,先是惊喜万分,随即不免存疑,往后闲来读苏诗,竟意外创造,苏东坡笔下还有两首诗,涉及到浙东奉化溪口的雪窦山。
苏东坡之父苏洵,生前曾游庐山西南的滑腻调皮寺,还结识了几位僧友。多年后的1084年,已是誉满朝野的苏东坡登庐山,念想到父亲的这桩往事,他特地拜访滑腻调皮寺,并应寺僧之请写了一首《过滑腻调皮诗》。诗中就有“此生初饮庐山水,异日徒参雪窦禅”之句。1089年夏,在《再和并答杨次公》一诗中,苏东坡对雪窦云门宗“铁杆粉丝”杨杰居士欣然评价:“高怀却有云门兴,好句真传雪窦风。”
这两首诗,无疑是对“一声慨叹”最明朗的交代,最有力的支撑。至此,“苏东坡‘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恐为古人杜撰”之存疑,从我心头烟消云散,进而我还逐渐窥到“一声慨叹两首诗”产生的脉络和背景。
雪窦山在当时的有名高僧重显禅师方丈的阶段,是全国云门宗的传播中央。高僧重显俗姓李,禅宗五家之一云门宗四世法孙,今重庆潼南区人。他出身富豪之家,世代儒业相传。他最负盛名的经典之作《雪窦颂古》,不仅是禅法著作,也属于文学作品,几为北宋参禅士大夫大家都读的“脱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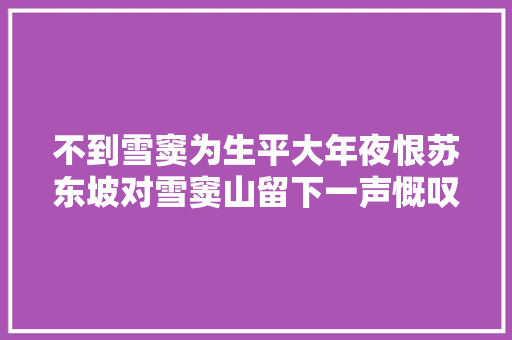
而苏东坡呢?正是北宋士大夫中参禅开悟最有造诣的代表人物之一。许多苏东坡的研究者都称:云门宗是苏东坡参禅过程中接管的紧张宗风,雪窦重显之作《雪窦颂古》,对苏东坡产生“直指心思”的积极影响。这是苏东坡为雪窦山留下“一声慨叹两首诗”的最直接缘故原由。
公元1052年,雪窦重显圆寂于雪窦山。这一年,苏东坡仅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他们在生前无缘谋面。如果说《雪窦颂古》是苏东坡精神上的良师良朋,那么,雪窦重显则是他意接而神交的心腹。入仕后,苏东坡对雪窦重显景仰有加,但此时人去山空。他对云门宗圣地雪窦山太神往了,却又身不能至。于是发出“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的慨叹,两度借诗挥洒,表达自己对雪窦难以放下的情愫。
多年来,对付苏东坡留给雪窦山的“一声慨叹两首诗”,我总抱着引以为荣的心态,一次次引入我的文章中,试图让文化大师为我故乡这座名山增色壮威。再看近几年的许多城市和旅游景区,纷纭推出的形象宣扬口号。它们多是四言两句,也有四言三句、四言四句的,句式整洁,文辞幽美,但有一个共同缺陷便是词汇雷同,人家不易记住。于是,“用一句话讲清爽”广告词成为新的趋向。比较成功的有普陀山——“想到了就去普陀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闪光点在于那个“想”字,一语双关,与“进喷鼻香”之“喷鼻香”谐音。还有杭州宋城——“给我一天,还你千年!
”等等。许多城市和景区,却是“古为今用”。例如,桂林之“桂林山水甲天下”,烟台蓬莱阁之“人间瑶池蓬莱阁”,等等,一经提及,认同感油然而生。溪口雪窦山的广告语呢,不是有现成的苏东坡慨叹——“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吗?
苏东坡已为杭州西湖和江西庐山这两大天下级游不雅观胜地,做了“绝版广告词”:“不识庐山真面孔,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们登临匡庐之前,谁不遐想到这句苏诗呢?“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抺总合适”,把西湖写得很真切的又是苏东坡!
至于“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凭借苏东坡强大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感召力,知者闻者定然会产生认同感。再试想,就连纵情山水、生平好游的苏东坡,也把未到雪窦而视为平生一个大遗憾,这等名山能引动多少人无限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