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环绕《史记》等中国古代文籍的26个谜题展开磋商,涉及历史事宜、历史人物、历史文献等多个方面。这些谜题包括了历史事宜的原形、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历史文献的真伪等,一贯以来都是历史领域的热点和难点。
本书中,作者不仅磋商史籍上写了什么,更磋商史籍为什么要这样写。喜好统不雅观正史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古人修撰史籍时的沉潜思考与微言大义,而喜好探索历史细节的人,或许也能在浩如烟海的文籍中,创造隐蔽在表层言语之下的丰富内涵。
>>内文选读:
鸿门宴的樊哙视角(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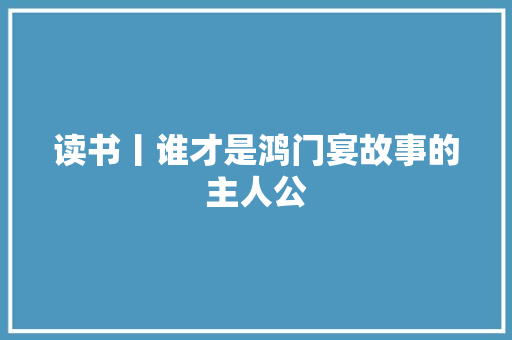
如果我们仅仅把鸿门宴的故事当成司马迁的“脑补”,仅从文学虚构的角度看《史记》里这类精彩的场景,恐怕有失落偏颇。司马迁对付著史的态度极其严谨,后世不清楚的细节,不虞味着司马迁没看到干系史料。那么,鸿门宴的现场感如此之高,司马迁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史学家李开元在《论〈史记〉叙事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他广和杨敞》一文中,曾经首创性地提到解读历史细节的一种思路。他在点评鸿门宴时樊哙的“精彩表现”时,就这样提到:“樊哙鸿门宴救驾的事情,是樊哙家子孙后代世世相传的光荣历史,司马迁以访问丰沛龙兴故地为契机,从樊他广处听到鸿门宴的详情叙事,后来,当他撰写《史记》的有关章节时,就将樊他广的口述作为主要史料。”
而史籍和小说一样,只要有人物和事宜,一定带有自己的叙事视角。绝大多数史籍的视角,都是全景式的,但在《史记》中,在一些浓墨重彩的篇章里,确实能看到类似个人视角的细节。比如,在《项羽本纪》中,对鸿门宴最具文学性的描述,则很像樊哙的视角。樊哙并非鸿门宴的主角,却占了不小的篇幅,他说的话竟然比刘邦、项羽还多。这便是叙事视角上的不同平凡之处,这类分外细节的背后,很可能隐蔽着历史写作的秘密。
鸿门宴是刘邦命运的迁移转变点。秦朝灭亡后,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刘邦比项羽更早进入咸阳,其部下曹无伤叛逃,向项羽密告,项羽便发兵刘邦,两人此时实力悬殊,刘邦只能只管即便避其锋芒。刘邦向项羽开释旗子暗记,表示自己并无攫取天下之意,项羽便摆下鸿门宴。这场酒宴既有庆贺灭秦之义,也有双方和谈之念,但亚父范增认为鸿门宴是项羽杀掉刘邦的好机会,而项羽迟迟下不了决心,终极让刘邦逃掉。樊哙是刘邦的同乡旧部,从前以屠狗为业,但在刘邦军中立下了诸多奇功,很多次攻城都能疾足先得,在勇武和忠实上,都被刘邦高度信赖。因此,把帮助刘邦解除困境的关键任务交给樊哙来做,也算通情达理。
《史记·项羽本纪》对鸿门宴的阐述首先是座席的安排:“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此时,樊哙并未登场,但他在后面登场时,很随意马虎进门后第一眼就看到项羽和项伯他们坐在朝东的位置。从后文的描写来看,樊哙的视角确实是先看到的项羽,并且“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樊哙登场,是由于酒宴上发生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事情,国人对这个故事很熟习,在此不再赘述。樊哙闯进来,要保护主公刘邦。他还未说话,项羽就看到这位彪形大汉,说道:“壮士,赐之卮酒。”樊哙十分豪迈,也不推辞,接过羽觞,便一饮而尽。对付项羽赏给他的猪腿肉,他也用剑切开,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史记》对这一细节的描述,到了“动作分解”的地步:“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这就像一部电影,在呈现主角生理变革时,要在他的脸上打光,通过光影的变革,来展现人物表情和动作的细微变革。对付“粗线条”的历史叙事来说,能将樊哙拔剑吃肉的场景还原到这个地步,很难想象这是没有根据的“脑补”。
接下来,便是樊哙那段有名的豪言壮语:“臣去世且不避,卮酒安足辞!
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
”
在后世不少人的影象里,樊哙只不过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将,但樊哙在此时说的一番话,切实其实有春秋战国时纵横家之风,不仅有理有据,还能结合暴秦的典故,让其辞吐有了当时最具道义合法性的根据——反对残暴不义,仁德者才能拥有天下。再加上之前樊哙饮酒吃肉的夸年夜动作,急速把项羽镇住了,这就为刘邦逃离现场争取了机会。
项羽反应迟缓,没能捉住机遇,让刘邦借口上厕所的时候逃走了。这对项羽来说,当然是无法挽回的丢失,但从“历史成功者”的视角看,这是刘邦在成功前最凶险的经历之一,而帮助他化险为夷的人,不仅是出谋划策的张良,更是直面危急时候的樊哙。
至此,樊哙的“精彩演出”还没结束。《史记》有记载:“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
如果说前面樊哙的一番豪言壮语已经令人惊叹了,此处他说的话则更不屈常。虽然刘邦碰着了危险,但竟然在慌乱中问樊哙怎么办,而不是问张良,或者自己直接下命令,这彷佛不合常态。但如果我们把樊哙当成这个故事的主色,理解到这场鸿门宴的细节很可能出自樊哙的讲述,那么这不屈常之处,也就能说通了。
我们再看《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对鸿门宴故事的阐述。这些内容既然来自樊哙的列传,主角当然该当是樊哙。但有趣的是,其内容与《项羽本纪》中的干系内容差不多,缩写了与樊哙无关的内容,而樊哙在鸿门宴上的表现,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删掉与樊哙无关的细节,依然不影响读者对鸿门宴前因后果的理解,这也从侧面解释,鸿门宴故事最精彩的场面,恐怕真是来自樊哙的视角。
樊哙前前后后的表现,成为鸿门宴上最精彩的瞬间。历史上鸿门宴的主色,当然是刘邦和项羽,但从史籍叙事的角度看,樊哙才是鸿门宴故事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