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沈从文
提到沈从文,就想到了他的情诗,他和张兆和的爱情故事,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他的笔墨是浪漫的,是诗意的,措辞格调古朴,纯挚厚实,朴讷真切,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他的生平充满坎坷,但他在这些坎坷经历中奉献了自己的生平。
沈从文生平创作过80多部文学作品,他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都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先后被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比候选人。
在沈从文的《虎雏》一文,讲述了一个关于改造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人的本性真的能被完备改造吗?故事中对小兵的改造,真的能成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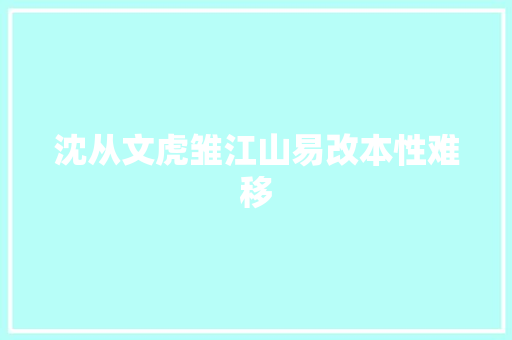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古以来我们就常常听到这句话,生理专家指出,“江山”指的是人的表面性情,是呈现给别人看的,会由于环境、外界成分而改变,而“本性”指的是人的内在人格,是专属于自己的特性,想要内在人格得到改变,一定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
1.机遇的涌现,可遇不可求
做军官的六弟带来一个勤务兵,二哥对他十分喜好,小兵不过十二岁,品貌出众,十分乖巧,干事有派头,还认识一些字。二哥对他欣赏不已,提出来让他随着自己,送他进学堂,给他另一个机会,使他在一个好运气里,得到他适宜的发展。
然而六弟并不以为然,以为十分可笑,以他对小兵的理解,以为这样做是在“害他”。他认为小兵在野蛮地方终年夜,他的内心充满野性,并不是如外表那么和顺。
“你以为那是在培养他,个中还有你一番美意值得感谢,你以为他读十年书就可以成一个名人,这真是做梦!
”
平时话不多的六弟,竟然讲出一大堆小兵不适宜进学堂的情由。兄弟俩间辩论不休,二哥以为环境可以改变任何人性,六弟的话过于武断。
末了二哥不甘心,也是带着闹气的说:“把他交给我再说。我要他从海内最好的一个大学毕业,才算是我的主见成功。”
两兄弟算是达到共识,六弟乐意把小兵留下来交给二哥培养,让他去试验一下,用事实来得到一个真理。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在部队里只能当一名勤务兵,侍候着军官们,因体弱又受到他人的陵暴。然而他并不是什么善类,只因拍浮时被一个学生取笑,自知空手打不过人家,便偷了枪去打人家,好在一枪不中,又怕人捉他,才走了,险些酿出大祸。
粗野的环境,让小小少年如野草般发展,学会了以暴制暴,六弟认为他这种脾气只好去当强盗。正是这种弱肉强食的环境,让他学会了察言观色,知道什么时候把自己隐蔽起来,也知道如何与大人打交道,取得他们的欢心。
小兵也被大学教授以及名人们的文人气息所吸引,小兵乐意留下来,“他见告我不愿意做将军,乐意做一个有知识的平民,他欢畅的样子是我描摹不下来的。”他喜好读书人的作派,也神往着文明地生活。
机遇可遇而不可求,对付小兵来说,这无疑是改变人生的一个转机,二哥也算是他生命中的朱紫,如果小兵能真的读书学文,往后的人生道路将会是另一番风景。
2. 表面易改,本性难移
二哥给小兵配置了学生的行头,给他找寻精良的老师。小兵认负责真学习,取得很大的进步,周围的人都对小兵赞不绝口、刮目相看。
二哥尝到了像做父亲一样的滋味,如果能培养一个精良的子弟,自己内心也会得到很大的知足感吧。
在茶余话后,小兵聊到与六弟各处剿匪的事情,谈到喜逐颜开,二哥看到小兵眼中放着一种奇异的光。大概二心坎深处更喜好军队生活吧,只是小兵年纪也小,还不会思考哪个路更适宜自己。
经由一段韶光的文学熏陶,小兵看似粗鲁的那部分一点点消逝,正在朝着希望的方向一点点提高。
改造两字可拆分解释,改字基本释意为变更,修正,而造字基本释意为制作的意思。结合起来的意思为变更原有的制作方法。修正或变更原事物,使适宜须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建立新的,使改造适宜新的形势和须要。
小兵受到了改造,确实变了,最最少表面上是。
可后来,小兵和另一个勤务兵三多一起出去玩,第二天,两人趁大人相聚的功夫,他们又偷溜出去了。然后,不再见人踪影,是逃了,还是去世了?谁也不知道。
在被子角,二哥创造了一封信,小兵见告他,他和三多闯了祸,打去世了一个人,三多被人打去世在自来水管上,小兵走了。
二哥依然远远地去打听小兵的,究竟一无所获,也登缘由想见告小兵,不愿意回上海,还是可以回湖南去,小兵依旧杳无音讯。
小兵在军营中终年夜,加上正是青春年纪,身上的野性在短韶光内不可磨灭。那样的时期,那样的社会环境,这个卑微的生命在努力地绽放着他的色彩,年夜胆胆大,不甘受陵暴。战乱、灾害都会重唤醒他的野性。
我们可以说小兵是本性难移,但大概是和韶光有关,毕竟他受到文化熏陶的韶光比较短,想要改变一个人,又怎么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呢?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教诲是一件大工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在动乱的年代,知识份子乐意以己之力去救国救民,饱含一颗颗忧国忧民的小儿百姓之心。
3.文学的时期代价
沈从文在文中末了说:“我连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还为他那外表所迷惑,不能理解,怎么还好说懂这样那样。至于一个野蛮的灵魂,装在一个俏丽的盒子里,在我故乡是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我还不大知道;我所知土豪平日,是那些山同水,使地方草木虫蛇皆非常厉害。”
从充满希望到令人揪心,出乎猜想的结果不仅给二哥带来欲望落空的悲痛,同时也使二哥流露出一种知识分子渴望改造国民却彻底失落败的茫然与困惑,颇具反讽意味。
人的野性到底能被改造吗?小兵自小的经历,充满野蛮的处事办法,到底能不能通过读书得到改进?
这篇文揭橥于1931年,我想沈从文此篇文章的意思便是如此吧,他也在迷惑:知识是否能改变命运,读书是否能影响国民整体本色,在战乱中生存,是须要文学的滋养,还是靠野蛮的战役?
在同期间,我们国家出身很多精良作家,鲁迅、萧红、抵牾、郭沫若等文学大师,他们用手中的一支笔,化成精神上的灵魂支柱,代替民众发出叫嚣的声音,在苦难的战役岁月里,他们用笔安慰着万万万的百姓心灵,让他们得到内心的安静。
文学一样是打击仇敌的武器,是解剖社会的钢刀,是唤起公民进军的战鼓。
《虎雏》故事不长,也很好理解,但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思考。由于当时的国情来看,沈从文忧国忧民的心思必定很深,他也在思考,作为一个文人,到底能做些什么,来帮助社会和民众。“战役使人类的灵魂野蛮粗糙”,那么,文学是否能让民众的灵魂变得崇高起来呢?
我们现在生活在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的环境中,从小接管文学教诲,也得到文明的熏陶,当然没有了野性,即便有,是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文明一定改变人类,文学的代价也更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