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落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嗟叹。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日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就寝,永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面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去世亦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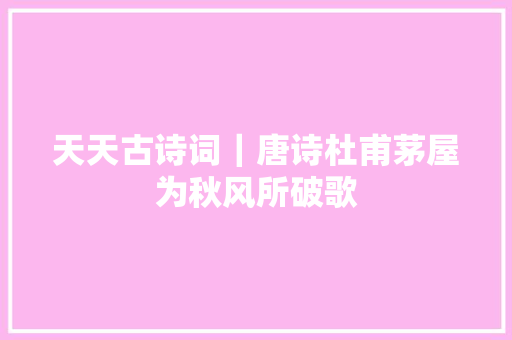
【注释】
(1)秋高:秋深。
(2)挂罥(juàn):挂着,挂住,缠绕。罥,挂。
(3)长:高。
(4)沉塘坳(ào):沉到池塘水中。塘坳,低洼积水的地方(即池塘)。坳,水边低地。
(5)忍能对面为盗贼:竟忍心这样当面做“贼”。能,如此,这样。
(6)入竹去:走进竹林。竹,竹林。
(7)呼不得:喝止不住。
(8)俄顷(qǐng):不久,一下子,顷刻之间。
(9)秋日漠漠向昏黑(hè):指秋季的天空浓云密布,一下子就阴暗下来了。漠漠,阴沉迷蒙的样子。向,渐近。
(10)布衾(qīn):棉被。
(11)娇儿恶卧踏里裂:指儿子睡觉时双脚乱蹬,把被里都蹬坏了。恶卧,睡相不好。
(12)床头屋漏无干处:意思是,全体屋子都没有干的地方了。屋漏,指屋子西北角,古人在此开天窗,阳光便从此处照射进来。“床头屋漏”,泛指全体屋子。
(13)雨脚如麻:形容雨点不间断,向下垂的麻线一样密集。雨脚:雨点。
(14)丧(sāng)乱:战乱,指安史之乱。
(15)何由彻:意思是,如何才能熬到天亮呢?彻,通,这里指结束,完结的意思。
(16)安得:如何能得到。
(17)广厦:宽敞的大屋。
(18)大庇(bì):全部遮盖、掩护起来。庇,遮蔽、掩护。
(19)寒士:“士”原来指士人,即文化人,但此处是泛指贫寒的士人们。
(20)突兀(wù):高耸的样子,这里用来形容广厦。
(21)见(xiàn):同“现”,涌现。
(22)号:叫
(23)三重(chóng)茅:几层茅草。三,表示多。
(24)向:渐近,将近。
(25)茅屋:这里指草堂。
【赏析】
这首可分为四节。
第一段中共有五句,句句押韵,“号”、“茅”、“郊”、“梢”、“坳”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伟大,犹如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郁的感情色彩——墨客好不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呼啸而来,卷起层层茅草,使得墨客发急万分。
“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紧承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草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地、雨点似地“洒”在“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转沉塘坳”,也很难收回来。“卷”、“飞”、“渡”、“洒”、“挂罥”、“飘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光鲜的图画,而且牢牢地牵动墨客的视线,拨动墨客的心弦。
墨客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怀达意,而是寓情意于客不雅观描写之中。这几句诗所表现的场景是:一个衣衫软弱、破旧的憔悴老人拄动手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呼啸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去,稀里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怫郁之情,不能不激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
第二段中共有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
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除此以外,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茅草,但却被“南村落群童”抱跑了。“欺我老无力”五字宜着眼,如果墨客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矫健有力气,自然不会受这样的欺凌。“忍能对面为盗贼”,意思是,群童竟然忍心在他的面前做盗贼。但实在,这不过是表现了墨客因“老无力”而受欺凌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以是,“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了。用墨客《又呈吴郎》一诗中的话说,这正是“不为困穷宁有此”,墨客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由于他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走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统统,都是结尾的伏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和崇高欲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根本上产生出来的。
“归来倚杖自嗟叹”总收一、二两节。墨客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足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料。“自嗟叹”中的“自”字,下得很沉痛,墨客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他自己在嗟叹,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淡薄,就弦外之音了,因而他“嗟叹”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分明遐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汉。
第三段共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日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陪衬出墨客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见之中。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贫乏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把稳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景象并不“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以是才感到冷。
“自经丧乱少就寝,永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纵,从面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各类痛楚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繁、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又回到“永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永夜沾湿”,墨客自然不能入睡。“永夜”是作者由于自己屋漏因而更觉夜长,还因自己和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中挣扎而以为夜长。“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料,表现了墨客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急迫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铁的艰巨处境引发出来的。于是墨客由个人的艰巨处境遐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迎刃而解,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全诗的结尾。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蝉联而下,而表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绪的词如“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宏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驰提高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墨客从“床头屋漏无干处”、“永夜沾湿何由彻”的痛楚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旷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这种旷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咏歌不敷以表达,以是墨客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呜呼!
何时面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去世亦足!
”抒产生发火者忧国忧民的情绪,表现了作者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高尚风格,墨客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空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诗作者抒发的情怀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抒发的情怀基本同等。
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墨客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楚,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墨客之以是伟大,是由于他们的痛楚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由于他是社会、时期、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楚,但他不是孤立地、纯挚地描写他本身的痛楚,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楚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楚,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期的苦难。他也不是仅仅由于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落眠、而大声疾呼,在狂风猛雨无情打击的秋夜,墨客脑海里翻滚的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绪和急迫哀求变革阴郁现实的崇高空想,千百年来一贯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浸染。